鲁迅晚年得子,他对待孩子什么样?
就像老子对待儿子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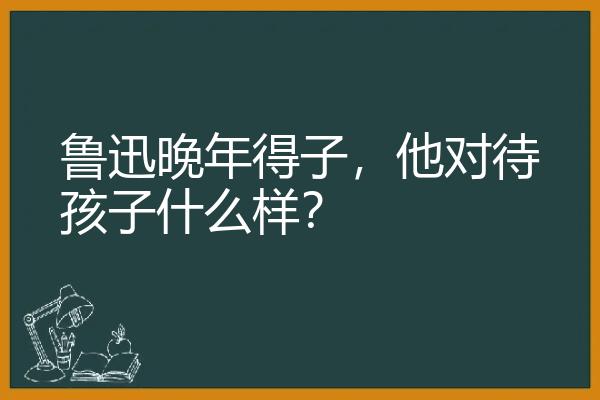
鲁迅晚年得子,他对待孩子什么样?
鲁迅持‘幼者本位’的立场,主张理解孩子、平等相待、解放孩子。”
但是,作为一个男孩,周海婴也偶然因顽皮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
鲁迅宽容的家教方式对周海婴产生了深刻影响。
鲁迅晚年得子,他对待孩子什么样?
走过了近百年的岁月,鲁迅流传下来的作品,至今都是语文课本中的经典,从小学到大学“鲁迅”这个名字,从未缺席过人们的读书岁月。无论是在课本中,又或者是一些老照片中,鲁迅先生总是一脸严肃,他的眼神、他的姿态,就如他手中的文章一样犀利。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待孩子又是什么态度呢?
鲁迅旧照
鲁迅的第一段婚姻是媒妁之言,他和朱安只是有名无实的假夫妻。直到后来遇到了许广平,这个看似木讷、不苟言笑的男人,终于收获了真爱,这在当时的民国,可是轰动文坛的师生恋。到了鲁迅晚年的时候,许广平终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周海婴。鲁迅仅陪伴了儿子7年的岁月,在这七年的时间里,鲁迅对待亲爱的儿子,展现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鲁迅与许广平
他给儿子取的名字很随意,儿子在上海出生,所以才有了“海婴”二字。当时听完鲁迅对于儿子这个名字的解释,人们都感到十分诧异,毕竟有个大文豪父亲,儿子的名字一定别具深意,绝对是深思熟虑所得,然而并不是。可是这并不代表着,鲁迅对儿子不疼爱。人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个平日里看起来格外严肃的文豪,从来不掩饰对儿子的宠爱。
在儿子还小的时候,鲁迅当时为了哄海婴睡觉,竟然写了一首《小红象》的打油诗,整首诗翻来覆去就标题中的这三个字,但是读来却格外有童趣。
鲁迅全家福
除此之外,鲁迅还凭借一切可以晒娃的平台,总是在不经意间就秀了一波娃。比如每当家里有朋友来做客,无论海婴是醒着,还是睡着了,他总是要把孩子抱出来炫耀。一旦吵醒了熟睡中的海婴,他还要细声细语的在哄儿子睡觉。这样巨大的反差,让人感受到了他当父亲时的喜悦心情,还有与往日全然不同的可爱。
鲁迅全家福
不仅如此,自从儿子出生以后,鲁迅每次给母亲写信,基本上两三句话里总要掺杂些儿子的信息,儿子平日里吃的好不好,最近有没有长个子,他都写在寄给母亲的信里。一方面是让母亲了解自己亲爱的孙子的状况,另一方面他能对儿子所有的事情如数家珍,可以看出他对于海婴的宠爱。
鲁迅和儿子周海婴
当儿子开始写字的时候,他就把儿子写的字拿给朋友炫耀。对于鲁迅这种过分的晒娃行为,也惹的朋友们时不时的笑话他,可是他还写了一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回怼朋友,从这句诗里可以看出,反正他就是要一个劲的宠着儿子。
鲁迅虽然是一个作家,可是他从来不强迫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比如海婴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将买回来的各种机械玩具拆开,鲁迅从来没有对他多加责骂,反而鼓励他去拆卸一些家中的大家电,更不强迫他去学习与文学有关的东西。鲁迅为人父只有7年,可是在这7年的时间里,他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
鲁迅晚年得子,他对待孩子什么样?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了很多与鲁迅短暂相处的片段,从这些小事中,足以可见鲁迅对待孩子是一个慈父。
父亲为我治病记得我小时候膝盖部位长过一疮,出脓穿破后,一个多月总不长新肉,露着一个大洞,经常流血不止,父亲给我用一种玻璃瓶装浅黄色的细腻药粉,填入伤口,过了不久,就从里向外长出新肉,伤口逐渐愈合。几十年的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但是父亲弯下身,细心地给我敷药的情景,至今犹在眼前。“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他的名言,也是对自己的很好写照。
我每年一到夏季,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抓挠不得,一不小心,溃破化脓,那就更加难受。记得每到晚饭以后,我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天色已暗,但不开灯,以求凉爽。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有盖的小碗和一块天然软海绵,将“兜安氏”痱子药水先摇晃几下,待沉淀在下层的药粉混合均匀,然后在小碗里倒上一点,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再搽一面。这是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刻,可以不怕影响父亲的写作而被“驱赶”,有机会亲近父亲,躺在父母两人之间,心里感到无比温暖。时间悄悄逝去,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回到三楼,在自己的卧床上进入睡乡。
我小时候种下了气喘病的根子,每到疾病发作期间,不但自己痛苦不堪,也使父母担心劳神,不胜其苦。
我得的这种哮喘病,每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发作。一犯起来,呼吸困难,彻夜不眠。父亲为我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且称之为蒸汽吸入法。架好一套吸入器皿,即在盛水小锅中卡上一支细管,加橡皮圈密封,将细管一端通入另一小杯,杯中装有调好的“重碳酸曹达”和食盐稀溶液,用酒精灯加热烧开,蒸汽将药液喷射带出,再经一玻璃喇叭口集中成为一束。这时母亲给我戴上围兜,并且蒙上眼睛(怕盐水刺痛眼睛),叫我张口吸气。湿润的水汽进入气管,药味咸而略苦。如果还不痊愈,父亲就改用一种药膏热敷。先将“安福消炎膏”隔水泡热,母亲按我背部大小准备一块布料,父亲用钝刀将白色的黏稠药膏刮在布上,贴在我的背部或前胸。二十分钟以后揭去。这种药膏不知都有哪些成分,仅感到有一种薄荷味,十分清凉,对于我剧烈的哮喘,也能起到缓和作用。
但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如芥末糊的功能来得神速。这似乎成了父亲对付我哮喘病的一张王牌。说起来也很简单,用一个脸盆,放进二两芥末粉,冲入滚烫的开水,浸入一块毛巾,待芥末汁浸透以后,父亲便用两双筷子插入毛巾,以相反的方向绞去水分,以我能够忍耐的温度为准,热敷背部,上面再用一块干毛巾盖住,十几分钟后撤去,此时背部通红如桃,稍一触及颇感疼痛。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而且又困又乏,缓缓睡去,往往可以睡个通宵。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其疗效大好,屡试不爽,但有时哮喘剧烈,此法仍不大奏效,父亲就直接用二三两芥末,加凉水和匀,如“安福膏”一样涂在布上,贴在背部。此糊虽凉,但越敷越热,刺痒灼热,颇不可忍。时间也以十分钟为度,若时间稍过,则背部灼出水泡,如开水烫伤一般。这样气喘虽缓,但却要吃另一种苦头了,因此父亲一般不轻易采用。
父亲因对我疾病十分重视,费去他不少精力。平时有点小毛病,即趁早为我治疗,如不奏效,就请医生或到医院就诊。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我没有详细统计,至少也在百次左右吧!但他对自己的疾病,却似乎不太当一回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父母去须藤医院诊治,我比较简单,只取一点药品,便和母亲进入一间有玻璃隔墙的换药室,这时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敞着。再顺眼细看,他的胸侧插着一根很粗的针头,尾部连有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接着地下一只广口粗瓶,瓶中已有约半瓶淡黄色液体,而橡皮管子里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其流速似乎与呼吸起伏约相适应。父亲安详地还与医生用日语交谈着。过了一会儿,拔去针头,照常若无其事地和我们一同步行回家。后来,我看他的《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记有“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相当于两百毫升),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目睹的这一次了,离他去世仅两月多一点,应该说,此时他已进入重病时期,而仍显得如此满不在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以至生命,真是太不看重了。对医生来说,除了注射一种药剂,我也未见施以什么特别的治疗手段。
电影和马戏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观看。有时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记得和父母一同看过的电影,有《人猿泰山》《泰山之子》《仲夏夜之梦》以及世界风光之类的纪录片。
看电影一般不预先买票,碰到喜欢的片子,往往在晚餐以后即兴而去。或者邀请叔叔婶母,或者邀请在身边的其他朋友,共同乘坐出租汽车去,当时汽车行就在施高塔路(现山阴路)路角,去人招呼一声,就能来车。车资往往一元,外加“酒钱”二角。因为看的多是九点晚场,因此对我来说,出去的时候兴高采烈,非常清醒,等到回家,已经迷迷糊糊,不记得是怎样脱衣,怎样上床的了。
由看电影进而观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名闻世界、誉驰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在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前,怕我受到惊恐,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自己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上述考虑的意见,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在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这“兽苑”里面,只是关着的动物,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的滑稽节目。不过这对于我,已经是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噘嘴嘟囔不休了。后来听说,这个马戏团去美洲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浪(一说船上失火),连人带兽,全部沉入海底。
从《日记》推算起来,我当时只有四岁多一点。时间虽然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由此可见,父亲为了我的身心健康,是何等煞费苦心。他的慈爱之心,至今仍时刻在温暖着我,也使我认识到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鲁迅晚年得子,他对待孩子什么样?
鲁迅原名周树人,生于乱世中,鲁迅坚决弃医从文,从文字上曲线救国,鲁迅也因此被称为知名的文化工作者,其作品老者,背影更是在文学届有鼎鼎大名。人无完人,婚姻上的鲁迅却一直被人指指点点。
有着超前思想的鲁迅,对于父母包办婚姻一直不认可,数次反抗无效后,鲁迅还是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虽然那个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正也因为这样,鲁迅母亲害了那个女子一生,受活寡的滋味,相比一般人是不能理解了。最终鲁迅还是和原配离了婚,勇敢的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人,换做现在来说,鲁迅没错,可是在那个年代,这已经超出了叛逆的范畴,已经是忤逆了。
鲁迅娶到自己喜欢的女人是他的学生,叫做许广平,两人非常相爱,两个人剩下了一个女婴,取名周海婴,因为从小受到父母文化的熏陶,在家鲁迅超前的思想,所以使得周海婴从小就接受新鲜事物,业务爱好更是跳舞,唱歌样样出众。
因为在周海婴八岁的时候鲁迅去世,十几年来周海婴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后周海婴嫁给了青梅抓马的玩伴他叫做马新云,两人婚后生下了四个孩子。
鲁迅的孙子称为周令飞。 去部队当了兵。练就了一身本事,后来我在国外大学读书。鲁迅的大曾孙子周景欣从小就长得好看,当他长大后,他从事表演艺术行业。鲁迅的第二个孙子是周亦斐。我从小就生意感兴趣。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鲁迅另外两个孙子已经去了日本出国留学。除了他儿子孙子外,鲁迅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后代,是他的侄孙子,也是骨干演员,他的名字是许绍雄,许绍雄并没有很高的面值,但许绍雄有能力在娱乐圈翻滚多年,很少有人知道他与鲁迅有关系。
鲁迅晚年得子,他对待孩子什么样?
而在多数人眼中,身为思想家、作家的鲁迅总是严肃犀利的,整个人仿佛好斗、多疑、不宽容、不苟言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耳熟能详的写照。
这样一位鲁迅先生,当他成为父亲,会在家庭教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教育孩子之时,又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是,现实中的鲁迅,其实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宠娃狂魔”……
49岁得子,宠娃成狂
鲁迅一生,有且仅有一个儿子,那就是与许广平所育的周海婴。
而且这个孩子,是在鲁迅半百之年所得。
当一个人到此年纪才有孩子,那份欢欣雀跃都不知要如何表露才好。时下常被批判的“丧偶式育儿”,在鲁迅这里全然不存在。
“海婴六个月,1930年3月23日,上海”
海婴幼时体弱多病,半夜每每咳嗽啼哭,需要大人照料,据许广平回忆,不管隔了几间房间、几幢楼,只要儿子咳嗽一声,鲁迅总会敏感地起身,前去查看。
在鲁迅的笔下,那份爱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温柔耐心也时常洋溢于纸面之上。
他会绞尽脑汁给孩子讲睡前故事;
也会打趣般和孩子说一些童真洋溢的胡话;
每逢孩子闹情绪消极抵抗的时候,鲁迅也不恼,而是竭尽全力地哄着,说好话;
就算是儿子在自己伏案写作到一半时跑来,或是小手胡乱弄脏了文稿,鲁迅也不生气,而会无奈地笑笑,停下来陪孩子玩耍。
也难怪后来周海婴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远远不是历史资料中那种古板严苛、不苟言笑的模样,而是会亲昵地叫着自己“小乖姑”、好脾气又愿意听自己说话的玩伴。
鲁迅的确是一位“日理万机”的文坛巨匠,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位爱意满满的父亲,而这种近乎宠溺的关爱与陪伴,也为幼年时期的周海婴提供了最美好的成长温床。
家庭教育的精髓
在于“顺其自然”
当然,鲁迅为父之道的独特,不在于他肯通宵地照料孩子,不在于愿意拿出时间来陪孩子,也不在于孩子怎样捣乱他都不恼怒,而在于鲁迅对于自家孩子,始终保持同理心与宽容的态度,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儿童。
“顺其自然”,正是他一贯奉行的教育准则。
鲁迅自身成长于一个传统的封建之家,在那样的家庭里,父辈的权威大于一切。
孩子,更多地被训练成听话的机器,或是按照父母的想法,成长为成年人需要的样子。
但如此规训式的教育,并不为鲁迅所接受,相反,他发誓要在自己的家庭教育实践中,永远倾听孩子的声音,尊重孩子的选择。
鲁迅给儿子取名“海婴”是因为孩子在上海降生,自己极其喜欢这座城市,但他也直言,若是孩子哪天不喜欢此名,“可随意去改”。
周海婴幼时有一件珍爱的组装金属零件的玩具,用这些零件,他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再拆,拆了又装,乐此不疲。
鲁迅对此丝毫不觉得“玩物丧志”,而是由着孩子的天性随他去,时不时还在一旁鼓励。
等到有兴趣读书时,海婴要看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文库》,许广平以为太深,要大些再看,鲁迅则站在孩子一边,“任凭选阅”。
鲁迅的好友、著名作家萧红就曾诧异于备受尊崇爱戴的鲁迅先生,在对待自己儿子时,就好像刹那间变成了同龄的伙伴。
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提到:
有一次她跟着鲁迅全家人下馆子,点了一道常吃菜式——鱼丸,可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尽管大人们吃起来都觉得并无问题。
换作旁人,定会认为是孩子故意找茬,许广平就已面有愠色,觉得孩子不省心,可鲁迅先生却认真听了儿子的抱怨,又亲自尝了尝孩子碗里的鱼丸,发现果然有个是坏的。
“孩子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大人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这句平平无奇的话语,让萧红感叹了很久,要知道,这种任何时候都能与孩子平等对话的能力,并不是每个父亲都能有的。
鲁迅的态度,和如今大热的“蒙特利梭教育”颇有些不谋而合。他倡导“儿童的发现”,尊重孩子的自然天性,两代人相处之道应是平等的亲爱与宽容,而非上施于下。
他没有培养出天才
却培养出一个完整、圆满的人
在1919年发表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鲁迅更为细致地给出了自己的教育观:
譬如把儿童当作独立自在的人去理解;譬如以儿童为本位,指导孩子的身心;譬如给孩子发扬天性的机会等等……这一切,也是被他浸润在日常家庭教育中的核心。
“养成孩子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即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而不被淹没的力量……”
那么如此成长起来的周海婴,究竟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周海婴并非世俗意义上人们所期待的天才,某些能力远不及父亲,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幼时背书怎么也记不住,文字才华也有限,时常听到老师发出叹气。
但周海婴的人生,延续了由父亲鼓励玩耍的组装玩具所生发出的机械理工兴趣,少年时用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之后,最终在无线电领域扎根。
随后,便是低调、勤恳的科研岁月,偶尔露面,也是为了宣传纪念父亲及其作品,要说他活得多么轰轰烈烈、功成名就,那倒未必,到头来也只不过在一份平淡的事业之余,娶妻生子,淡然过完一生。
他没有父亲的名气,事业上的成就更比不上父亲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却展现了一个资质普通的孩子完全伸展自我后发展出的模样。
周海婴的人生,是平淡,清正,却又幸福的,他在父亲醇正的爱意与陪伴中成长,享受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平等的父子关系,父亲对他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伴随了一生。
周海婴曾说:且不论赚多少钱,有多少声名,一个人能过得“完整、圆满”,就很好。
人的“完整、圆满”,不正是教育的初心?
据说,周海婴与父亲之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父子俩都要互相打招呼,道一句“明朝会”。
后来,鲁迅病痛渐深,喉咙那里总有浓痰堵着,但无论如何难受,每晚他都会勉强支撑起身子,用尽可能响亮的声音回应儿子:
“明朝会,明朝会。”
1936年,鲁迅病逝,这一年鲁迅55岁,周海婴7岁。七年的父子情缘,就这样以“孩子长大后不喜欢名字可随意改”为开头,以重病中挣扎起身、互道“明朝会”而结束。
虽然参与孩子生命的日子不算太长,但谁又能说,鲁迅不是一位好父亲?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