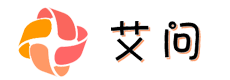《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让吕方去守灵?
刚才在大街路边上坐着,一个老头牵着一条狗,路边来来往往的人都绕着他们走,老头左牵猛犬右扇蒲扇悠闲地走着,这时候一个骑自行车的飞速冲来,黄狗立刻呲牙相向,老头马上一收狗绳,把狗拉了回去,小黄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
说难听点,吕芳就是嘉靖皇帝的一条狗,平时放出来咬人,遇到狠角色,就要把他拉回去保护一下,硬碰硬嘉靖不会受损,吕芳却会遭殃。明朝的内监专权跟历朝历代都不同,前朝的内监们有很多是实打实地把最高权力抓在了手里,明朝的内监们只是代皇帝行使皇权,大多是狐假虎威而已。吕芳被赶走守皇陵以后,陈洪拿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嘉靖说了一句,掌你的印去吧,这个陈洪还算聪明,听了这句话还琢磨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他只是给主子看护印的,嘉靖这才满意,因为陈洪不像吕芳那么有分寸,所以嘉靖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不要太过跋扈,他只是主子的一条狗。
吕芳被赶去守皇陵的导火索是海瑞夜审郑必昌何茂才这两个蠢货的那份供词。第一次这份供词送到京城,让吕芳拦截了下来,没给嘉靖看,但是消息到底传到嘉靖那里了。吕芳这时候却去找了徐阶和严嵩两个党争的首领去劝酒谈和。不得不说,这件事已经超出吕芳的能力范围了,所以事后嘉靖对吕芳说这酒也是你劝得的?还举出典故,说出这件事的严重程度。
前期严嵩作为内阁首辅十来年专权跋扈,甚至连裕王的年例银子也敢怠慢,都是因为嘉靖的宠信,可是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开头,我们的编剧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倒严的势力已经联盟成功,老中青三代都聚集在了裕王府,其实真实的历史上,这个时候常呆在裕王府的是陈以勤和高拱,因为他们才是裕王的老师。但是编剧却把徐阶高拱张居正放在裕王府,意思很明白,倒严的势力已经结盟,而且背后有了裕王的支持,让嘉靖不能再忽视他们的实力。
如果说前期派谭纶去浙江,还只是倒严党对严党的掣肘,把海瑞弄到浙江去,则是正式对严党出手了。接着就接连拿下了沈一石,郑必昌,何茂才,杨金水,海瑞就是倒严的急先锋,只是海瑞并不知道他被利用了,他也只是这盘大棋的一个棋子,却还跟王用汲忧心能不能因为改稻为桑的事走出浙江。倒严党胜了,海瑞就是功臣,倒严党败了,海瑞就是替罪羊,活不活已经不是由改稻为桑这件案子决定了。
深居简出的嘉靖鼻子很灵敏,他已经知道这场绞杀已经开始,无法避免,而吕芳却还后知后觉,还去劝和,哪有这么蠢的奴才?
此时的吕芳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赶紧退出,逃离战场,另一个就是狠下心来,拿出雷霆手段,代主子大兴杀伐,替主子尽完忠背完锅而后粉身碎骨。可是这两条都得主子嘉靖点头才行。
吕芳这个人,嘉靖是了解的,忠心为主,明辨是非,左右逢源,唯一的缺点就是心不够狠。所以嘉靖给他选了前面一条路,把他弄出了这场严党和倒严党的绞杀,因为无论跟哪方搏斗,吕芳都不是对手,因为心不够狠,而且还有可能因此把战火引到嘉靖本人身上,这是嘉靖最忌讳的,外面怎么斗,包括他的儿子掺和进去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把他自己卷进去,他要的就是权力平衡,而那个唯一能左右所有平衡的只能是他嘉靖。
总之,嘉靖对吕芳还算不错,把他弄走保护了他。同时弄走了吕芳,重用陈洪这个狠人,可以把一切在这场斗争中想攀扯他的都打回去。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让吕方去守灵?
两个原因。
第一,吕芳开始押宝裕王。从吕芳派冯保去裕王处开始,其实吕芳就已经在为自己留后路了。嘉靖明面上啥都没说,可吕芳后来私自同徐阶和严嵩会谈,就彻底惹怒了嘉靖,吕芳被发派吉壤半个月。
本来这事处罚完了也就过去了,可等到海瑞进京,偏偏又在嘉靖钦点的六必居上做文章。嘉靖改字的本意是要给那些倒严的人心里添一把刀,一个酱菜的老板都这么落井下石,其他的官员可想而知。
嘉靖需要平衡朝野势力,尤其是想起用胡宗宪这样的人,因此肯定不想让严党被打压的太厉害,改字就是为了给清流一个警告,凡事别做得太过了。可这样做也催生了新的问题:即严党势力不堪大用,而清流派也处处手脚被缚,国家机器运转效率太低。
海瑞改字本来就是直接把矛头对准嘉靖,其次裕王又通过冯保和吕芳这条线得知消息,而海瑞本身也是欲望举荐的。这样一来,裕王、海瑞、吕芳、冯保变成了同一战线,而对手正是嘉靖。裕王肯定不能动,海瑞也是朝廷命官(动他需要合理的理由),这样一来就只能通过惩戒吕芳和冯保这两个人来敲打裕王集团。因此,冯保被关押至朝天观,吕芳被发派去南京守灵。
第二,嘉靖不忍心让吕芳为他遮风挡雨。严嵩严世蕃倒台后,嘉靖怠惰朝政,修宫殿炼仙丹的臭毛病一点没改,结果就是官员发不出俸禄,灾民被饿死,打仗没有军需。徐阶此时作为内阁首辅并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许多事撇得十分干净,官员们也知道找徐阶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就有了群臣雪夜在西苑门口抗议的一幕。
嘉靖是何等聪明专权的帝王,四十年前杨廷和那帮人都没有让他低头,现在这些个小虾米更不可能。但他又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不会直接去训斥这些官员,结果那就只能去找个恶人来帮自己挡一挡了,陈洪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就像嘉靖说的“朕用陈洪就用在一个狠字。吕芳不会这样做,朕也不忍心让他做。”
提前同储君往来,这是不忠;一朝天子一朝臣,时局变了,人也就该换了,这是无用。不忠而又无用,吕芳焉能不去守灵?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让吕方去守灵?
吕芳是干嘛的?司礼监太监。
司礼监有一个掌印太监和若干个秉笔太监,负责代行皇权中的“批红”。军机大事由各省、部报到内阁,内阁拟出处理意见,用纸票贴在封面上(是为“票拟”),由司礼监代皇帝批复,因为用红笔,是为“批红”。
吕芳被贬,是从“六必居”开始的。严党倒台,严嵩给酱菜铺“六心居”题的匾额没人要,嘉靖御笔改为“六必居”,取“六合一统,天下一心”之意,即告诫清流不要因为严嵩倒了就自以为得计,大明还是要以嘉靖的心为心,不能有二心。海瑞到了之后,却在嘉靖密探的眼皮底下公开指出这“六必”应该是“产地必真,时令必合,瓜菜必鲜,甜酱必醇,盛器必洁,水泉必香”。嘉靖没有发作,让裕王(注意这点)亲笔抄下海瑞的话,送到六必居去。(题外话,真正的六必居是清朝创立的,严嵩题匾只是传言)
嘉靖和清流互相试探,海瑞初入北京一番言论使得嘉靖更为警觉——没了严党,等于“严党-清流-太监”的铁三角缺了一块,“云在青天水在瓶”也在不下去了,所以一直在弥缝局势的吕芳就不适合此时的朝局了,嘉靖需要一个能给自己干脏活、能出去和清流打擂而且下得去手的人。这个人就是陈洪。于是,吕芳去了南京守陵。
其实到了这一步,去南京守陵也未必不是个好退路——看看严嵩什么下场大家就知道权力这玩意多可怕了。“思危、思退、思变”,在退的时候嘉靖给了吕芳退路,由此可见嘉靖对这个跟随了自己四十年的太监,还不是心如铁石。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让吕方去守灵?
嘉靖皇帝朱厚熜作为一个捡来的皇帝,要不是上一任皇帝没有子嗣,也轮不到他,又因为“壬寅宫变”差一点被宫女杀死,使他任用奸臣严嵩,把大明弄得破烂不堪,入不敷出,他又一心修道,自以为是,虽然他还算明白,有一些帝王之术,不过作为一个皇帝,用一些阴招来驾驭朝局总不是办法。
太监作为明朝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存在,吕芳还不算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他善于揣测帝心,又想为皇帝、为大明操好心,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所以嘉靖皇帝先让他吃吃苦头,再返回头去重新任用,也让吕芳认识到自己的那些儿、孙,谁更着靠。
《大明王朝1566》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上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既有天下第一直吏海瑞的出现,也有戚继光大败倭寇的战争,更有大奸臣严嵩的垮台,让我们通过嘉靖皇帝对大太监吕芳的教诲,看看1566年都是发生了些什么!
那么嘉靖帝为什么让吕芳去守灵呢?主要是严嵩把持朝政,引起了以太子裕王为首的清流派的不满,严嵩、特别是他的儿子严世藩更是篡改圣意,中饱私囊,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又与宫中制造局狼狈为奸,把年初制定的“改粮为桑”的国策,演变成了残害农民,强取豪夺土地的败策。
从而制造出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大案,最后以查出浙江巡抚、浙江按察使才算匆匆了之。先从海瑞审案开始,让我们一步步揭开当初那个年代终究发生了什么!
海瑞审案海瑞又望向了何茂才:“你说毁堤的事是杨金水指使的,有何证据?”
何茂才这是最后一张牌当然咬死了:“没有证据。要证据,你们可以去问杨公公。”
何茂才如此狡赖顽抗把王用汲也激怒了:“何茂才,你也是两榜进士,这个时候把罪证往一个疯子身上推,你不觉得汗颜吗?”
何茂才:“他疯不疯不关我的事。”
海瑞:“你是浙江按察使,当时胡部堂是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这样大的事胡部堂不知道,你也不请示胡部堂,就会听一个织造局总管的话?你以为你这样的供词能蒙混过关吗?”
何茂才咬着牙又想了想:“杨公公当时说是奉了上面的意思叫我们这样干的,我不能不听。”
海瑞:“这个上面是谁?”
何茂才被问住了。
海瑞:“是谁!”
何茂才:“他说的上面我怎么知道?”
海瑞转对王用汲:“请记录在案。”
王用汲心里痛快些了,飞速记录。
海瑞:“何茂才,我现在把你刚才的供词归纳一遍,你听清楚了。你说今年五月毁堤淹田是杨金水的主意。可杨金水不过是一个织造局总管,并无权力调动你按察使衙门的兵丁,你又说杨金水是奉了上命,因此你不敢不听。问你他奉了谁的上命,你推说不知道。其实你知道。杨金水直接归司礼监管,司礼监一向奉旨意办事。你说的这个上命就是司礼监,就是皇上。是不是?王大人,请把我的话记录在案。”
“慢!不要记录。”何茂才有些喘气了,“我、我没有这样说。”
海瑞站了起来,猛拍惊堂木:“那我最后问你一句,毁堤淹田是谁叫你干的!”
何茂才还是沉默在那里。
海瑞:“那就将这张供词让他画押,立刻送到朝廷。画押!”
何茂才哪里敢在这样的供状上画押,一下子懵在那里。
海瑞:“你不画押,我就叫人让你按上手模也行。来人!”
提审房的门砰地被推开了,两个狱卒奔了进来。
海瑞:“钦犯不肯画押,架上他按手模!”
两个狱卒一边一个架住了何茂才。
何茂才扛不住了:“我、我有另情招禀!”
海瑞和王用汲对视了一眼:“那你们先下去。”
两个狱卒又放下了他,退了出去,把门又掩上了。
海瑞两眼直盯着何茂才。
何茂才低下了头:“毁堤淹田是小阁老写信让我们干的。可杨公公也知道,也同意。”
海瑞:“胡部堂知不知道?”
何茂才:“不知道。”
海瑞:“郑泌昌知不知道?”
何茂才:“知道。”
王用汲飞快地记录,记完了向海瑞点了点头。
海瑞望向何茂才:“画押!”
何茂才那份供词就摆在大案上,赵贞吉站在中间,谭纶站在左边,锦衣卫那头站在右边,都睁大了眼睛一个字一个字看着。
海瑞、王用汲还有另外三个锦衣卫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他们看完供词。
供词看完了,三个人都抬起了头,目光都亮亮的,但谁也不说话。
“我看这份供词可以立刻呈交朝廷!”谭纶打破了沉默。
赵贞吉把目光转望向锦衣卫那头。
锦衣卫那头:“郑泌昌那份供词送不送?还有,这里面这么多诽谤圣上的话也能够原样送上去吗?”
赵贞吉:“那上差的意思是什么?”
锦衣卫那头:“一切牵涉到圣上的话都要删去。”
赵贞吉又望向了谭纶、海瑞和王用汲:“你们看呢?”
海瑞:“我不这样看。诽谤圣上正可见郑泌昌、何茂才已经是无父无君之人,这样的人才会干下这么多祸国殃民的罪孽。《大明律》载有明文,凡是奉旨审案,都要将原供词一字不改呈交朝廷呈交皇上。改了,便是欺君。”
锦衣卫那头不说话了,转看向赵贞吉。
赵贞吉知道,这时最要紧的是态度,想了想慢慢说道:“《大明律》是有明文规定。可身为臣子,明知逆犯是为了规避罪责诽谤圣上,也不忍将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送上去有伤圣名。海知县,可不可以再审何茂才,按照镇抚司上差刚才的意思,另呈一份供词?”说到这里他又转望向谭纶,目有深意。
谭纶立刻明白了个中利害,但实在没有把握能说服海瑞接受这个主张,一时愣在那里。
海瑞立刻说话了:“各位大人当然可以再审何茂才,也可以再审郑泌昌。但这份供词是我审出来的,我必须原词呈交朝廷。”
锦衣卫那头焦躁了:“这样的供词交到朝廷内阁看了会怎么样?司礼监看了会怎么样?怎么上奏皇上?”
海瑞:“如实上奏皇上。狂犬吠日,我不知各位何以有这么多的忌讳。”
天生一个海刚峰,作为明朝历史上难得的一个亮点,海瑞如同一股清流让人眼前一亮!
吕芳擅作主张,揣测帝心被罚守灵四大秉笔太监是早已看过的,这时都屏着呼吸等吕芳看完。
吕芳的目光慢慢抬起了,望向门外越来越亮的曙色,一只手慢慢伸过去摸案头边的那个茶碗。
黄锦及时端起了茶碗双手递了过去,吕芳抓过了碟子上的茶碗,竟突然狠狠地向大案前的砖地上砸去!
碎片迸溅,茶水四溅!
四个人都吓了一跳。
“浙江到底要干什么!严嵩和徐阶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吕芳从来没有这般怒过。
“要咱们五个人的头嘛。”首席秉笔太监陈洪接言了,“杨金水已下令抓了,尚衣监、巾帽局,还有宫里好些人都在查办了,他们还要把事情往宫里扯,往皇上身上扯,大不了把宫里这十来万人都砍了头嘛。”
“前边在打仗,国库里又空着,真不明白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斗。”另一个秉笔太监也十分气愤地说道,“严阁老、小阁老他们就算做得不像话,这个时候也还得靠他们的人在前边顶着。都拿郑泌昌、何茂才开刀了,还要追什么毁堤淹田,追什么井上十四郎,这样子赶尽杀绝,把胡宗宪也扯进来,浙江的仗还打不打了!”
“置气已经晚了。”这些人一闹,吕芳反倒很快冷静下来,“这样的供词万不能呈到主子那里去。你们说怎么办吧。”
表态是不要本钱的,出主意日后可要担干系,刚才还十分义愤的几个秉笔太监这时偏沉默了。
只有那黄锦实诚,望着吕芳:“干爹虑得是。这样的供词呈给主子万岁爷,那便是要逼着主子下决断兴起大狱,可这个时候主子哪能下这个决断。这样让主子作难,我们这些人真就都该死了。干爹,这个难得我们担起来。”
吕芳深深地望向黄锦,目光里三分感激七分透着忧伤:“他们这些家大业大的反不如你一个没家的人晓事啊!”他叹了这句,提高了声调:“可咱们也不能五个人全扯进去,主子将司礼监交给了我,这个难应该由我来担。你们听好了。”
四个秉笔太监都深深地望着他。
吕芳:“主子已经有二十一天没有修手脚了,锦儿,今天上晌你去替主子把指甲都修了,活做得越细越好,给我腾出两个时辰,别让主子叫我。”
黄锦:“儿子这就去。”
“不急。”吕芳慢慢拿起了大案上的两份供词,折好了塞进袖中,“海瑞和王用汲审的这两份供词我得给两个人先看看。等我回来,立刻发回浙江,明令赵贞吉重审。陈公公。”
“干爹。”陈洪连忙躬了下腰,您老还是叫我儿子吧。”
吕芳审望了他一眼,稍顷:“也是。上阵父子兵,你是首席,平时我得尊着你一点,今天我就叫你洪儿吧。”
陈洪这时立刻接道:“儿子在。”
吕芳:“给赵贞吉的廷寄你立刻写,问他将这样的供词呈上来是呈何心!写完后等我回来再将海瑞和王用汲那两份供词一同八百里急递浙江,命赵贞吉叫海瑞、王用汲重审。”
“儿子明白。”陈洪答了一声,却又问道,“倘若干爹回来之前主子万岁爷问起这个事,儿子们如何回话?”
吕芳望了他一眼:“这几份供词也不能全瞒着主子。主子真要问起,便把赵贞吉、谭纶他们审的那两份供词呈上去。那个时候我的事也该办完了,问什么话,你们不好回答往我身上推就是。”
陈洪两眼望着地:“干爹放心,能拖儿子们一定拖到干爹回来。”
吕芳望向另外两个秉笔太监:“打招呼,这里的事有一个字透出去,立刻打死!”
那两个秉笔太监:“儿子明白!”
“快卯时了。”吕芳站了起来,“立刻叫酒醋面局找一坛嘉靖元年窖藏的花雕,搁到我轿子里,我要出宫。”
……
嘉靖还是那身宽大的便袍盘坐在蒲团上,厚重的淞江棉布袍服罩着盘腿也罩住了整个蒲团,见黄锦一手提壶、一手提盆走进精舍,脸上竟露出了孩童见到糖葫芦那般的笑容。
黄锦将木盆下脚的那边摆向嘉靖的蒲团前,拖着长音说到:“主子,松柏常青!松香味要起喽!”一边喊着,铜壶里粗粗的一线热水沿着木盆内部的木板周圆射了进去,热水激出木香氤氲腾起。
嘉靖早吐出了腔腹中的那口气,这时微闭着嘴,用鼻子细长地深深吸着,热水泡着新木那股松香味慢慢吸进了他的五脏六腑,在他的龙体中游走。如此往复,嘉靖一连吐吸了好几口长气,一直把松木的香气吸得渐渐淡了,便不再吸气,眼睛也慢慢睁开了。
黄锦这才到木盆边蹲下:“主子,咱们热脚喽!”喊了这句,伸过手去轻轻捏着嘉靖身前的袍服往自己这边一撩,整个袍服恰好盖住了脚盆,搭在高出一尺的木盆边上。
嘉靖看人从来没有这样的目光,望着黄锦就像乡下人家的老爷望着自己憨直的仆人,脸上露着毫无戒意又带着些许调侃的笑态。
黄锦蹲着,将双手从高处木板那两个圆洞中伸了进去,在罩着木盆的袍幅里开始给嘉靖按着穴位搓脚。
嘉靖望着黄锦,整个面容都松弛了下来,显然十分舒坦,平时从不说的家常话这时也开始说了:“黄锦。”
“奴才在。”黄锦一边娴熟地给他搓脚,回话也十分松弛。
“古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你们扬州有什么好?”嘉靖开始调侃他。
“主子这是在明知故问呢。”也只有黄锦敢如此回话,低着头找着穴位只管搓脚。
“杭州那边有新消息吗?”嘉靖突然问道。
黄锦的手在圆洞里停住了,接着故作放松又搓了起来:“好像有两份赵贞吉和谭纶审郑泌昌、何茂才的供词,司礼监正在归置,归置好了就会呈奏主子。”
嘉靖的脚在木盆中定住了,黄锦的手也只好跟着停住了,抬头望向嘉靖。
嘉靖:“两份供词归置什么?谁在归置?”
黄锦只好答道:“今日陈洪当值,应该是陈洪在归置。”
嘉靖将两只脚提了起来踩在木盆边:“叫陈洪立刻拿来。”
黄锦一怔,那颗心立刻提了起来,他知道干爹此时尚未回宫。
——吕芳这一坎只怕是很难过去了。
玉熙宫里已经没有了黄锦,也没有了那个脚盆,跪在蒲团前的是陈洪!
嘉靖适才对黄锦那副轻松调侃的神态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张脸比身边那座铜磬还要冷硬,在等着陈洪回话。
陈洪只是趴着,两眼反正嘉靖也看不见,不停地在那里转溜。今日这一番奏对,不是一步登天,便是一脚深渊,他准备赌了。可怎样赌,那颗心已经提在嗓子眼上急剧思索。
“不回话,就不用回话了。”嘉靖的声音比脸还冷,“滚犊子吧!”
“回主子万岁爷!”陈洪装出十分惊惶,头却反而埋得更低,“奴才这就回话,如实向主子回话。只是望主子体谅老祖宗也是一片苦心……”
“什么老祖宗!”嘉靖吼了,“谁的老祖宗!我大明朝只有太祖成祖才是老祖宗,你们哪里又找来个老祖宗了!”
陈洪心里颤着发喜,声音也就颤得十分自然,连着磕了几个响头:“奴才糊涂!奴才浑球!奴才这就将这张臭嘴撕了!”说着硬是狠狠地掐着自己的嘴使劲一扯,那血便从嘴角流了出来。
“不要装了!”嘉靖又喝住了他,“吕芳跟你们怎么说的?都瞒着朕在干什么?”
陈洪慢慢抬起了头,要将嘴角那些血露给嘉靖看:“回主子万岁爷,浙江八百里加急递来了几份供词,吕芳只让奴才们将两份呈给主子,还有两份他带着去见严嵩和徐阶了。”
嘉靖那张脸立刻涨红了:“好哇!三个人联手瞒朕了!”
陈洪又把头趴了下去,在等着雷霆更怒。
嘉靖这时反倒没有声音了,脸上的潮红也慢慢隐了回去,在那里阴阴地想着。
陈洪忍不住偷偷望去。
嘉靖望着精舍门外的南窗:“他叫你们怎么做?”
陈洪慌忙又磕了个头:“回主子,吕芳叫奴才用司礼监的廷寄连同另外两份供词发回浙江,命赵贞吉另外弄两份供词再呈给主子看。”
嘉靖:“好办法。就照他说的去做。”
“主子!”陈洪倏地抬起了头,“奴才万万不敢。”
“朕叫你敢!”嘉靖紧盯着他,“朕刚才同你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要露出去。回司礼监仍按吕芳说的去做。听明白没有?”
陈洪知道大功成了一半了,仍装着惶恐:“奴才、奴才遵旨。”
吕芳回到司礼监值房已近午时,累的是心,坐下来时接过黄锦递来的面巾擦了擦汗已经十分疲惫。
黄锦有好些话要说,陈洪偏又在面前,心里急,只好等吕芳问话。
“主子那边怎么样了?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吕芳问话时气有些虚。
黄锦还没开口,陈洪已经把话抢了过去:“回干爹,开始是黄公公在伺候主子,不知为何主子问起了杭州的事,把儿子叫了去……”
“你是怎么回话?”吕芳倏地站了起来。
陈洪:“当然照干爹吩咐的回话。主子起了疑,儿子掌嘴发誓,这才平了主子的气。”
吕芳这才看见陈洪的嘴角肿了,破了的那条口子仍带着血痂,便有些伤感:“你们的差也难当啊。给浙江的廷寄写好了吗?”
陈洪从袖中掏出了写好的廷寄:“干爹看看还要不要改一改。”
吕芳:“你写的自然不会差。不看了,连同这两份供词立刻送浙江吧。”说着从袖中也掏出了海瑞审郑泌昌、何茂才那两份供词递给了陈洪。
“干爹!”黄锦在陈洪接过供词时忍不住叫他了。
吕芳望向了黄锦。
黄锦眼有忧色:“是不是再想想,这两份供词还是呈给主子看了?”
吕芳:“不能呈主子看!发吧。”
“儿子这就去发!”陈洪大声接言,拿着廷寄和供词大步走了出去。
吕芳捶了捶后腰:“我也该去见主子了。”黄锦立刻搀着他,向值房门外走去。
精舍平日里只有吕芳进来时可以事先不禀报。此刻吕芳轻轻进来,见嘉靖闭目在蒲团上入定,便也不叫他,一如往日,到神坛前先换了香,然后拿起一块白绢湿巾无声地四处揩擦起来。
“修长生,修长生,古来到底有谁是不死之身?”嘉靖突然说话了。
吕芳一怔,轻步走了过来:“回主子,远有彭祖,近有张真人,都是不死之身。”
“彭祖不可信。”嘉靖睁开了眼,乜向吕芳,“张真人一百二十岁突然没了踪迹,找了二百年仍然没有找到。依朕看,朕的万年吉壤还得抓紧修了。”
吕芳沉默在那里,已经感觉到嘉靖的神态有些异常。
吕芳:“你是跟了朕四十年的人了,朕的万年吉壤派别人去朕不放心。把司礼监的事交给陈洪,你今天就去,看看朕的永陵修得怎么样了。”
何以有如此大的变故!乍听太出意料,似乎又在意中。吕芳不暇细想,跪下了:“启奏主子,奴才是就去看看,还是留在那里监修工程?”
嘉靖盯着他:“好些事你都是自己做了主算,这还用问朕吗?”
吕芳先还是一愣,接着明白了,趴了下去:“奴才明白了。主子的万年吉壤奴才一定督着他们修好。”
嘉靖闭上了眼不再跟他说话。
吕芳磕了个头,慢慢站了起来,走出去时也不知是太累还是因这件事来得太突然,跨门槛竟然趔趄了一下,赶紧扶着门框这才站稳了,匀了匀气,艰难地走了出去。
嘉靖的眼这时才倏地睁开:“陈洪!”
“奴才、奴才在!”陈洪的声音远远的在大殿门外传来,身影却出奇地飞快显现在精舍门口。
嘉靖:“传旨。”
陈洪跪在精舍门外,抬头紧望着嘉靖。
嘉靖:“严嵩不是病了吗?那就叫他在家里养病。叫徐阶搬到内阁值房来,就住在这里。司礼监的印你先掌着。”
对于吕芳的责罚,是嘉靖帝对吕芳擅越朝政的不满,因此让他吃些苦头,好认识到天下是皇帝的,你一个太监不过是皇帝身边的一条狗,虽然主人对你好、对你信任,可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吕芳趴在了地上,尽力控制着身子不动,泪水却一滴一滴洒在了砖地上。
嘉靖看着他:“江南织造局闹成这样,宫内尚衣监、针工局、巾帽局那么多奴才贪了多少银子,只差没来玉熙宫拆瓦了。这可都是你管的人。朕也只让你去了半个月永陵,你还觉着这么委屈?”
吕芳抬起了头,满脸的泪,哽咽道:“奴才哪有什么委屈……九州万方都在主子一个人的肩上,护着这个,还要护着那个,主子才是最委屈的……”
嘉靖叹了一声:“当家三年狗都嫌哪!宫里的家朕一直交给你在当,有些事你也是在代朕受过。浙江重审郑泌昌、何茂才的供词昨天送进宫了。朕原本不想拆看,踏了一卦,竟得了个乾卦,‘元亨利贞’,上上大吉。供词就在案上,你也去看看吧。”
“是。”吕芳听他如此一说便以为浙江的供词一定是按照司礼监内阁的意思改好了呈上来的,心中一宽,拿衣袖揩了泪,站了起来。
嘉靖从宽大的袍袖里掏出了自己御用的一副眼镜递了过去,吕芳连忙躬腰双手接了过来,向御案前走去。
走到御案前,发现御案上依序摆着一张张供状,都用玉石镇纸压着,供状上有些字大有些字小,密密麻麻,他将嘉靖那副御用的眼镜先举过头顶虚空拜了一下,这才戴上,向那些供状仔细看去。
一眼便发现原来打回去的那份供状竟赫然摆在首位!吕芳立时愣了,不禁向嘉靖悄然望去。
嘉靖:“看,看了再说。”
吕芳连忙飞快地一路扫看过去,确认那份打回去又呈回来的供状一字未改,目光立刻跳过去看后面的供状。
嘉靖已经从蒲团上下来了,开始独自在精舍里徘徊起来:“百姓家有一句常说的话,帮忙帮忙越帮越忙。第一次递来的供词你不呈给朕看,瞒着朕跑去找严嵩找徐阶,还捧上一坛四十年的陈酿去劝酒。一个首辅,一个次辅,一个井水,一个河水,这杯酒也是你能劝得的(音di)!不用忙着跪,接着看完。”
吕芳听得心惊,本来想跪下解释几句,听嘉靖一说,只得又戴上了眼镜,弯腰向后面的证词一行行看去。
嘉靖绕着蒲团那三级坐台,脚踏八卦走了起来:“当时听到你去劝酒,朕就想起了太祖高皇帝宴饮功臣时说的两句话……知道太祖爷当时说的是两句什么话吗?”
一边耳听雷声隆隆,一边眼观刀笔攒攒,吕芳已然满脸是汗,不看完也已知道是什么内容了。听嘉靖这时突然提起了太祖高皇帝,他便不能再看又不能取下眼镜就此不看,只能侧身站在案边低头接言:“奴才不知道,请主子赐教。”
嘉靖停了脚步:“你不知道,可严嵩和徐阶知道。两个大学士,《太祖实录》他们不知已经读了多少遍,都烂熟在肚子里了。端起酒杯的时候,他们早就想起了太祖那两句话。”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然后一字一顿地念出了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当时宴饮功臣的那两句话:“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这句话用在明朝历史上太恰当了。
刚才嘉靖的话还是雷声,这两句太祖的话简直就是霹雳!吕芳慌忙取下眼镜搁在案上,扑通一下在御案的侧边面对嘉靖跪倒了,把头紧紧地趴在砖地上。
嘉靖:“有些家你能替朕当,有些家朕交给了严嵩和徐阶去当,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美酒在前,白刃在后,他们能不想法子对付吗?”
吕芳连磕了三个头又趴在地上不再答话。
嘉靖:“倭寇在东南闹,鞑靼在北边闹,国库又是空的。现在你打回去的供状不但一字未改送了回来,还添上了郑泌昌、何茂才翻供的供词,又添上了对付翻供的另一些供词和证言。毁堤淹田,私放倭寇,贪墨国帑民财,都翻出来了!有辜的无辜的牵涉那么多人,你叫朕这个时候拔出了白刃杀谁是好?”
吕芳只能重重地又磕了个头:“奴才无知,犯了大忌,闯了大祸,甘伏圣诛!”
嘉靖这时已在御案边,信手拈起他画的那张乾卦和写有卦词的御笺轻轻一扔——飘在吕芳面前:“跟朕这么多年了,你也懂得卦爻,参祥一下,这个乾卦什么意思。”
吕芳慢慢捧起那张御笺,跪在那里想了想,答道:“奴才想既是‘元亨利贞’,便含着‘以贞而利’的意思。这是说主子圣明,用了胡汝贞和赵贞吉便无往不利。东南的事有二贞在能够稳住。”
嘉靖:“这层意思谁也能看得出来。可两个乾卦,乾下乾上又做何解?”
吕芳的目光又定定地望向嘉靖画在御笺上的那上三横和下三横,冥想着答道:“这是极阳之象。乾上自然指的是主子,乾下指的什么,奴才便参祥不透了。”
嘉靖:“你们要都能参详得透,朕也就枉称了飞元真君。这个乾下指的是海瑞!”
吕芳一愣,睁大了眼望着嘉靖。
嘉靖眼睛望向精舍门外将落的月亮:“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竟有如此霹雳手段,可见是个至阳至刚之人。都说朕那个儿子孱弱敦厚,其实也还知人善任。”
吕芳做恍然状:“主子圣明。”
嘉靖:“这个海瑞是要杀人的,但朕现在还不能杀人。除了郑泌昌、何茂才,还有尚衣监、针工局、巾帽局三个为首的奴才,其他的人,这一次朕一个不杀,也一个不抓。这个旨意要立刻传知严嵩和徐阶,叫他们清晨进宫。”
吕芳:“奴才这就去传旨。”
嘉靖:“你不要去,让陈洪他们去。天也快亮了,你收拾一下去司礼监,半个月不在,那里已经一团乱麻了。”
“内阁的云,宫里的风”。这是嘉靖时京师官场无不通晓的两句谚谣。做官欲升迁,必须内阁那片云下雨,至于那片云最终能罩在谁的头上还要看宫里的风把云吹到哪里,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再机密的事片刻之间宫里就会传出风来,此风所到之处,谁观知了风向便能趋利避凶。
半月前吕芳发去守永陵,风吹草偃都倒向了陈洪一边。今夜吕芳被密诏回宫,不到半个时辰这个消息立刻从玉熙宫先吹到了司礼监,东方未白这里已然是晓风浩荡了。
就是在这一年,大奸臣严嵩被强令致仕(退休),严世蕃先是发配边疆,后又以通倭罪被杀。严嵩的家产被抄,搜出大量金银珠宝,但这些仅为他全部的十分之三四而已。
严嵩独揽大权20年,他溺爱信任恶子,臭名昭著,人们都将他成为奸臣。看来这个教育问题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慎之又慎,现在看看一些大明星把子女教育成“流氓”、“无赖”,品行低劣,无不与教育有关系啊!
回到题目,为什么嘉靖皇帝让吕芳去守灵呢?其实上面文章给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嘉靖皇帝想给吕芳一个教训,让他知道他上面有一片天,那就是皇帝!嘉靖皇帝还是很看好吕芳并且非常信任他,以至于让他去守灵15天后又把他召了回来。
一个太监就敢把下面朝政随意扣发、篡改!太监当政,这也是明朝最后败亡的主要原因。
嘉靖皇帝作为历史上一个奇葩的存在,潜心修道,妄求长生不老,置朝政于不顾,二十多年不回大内,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可谓独树一帜,前所未有,虽然他的年龄在帝王中也算是长寿了,可要不是长期服用丹药,应该更好。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让吕方去守灵?
谢邀:
因为吕方瞒着嘉靖私自参与朝政,
也是想保护吕方让他可以安度晚年。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为什么让吕方去守灵?
在《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的确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把权力交给裕王,但在没有交出之前,他自己要玩个够。所以他一方面给裕王配备了三个老师:徐阶,高拱,张居正,并让他们进入内阁。另一方面有一套完全听任自己安排的系统,由严嵩、严世蕃、罗龙文、鄢懋卿组成,两个文臣集团形成矛盾的双方,既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从而让裕王在复杂的斗争中,观察官员并学习国家管理。另外,他还有一套监控所有人的特务系统,这就是司礼监和它统领导的锦衣卫,如陈洪、朱七、齐大柱等。
当他发现吕芳私下约严嵩、徐阶密谋,瞒着他直接处理浙江的贪墨大案,非常恼火,一气之下,便把这个跟了自己四十年的太监总管发配去永陵监修“万年吉壤”。他既不喜欢手下的人给自己留后路,也厌恶手下的人首鼠两端,勾打连环,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控制力,尤其是太监。这人够阴,够狠!把吕芳外派的同时,嘉靖让严嵩回家养病,由徐阶搬进内阁值房当班,而自己呢?又突然宣布闭关。三个元老一夜之间散伙了!大明朝这架巨大的机器似乎突然停止了运转。嘉靖要用变来观其动,而自己却以静制动。
半个月后,吕芳被叫回来了。嘉靖对吕芳的惩戒是很起作用的,而且后来证明了嘉靖的判断是多么地正确。
吕芳瞒着嘉靖,让严嵩徐阶派人打回去的那份供状,竟然又送回到嘉靖的桌案上。吕芳知道出事了。嘉靖这时候才对吕芳说:“百姓家有一句常说的话,帮忙帮忙越帮越忙。第一次递来的供词你不呈给朕看,瞒着朕跑去找严嵩找徐阶,还捧上一坛四十年的陈酿去劝酒,一个首辅,一个次辅,一个井水,一个河水,这杯酒也是你劝得了的!有些家你能替朕当,有些朕给了严嵩和徐阶当,可大明朝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你去劝酒,他们必然猜想是朕的意思。美酒在前,白刃在后,他们能不想法对付吗?”嘉靖还告诉吕芳,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当年宴请功臣时说的那句话“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而这两句话就在太祖实录里面,像严嵩、徐阶这样的大学士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都烂在肚子里了,你去劝酒,这不是坏事吗?”
惩罚吕芳半个月后,嘉靖之所以要派黄锦秘密请回了吕芳,因为到了真正要动严党的时候。要动严党,嘉靖对陈洪是不放心的。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