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里沈一石怎么做才能免于一死?
古往今来,白手套命运不过是夜壶,夜壶这东西,需要时非他不可,不需要时臭不可闻。
需要不需要都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价值体现。在改稻为桑这件事上,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这个事情,谁才是具体执行者?
首先:肯定不是嘉靖,他才不会管这具体的事情,其次不是严阁老,他最主要做的事情是填青词讨好皇帝,再次不会是浙江官场,主事的地方大员胡宗宪内心是反对急功近利的改稻为桑,在他看来,这是祸乱之道。
那么谁才是这件事最大推动者答案一:太监杨金水杨金水看上去是好人,可他最急迫,皇帝没钱啊,家奴要为主分忧,他代表干爹吕方意思,干爹吕方代表嘉靖,不知道多少夜晚,嘉靖在为钱发愁,为主分忧是家奴太监分内事。
答案二:严世蕃及其利益集团这里把严嵩排除,因为严嵩明白下面人心思,对钱财他看的很淡,作为严党领袖,最主要事不是做事,而是稳皇帝。只要皇帝信任,严党就能继续活,可他也被裹挟,裹挟这词有深意,他不希望做太过分,可他无力控制,因为肥肉太诱人,他儿子和那群人太贪婪。人心失控,而要挽回人心,他必须默许,因为亏空要补,钱要捞。
答案三:裕王党和所谓清流裕王党和所谓清流是好人吗?我看不见得,嘉靖话很贴切“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所谓清流也好,严党也好,本质一样,只不过一个有底线,一个没底线。可恰恰是有底线清流,做了没底线事情,他们违背底线默认毁提淹田,用无数百姓生命换党争筹码,脸是好东西可这些正人君子也没有。
看清楚这件事情所有推动者后,我们在看沈一石脸色!沈一石是谁的人?这问题值得研究,明面上他是严党,可他和太监杨金水关系很好,最后还把芸娘托付杨金水,那么他也有可能是嘉靖人,可他不能说,那他角色如何定位?
二面派?说是也是,不是也不是,他只是个在皇帝贪欲和官员贪欲间生存的人,是严党和皇帝共同白手套。这就决定他结局,不得好死,不过他看人还比较准,相对严党那群忘恩负义读书人,他托付并保全的杨金水没背叛他。这算他唯一幸运。
他必须死是为何,不看清来龙去脉是说不清的,必须理清逻辑。事情起点是财政亏空,必须进行改稻为桑,扩大丝绸出口,填补亏空,可这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其实谁都清楚,也都知道改稻为桑一年绝对搞不成,非要干,最坏结果就是浙江百姓造反,倭寇乘机进攻,明朝乱的一逼。这是客观事实。
于是胡宗宪坚决反对,可严党支持啊,原因简单,他们认为无人阻挡,因为胡宗宪和浙江官员全是严党。无非因为利益,嘉靖规定,桑田按农田征税,是啥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借改稻为桑,吞百姓田,做自己生意,自己产丝,卖自己,税还交的少,而这产丝,买丝代理人都是沈一石。
可老百姓不傻,他们不愿改,怎么办只能逼,于是斗争开始。而裕王和清流,决心在改稻为桑上与严党作对,于是他们派谭纶到浙江。谭纶到浙江了解情况后,发现胡宗宪也不想改,可他们派别不一样,这让他很诧异,难道严党有好人?而严党很愤怒,认为胡宗宪背叛严党投靠清流,严世蕃于是直接下令郑泌昌何茂才,瞒着胡宗宪,趁端午涨潮,将浙江杭州九县全淹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百姓何辜?这就是毁堤淹田,毁堤后,胡宗宪无奈只能分洪,淹了淳安县建德县,保全其他几个县。毁堤淹田这事情,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都知道,他们怕担责任于是想将这件事报成天灾,妄图用杭州知府马宁远,淳安县令常伯熙,建德县令张知良,等这些小角色顶罪。可胡宗宪不干了啊,他从马宁远嘴里问出所有真相,原来是严世蕃下令、郑泌昌,何茂才主使,杨金水也默认了。
于是胡宗宪用这份口供,胁迫杨金水和郑何二人一起同他上书朝廷。上书内容:被淹是因为河堤失修,引发浙江洪水,百姓疾苦,望朝廷借粮百姓,让百姓继续种田,三年内不改稻为桑。
目的如胡宗宪所愿不在继续改稻为桑。上书结果,嘉靖令胡宗宪、杨金水和谭纶进京。因为严世蕃逼迫,连夜赶来的胡宗宪没见到严嵩,也没有将原因对严嵩说透。最后胡宗宪还被免去浙江巡抚官职,任浙直总督,从实际上来看,胡宗宪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不能插手浙江地方事务。
原因很简单,嘉靖需要改稻为桑继续,但方式要变,而有个人出现让他觉得可一试。这人就是高翰文翰林,饱读诗书,提出“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因为是严世蕃提拔起来的。于是严世蕃派他去,皇帝也同意,既然提这主意,你就去落实吧,另一方面,严世蕃知道改稻为桑这事容易让百姓造反,百姓造反,高翰文人头还可以顶罪(他就更安全)
高翰文还没到浙江,就被胡宗宪截住,胡宗宪将浙江官场贱买百姓土地事一说,高翰文这个愤青当即表态,不坑百姓。
于是当高翰文与海瑞王用汲到浙江后,郑泌昌何茂才难办了,他俩想高翰文过来帮自己,谁知他和海瑞、王用汲居然是一伙的。
因为高瀚文态度,桑他们会错意思,觉得严世蕃派高翰文来目的,是要他们既改稻为桑,又安抚百姓,着高瀚文是过来居中调和的。
居中政策意味着要更多钱,可问题更难办,钱不够啊,沈一石没那么多钱买粮买田。好了下面开始是重点。嘉靖调回杨金水后杨金水就不露面,而是被保护起来,杨金水不露面,用意是出问题让郑泌昌何茂才顶罪。官员有错不会影响皇帝威望,而太监有罪,皇帝难辞其咎。可严世蕃不同意啊,严世蕃替罪羊另有其人,那就是高翰文。
这时候郑泌昌,何茂才也有小心思,他们怕自己被替罪,也在想办法,他们把目光瞄准办事的沈一石。郑何理解是:改稻为桑,并且安抚百姓不造反,这样要求,事情没法做啊,钱不够,时间不够,必然失败,改稻为桑失败,严党和织造局,会拿他俩顶缸。如果改稻为桑成功,百姓造反了,严党和织造局还是会拿他俩顶缸。
二个方向都有问题,事情又不能不做,怎么办?于是他们只能找软柿子捏。所以他们才会要求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灯笼去买田,沈一石没办法啊,他是白手套而郑泌昌,何茂才也是他上级,他必须听话。
郑泌昌,何茂才心思无非是彻底把水搅浑,把所有人拉下水,打着织造局灯笼买田,意思完全不同,君父居然用官方名义贱买百姓田地,嘉靖知道了,谁也逃不了,不管严党也好,清流也好,吕方也好。
牵扯这么多人,郑泌昌何茂才,反而安全了,因为他们个子不够高。就算不安全也法不责众!那么沈一石怎么想的,其实他很无奈,这个事情有他原因,是他提出买田可是他没想过用纸造局名义,但郑泌昌何茂才太坑爹,居然想用纸造局名义做,这不是嫌死的不够快吗。
郑泌昌何茂才让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灯笼买田,而沈一石却打着织造局灯笼去赈灾,“打织造局牌子买田”是郑泌昌何茂才下的险棋,目的是保全自己,拖更多人下水。沈一石看出来了,不过沈一石认为“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买田”这主意是严嵩严世蕃他们出的,目的是将清流给他们的压力,转嫁到织造局,因为船对岸接受救济的百姓是海瑞治下,淳安县百姓。如果海瑞因为百姓问题,开了口子卖田,那么清流就会被拖下水。
沈一石面对如此局面,不得不去,那么如何化解这场嫁祸,只能见机行事,和海瑞见面后,他看海瑞态度决定行事方式,看到海瑞态度坚决站百姓这边,于是将灯笼底下暗藏的“奉旨赈灾”拿出来,把买田变赈灾。替皇帝安抚灾民。
那么他如此费尽心机,能活吗?能吧自己摘出来吗?答案是不能!沈一石在这关口,无论如何活不了。原因何在,其实在他最后遗书中已经说的明明白白“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
”改稻为桑改不成,再改百姓就造反,而国库没有钱等不了,怎么办?只能杀他这个大商人,拿他钱补亏空,接济国家。
那么他做将买田变赈灾真的一点好处也没吗?其实也不是因为他给自己的爱人留了条后路“织造局”是杨金水主管,如果打着皇帝名义贱买土地,皇帝肯定愤怒,沈一石没这么做就是保护杨金水,保护杨金水就等于保护芸娘。
这沈一石也是至情至性好男儿,知道必死无疑,还能为爱人朋友想。让芸娘跟个好人,远离是非。沈一石死了,沈一石就这样死了,因为他面对必死之局,这局是如何产生的?其实他的命运是和改稻为桑结合在一起的,而改稻为桑目的无非是钱,之前改是为了钱,之后改不成也是为了钱,可是还是没钱怎么办?只能拿有钱人开刀,这就是他作为白手套的宿命。
那么问题已经回答完了,后续其实还有很多因果,有兴趣可以继续看。无论“织造局买田”因谁而起,各方势力如何看待,他都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严嵩已经不能控制严党,他已经被严党裹挟了。就连严世蕃也控制不了地方。
因为郑泌昌何茂才擅自做主,用织造局名义买田就是证据。这就让嘉靖开始害怕了,刀子开始钝了,切肉不方便了,是不是该换吧刀?或者磨下刀?
其实这件事才是真正意义上倒严开始,嘉靖对严党不满,才有后来嘉靖责问严嵩严世蕃: 朕是天子,也是万民君父。现在朕拿着钱去贱买子民田地。朕要是这样的天子,天厌之。朕要真是这样的君父,万民弃之。
嘉靖这番话重点在哪?重点在君父拿钱买田玷污嘉靖圣名,言外之意是,这都是你下面人做的好事。太不像话了,而其实归根结底,不过是嘉靖只关心自己名声,而不关心自己百姓!
何以见得,毁堤淹田时,胡宗宪上报河堤失修,朝堂以为嘉靖不知真相,其实嘉靖知道,吕芳就跟杨金水说: “你什么事儿都没瞒我,我自然什么事儿都不瞒皇上,毁堤淹田皇上都知道,你去把详情跟皇上详细说说。 ”你为宫里好,难得你不隐瞒,这便是最大的忠。一两个县,不算什么,皇上装的是九州万方。
毁堤淹田,百姓不光丢地,还丢命,嘉靖责难严世蕃了么? 没有。嘉靖后来态度是, 一两银子,十二钱归国库,四钱归他们,朕认了;十钱归国库,六钱归他们,朕也认了。要是他们还想多捞,容不下胡宗宪,逼反东南,朕就不容他们。 这就是他的态度。只要保证胡宗宪打仗有钱,保证东南不反,保证嘉靖自己有钱花,贪污不算什么,盘剥百姓不算什么!
可打着织造局牌子买田,玷污圣名,就万万不能容,忍不了怎么办,你们统统给我去死!这就是嘉靖的态度,那么一个白手套的沈一石在嘉靖哪里看来,又算的了什么?不过是一个夜壶而已。最可笑的是, 被炒家的沈一石,最后家产不明不白,都不知道去哪里啦,大部分也许还是进啦严党的口袋,嘉靖不怒才怪。所以严党末日也来了,可是上台的清流就是好人吗??
“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所谓清流也好,严党也好,本质一样,只不过一个有底线,一个没底线,本质没区别,这就是明朝的症结所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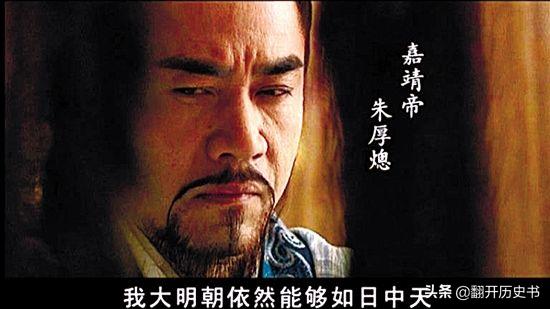
大明王朝1566里沈一石怎么做才能免于一死?
这么说吧,他怎么做都是死!
决定他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跟官员勾结,比如陷害高翰文,比如生活奢侈等等。但是今天我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出自谭纶跟海瑞的对话中,通过这次对话,一清二楚,沈一石必死无疑。
这件事还得从李时珍到淳安时说起:
一、
李时珍到达淳安县,在没有跟海瑞见面的情况下,就一个人去了县衙大院,在那里他遇到了王牢头。
这一段剧情不是什么重点,我们简单地一带而过……
大体表现的就是王牢头的飞扬跋扈,把李时珍误以为是灾民,更对李时珍把他辛苦熬的汤药倒掉而耿耿于怀。面对衙役的拉架,王牢头仍然不放过李时珍,一心要把他拉到里面去,正在这时,海瑞跟谭纶来了,王牢头先告状:
“有句话太尊说得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对他们越好,他们越不知好歹,就这刁民,您看见没有,他居然把您施的药给泼了。”
貌似大老粗的王牢头,拽出了一句名言,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篇》。
其实学术界一直对这句话有争议,这句话按照王牢头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王牢头还是相当厉害的,还会引章据典,还会转移矛盾,把自己跟李时珍的矛盾,硬往海瑞身上引,不愧是牢头,也会扣帽子。同时也揭开一个谜题,那就是当初徐千户和蒋千户让王牢头签字的时候,他说自己不会写字?
海瑞此时已经看出来这个人是李时珍了,也回他一句:
“以后再拿什么圣人的话瞎说,自己掌嘴!”
回到刚才《论语》的那句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断句这样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
二、
训了王牢头一顿后,李时珍算是跟海瑞正式见面了,与当初在江苏见赵贞吉一样,李时珍也不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太医。海瑞比赵贞吉爽快,立马就称呼李先生,还让李时珍称呼自己为刚峰。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看出海瑞的胆子之大,李时珍批评他药方开错了:
“凭一本千金方,你就敢给这么多人熬药治病?”
接待完了李时珍,谭纶和海瑞回到了县衙,他们这段对话,对后面剧情的发展做足了铺垫。
听说谭纶马上就要走,海瑞有点疑惑,谭纶这才告诉了海瑞急着走的真相:
因为此时的老百姓已经改种了桑苗,但是严党吞并百姓土地的计划泡汤,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仍然没有补足,因此,朝中自然有人要为此事担责。
在海瑞看来,他以为是严党担责,所以他回了一句:
“严党误国误民二十年,也该是要倒台的时候了!”
结果谭纶直接打断了他的说法,告诉他,严党目前还倒不了台!
之所以倒不了台,就是因为沿海的倭寇蠢蠢欲动,东南即将有战事发生,一旦发生战事,国库空虚,皇上更是着急,必然会指望严党弄钱。严党要想弄钱,自然冲有钱的人开刀,这个刽子手自然没人愿意当,这也是嘉靖帝不会让严党马上倒台的原因。
与此同时,谁会第一个遭殃呢?
“据胡部堂分析,眼下有巨财能填补国库空虚的,只有一个人,沈一石。”
三、
谭纶离开胡部堂身边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沈一石是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买粮。与此同时,海瑞的生死未卜,改稻为桑的国策到底往哪走尚不明确。
但是不管形势怎么走,沈一石都很难脱身,这跟他“赈灾”不“赈灾”无关!
海瑞并没有想通为什么会这样,而是问了一句:
“沈一石是织造局的人,他们敢动?”
在海瑞的眼中,织造局是宫里的,也就是皇上的,严党再大胆,也不能打织造局的主意啊?
其实他是被沈一石那身六品官服给蒙蔽了,以为沈一石真的是织造局的人,其实不然:
“现在百姓的田地贱卖不了了,朝廷就只好抄他的家来填补亏空……那么多的作坊也就顺理成章归了织造局,这样的结果皇上也会同意。”
听完谭纶的解释,相信大家的心情都比较低落,海瑞同样低落。是啊,明朝的商人命运却是悲惨,世道好的时候,商人就是朝廷的打工仔,生产工具,给朝廷创造财富。世道不好的时候,朝廷就宰了这个商人,吃他的肉,也能撑一阵子。
海瑞还是没搞明白,沈一石这次可是自掏腰包替朝廷赈灾啊:
“抄他的家,未免不近天理,也有违律法啊!”
海瑞思考问题还是比较全面的,抄沈一石的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尤其是于理上,毕竟海瑞熟读大明律法,前面几次脱险,也是凭借这大明律法才脱身的,为什么对待沈一石就不能按照律法来呢?
四、
谭纶再次刷新了海瑞的三观:
他指出,之所以沈一石临时改变主意,不再低价买田,而改成了“奉旨赈灾”,他就是看出来上面有裕王在反对,下面有海瑞在反对,最后没办法,想通过散掉家财,给嘉靖帝买面子,买人心,以图换自己一条生路。
其实他的主意算盘打错了:
“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现在百姓保住了,他,焉能自保?”
其实谭纶说的这句话,跟前面严嵩说过的“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天”意思相同,看来这种事情,在大明的高官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不仅仅他们看出来了,沈一石当天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毕竟红顶商人,再高贵,也不过是商人,也不过是朝廷嘴中的肥肉罢了,高贵不到哪去!
海瑞还不死心,即使你们想抄沈一石的家,总得给人家一个罪名吧?
“罪名还不容易,就拿他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招牌,买粮赈灾,朝廷就能给他安上一条,商人乱政的罪名。”
沈一石虽然有一身六品的官服,但是那是朝廷不认可的,是宫里的太监给他的,说到底,他还是商人,怎么做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况且在朝廷面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海瑞突然站起来拍了一下柱子:
“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朝廷挥霍无度,官场贪墨横行,可到了这时候却弄成如此结果,可见立国不正,大明朝再不整治,亡国有日!”
幸亏他说的这句话是对谭纶说的,换个别人,早就死了一百遍了,国事岂是你一个小小的知县能妄议的?
其实这句话,海瑞已经透露大明朝的问题所在,一是朝廷挥霍无度,其实就是指嘉靖帝挥霍无度。官场贪墨横行,其实就是说严党等人,后来严党被打败,海瑞就针对第一件事跟嘉靖帝怼起来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只是对于沈一石来讲,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了,所以说,在大明朝,安安稳稳做个小老百姓最好,当什么首富,当什么官啊?
我叫杨角风,换种视角看大明王朝,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乐趣,原创文章,喜欢就关注吧!
大明王朝1566里沈一石怎么做才能免于一死?
答:无论如何活不了。
《大明王朝1566》里的人设,其实只是借用了明朝的皮,里面的官场、商界的运行逻辑,其实是当今的,而不是明朝式的。
真实的明朝式的政商关系,哪怕是杨金水这样的中级宦官,连二十四衙门的主官都不是的角色,也不会承认沈一石这样的商人是自己的“搭档”(与锦衣卫交谈时所说),而是将之视为奴仆和肥羊。
在明代,商人的地位,其实被今天的很多“明粉”刻意拔高了,混淆了“绅商家族”和商人阶层的区别,比如说东林党代表江南工商阶层的利益等等。
事实上,明代社会地位高的,唯有“绅”,商,只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而非他们的正式社会角色。
所谓“绅”,要感谢明太祖对于科举读书人身份的固定和相应特权的保证,正是这一系列的特权,让“士绅”,比如有功名在身的在乡绅士,或是退职的科举官员,利用他们的官场关系和士林舆论,形成一个独立于朝廷法度之外的“潜规则社会”。
这个“潜规则社会”衍生出来的特权,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收纳民户为家仆,并接受他们田产的投献,免去附着于民户身份之上的赋税、差役,同时,也可以肆无忌惮地为行商的货物保驾护航,一路免除税关的正常税收和敲诈勒索。
在此条件下,商人与士绅的合作,乃至于官员的合作,本质上就是民户的“投献”,只是没有合法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能保证自身财产的一定独立性,但也仅此而已。
一个士绅,甚至地方的胥吏,想要整死一个没有后台的商人家族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比如派差采买的“役”,只需要在审核货物时稍做手脚,则商人家族哪怕家财万贯,也很快会被敲骨吸髓,甚至家破人亡,子女抵账。
所以,要想避免这样的命运,明朝的商人越大,越要寻找后台,而后台又有周期性的垮台,也就会出现周期性的“财富重新分配”,毕竟新来的官员“还饿着”。
而沈一石这样的具有独立人格和理想的商人角色,在大明朝的200多年间都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他所谓的“为国办事”,实际上是今天某些“白手套”的内心独白。
毕竟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理想就成为支撑个人继续下去的唯一动力,如果不能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解释,所有的一切都会化为虚无,事实上,沈一石最后的赴死,就带有理想破灭,终于认清污浊现实的成分。
而《大明王朝1566》实际上将这种现实无比的残酷政治斗争给浪漫化了,形成了相对脸谱化的善恶对决,事实上,白手套们的倒台,乃至于大明朝的商人家族的覆灭,往往没有那么多的善恶有报,只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罢了。
事实上,整个电视剧恰恰展示的是这个“换”的大时代,也就意味着原本的大船开始沉没,跳不到新船上的人物,只能通过减轻旧船的负重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也就意味着要把一个个“不重要”的人物踹下船去。
这个进程,如果你仔细看看《大明王朝1566》就能品味出来,一步步踹到严嵩,踹到吕芳、陈洪,最终踹到嘉靖本人……
沈一石这种小人物,当然是最早被踹下水的,否则呢?
难道让大人物先走?
大明王朝1566里沈一石怎么做才能免于一死?
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名义去买田,后来成了赈灾,当旗挂上,船开出去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定了,没有谁能救了他,也没有谁会救他。1、严嵩的定性
沈一石是江南首富,势力也是盘根错节。仅仅地方官想杀他,还是比较难的。但朝廷里定了调调,那就没救了。
严阁老在和严世蕃聊天中就说:要让商人高价买地,如果不花这价钱,官府就弹压。历来只有耕田的造反,还没有造反的商人。
(造反约束是朝廷的一个决策点)
显然严首辅对商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用则用之,弃则弃之。在后来沈一石的问题上,皇帝和首辅的态度也是一致的。毕竟沈一石只是江南的男男女女羡慕他,在整个序列中,沈一石的权重只是比马宁远高,何茂才、郑泌昌、杨金水、胡宗宪、小阁老这些权重都是加大的。
2、胡宗宪的想法历来国家财政亏空了,要么取于民,要么取于商。
严格的说,这并不准确,三五灭佛,就是取于佛;李自成追脏就是取于官。这是很少见的历史时候,更多就是上面的两种。而且在和平时期,基本取于商。
财政亏空,沈一石本身就是给皇家做事的商人,加上犯了错误,再加上都以为他有钱。然后就是这样子了。
没人救得了他,如果他壮士断腕,早一点切割开西洋贸易,不要卷入这样的事情中,或许会好一点。
在古代的商人,要么识大势,在合适的时候做切割,该隔开都隔开,或许能继续富贵。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窗口,那就只有交给概率论了。
欢迎关注、点赞、吐槽,我是一枚明粉,给你不一样的史学评析,期待你的评论,期待你的分享大明王朝1566里沈一石怎么做才能免于一死?
沈一石怎么做都难免一死。且听我仔细分析:
第一,沈一石是什么人?他是个商人。
不要看现在的人做生意当老板很风光。在古代,民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是地位最低的。因为商人不能直接生产财富,所以古代中国政府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看不起商人。
明朝特别地看不起商人,因为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不懂商人的价值。朱元璋规定,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只能穿粗布衣服。所以剧中沈一石总是一身布衣,还只喝凉水。
沈一石还不是普通商人,他是官商、皇商,是替皇上做生意的商人。虽然看上去靠着宫里的大树,很风光,但是其中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赚了钱,那是皇上的,宫里太监和严党也要分成。赔了钱,那是自己的,没人给他兜着。
所以沈一石表面上看很有钱,但实际家底早被大小官员、太监掏空了。
第二,改稻为桑注定是步死棋。
为什么?
皇上批准改稻为桑是为了填国库的亏空,严党提出改稻为桑则是为了自己捞一笔。
本来,如果让农民自己改,说不定能改成,严党从中可以小捞一笔。这是皇上吃肉,严党喝汤。
但是严党胃口很大,想借着改稻为桑兼并土地。这是严党吃肉,皇上喝汤。
于是严党想出了毁堤淹田的缺德主意,裕王党当然不能容忍,必定拼死抵抗。两党相争,改稻为桑就搞不下去了。
这就等于是,严党为了吃肉,不小心把锅砸了。皇上等着吃肉,结果连汤也没得喝。
你说皇上气不气?皇上一生气,严党必须找替罪羊。这时候沈一石不死谁死?
第三,跟严党合伙做生意,那就是跟魔鬼交易。郑泌昌、何茂才是两个政治婊子,他们的主人严世蕃,又会是什么样的人?
你想,他们为了吃肉,能干出毁堤淹田的事情来,置几十万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他们还会在乎沈一石这么一个小小的商人?就像剧中所说,从来只有农民造反,没听说过商人敢造反的。
严党打百姓的主意,裕王一派,特别是海瑞,肯定会斗争到底。但是严党打沈一石这个商人的主意,其他官员只会袖手旁观。
因为商人的政治地位太低贱了,在古代中国这么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商人的价值。
所以沈一石从一开始就是在钢丝上舞蹈,终于坠入了悬崖。
大明王朝1566里沈一石怎么做才能免于一死?
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大家一定都看过了,实话实说:这部剧拍得很好,有好多事情都讲透了。估计未来这样的电视剧会越来越少了,没办法,环境变了,有些东西就要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了。
这部剧里面的人物有很多、很多,但是总结一下无非这几类人:代表皇权的嘉靖、代表官员也就是官僚系统的严嵩、徐阶、代表清流的海瑞、代表监权的吕方、最后一个就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沈一石。
这部剧的最大看点就是——斗争的艺术了。嘉靖和大臣斗、太监和皇帝斗、太监和大臣斗、大臣之间斗。
其实斗来斗去无非都是为了:权力而已。徐阶和严嵩是为了争夺首辅之位、吕方和陈洪斗是为了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嘉靖与他们斗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权力。
当然本剧中有一个小人物很有意思,这个人就是:江南织造局业务的承包商、丝绸商人沈一石了。这哥们的工作很简单:承包官府的业务,帮着江南织造局来织丝绸。
江南织造局的主要业务原来是供应皇宫里面:皇帝、后妃以及一些皇亲国戚的衣服的。不过后来嘉靖帝由于财政吃紧,又要江南织造局把丝绸织好卖给外商赚钱。
不过沈一石还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平时还是要伪装一下的,例如:表面上穿的不好、吃的不好……
沈一石最后的结果是:死了,死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被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给无情地抛弃了。
我们一起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沈一石死亡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二是,沈一石怎么做才能不死呢?
沈一石的角色定位其实早就有了——“夜壶”是也前面说过了,沈一石只是江南织造局的承包商而已。不过后来有了钱了、有了关系之后,拿钱买了个官而已,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红顶商人了。
明朝的时候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当时的排名是:士农工商,商人那是属于比较靠后的一种职业了。这种排名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商人意味着狡猾、意味着流动、这是严重不利于统治者们的大位稳固的。
沈一石的所作所为就不用我多分析了,看过电视剧的应该都知道了。沈商人无非就是:赚点差价、贿赂点官员、然后利用自己的钱买个官帽、凭着有利的身份继续赚钱而已。
我们来从本质上分析一下:为什么沈一石必须死呢?
1、沈一石在嘉靖的眼里、在官僚系统的眼里、在太监集团的眼里、在整个古代社会的眼里:那都是一个不入流的角色而已。领导用你的时候,你就是钱袋子、不用你的时候,那就是毫无用处的垃圾了。
没办法,沈一石是借权生的财,只要有权力这活谁都能干,无非是换个人而已。
2、当时贪腐案件已经暴露了,郑必昌与何冒才都要被抓了。此时的沈一石手里还搞了一个账册,里面牵扯的官员有点多,那还不赶紧灭了口再说。
3、当整个案发以后,都知道沈一石是为江南织造局办事的、江南织造局又是为宫里办事的,这就直接指向了嘉靖帝本人了。不好意思,古代皇帝是不可能有问题的,有问题也是低下人的问题,那么沈一石的背景和实力最差,于是乎,那就最先死呗!
4、沈一石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败坏了嘉靖帝的名声。古代皇帝要维护其统治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对外号称是:爱民如子的。当然口号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意思都差不多。
可是淳安县遭受了“灾情”之后,沈一石居然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低价购买田地,这简直就是打嘉靖脸的举动了。虽然后来他改成了免费救灾,不过已经弄巧成拙了。
总之一句话,沈一石只不过是个“夜壶”而已,他又是记录官员的贪腐情况、又是乱打嘉靖的旗号。最终的结局那就很简单了:沈一石不死、谁死呢?
那么沈一石怎么样才能不死呢?我仔细想了很久,沈一石要是想不死的话,这办法实在是太少了。他得罪了官僚集团、得罪了嘉靖帝,自己又没啥后台,裕王根本又不可能出来保他。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沈一石要想不死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思考人,我就有两招能保证沈一石不死:
第一招:未雨绸缪法
这一招后来有很多人用,不过那时候用的人估计比较少。这招的办法是:提前转移资产、提前把老婆孩子转移走,然后自己再跑出去。
不过当时是大明朝,这招有点难度。当时是嘉靖40年左右,也就是:公元1561年的时候。此时的欧洲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夜,所以我觉得沈一石要是提前往欧洲跑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招:找到嘉靖的命门、一击必中
电视剧中有一个桥段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那就是:齐大柱已经被判了死刑了。可是齐大柱的老婆以及裕王一派不甘心,于是乎想了一个绝招:向嘉靖帝贡献了一本张三丰的血经书。这样一来,齐大柱就把命给保住了。
嘉靖帝当时最大的梦想不是钱、也不是大明朝多厉害,而是练成长生不老之术而已。假如沈一石能够找到一本书,帮助嘉靖帝实现这个愿望或者暂时慰藉一下嘉靖帝的心理需求,例如:太上老君之书、秦始皇长生不老秘术等等。
我想嘉靖帝一定不会杀掉沈一石的,因为这是上天派来的祥瑞、派来的使者,也很能从侧面证明:嘉靖帝这么多年没有白练、嘉靖帝感动了上天了。
以上就是在下为沈一石保命想出的两个绝招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绝招可想的呢?
最后我想说,在皇权社会里面,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存在、所有人都活在权力的阴影之下的。沈一石、严嵩、徐阶、胡宗宪、吕方、陈洪等等所有人,其实都不过是嘉靖帝的一个夜壶而已。嘉靖帝自己也永远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的到来、恐惧低下人架空自己、恐惧失去权力——也许制度的悲哀才是最大的悲哀、也许这就是很多人口中的江山吧!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