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当下围绕“新清史”的激烈讨论?
之所以说新清史“新”,是因为它有两点比较新,一个是材料新,一个是视角新。
首先说材料新,是因为新清史的学者率先发现了清朝满文档案的重要性。之前的学者主要使用汉文档案进行研究,满文档案利用的少,新清史一派倡导使用满文档案进行清史研究,因为满文档案比汉文档案内容更丰厚,所展现的细节也更多。由于新清史的带动,我国的清史研究也开始重视满文档案,这不得不说是史料学上的一大突破。
还有就是视角新,简单来说就是以内亚视角取代汉化视角。之前的学者,尤其是我国学者,主要建立在中原中心观的视角下,强调汉文明对周边文明的同化和影响。在这种叙事视角下,晚清之前的清朝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汉化的历史。
而在新清史的学者看来,内亚视角才是他们更熟悉的叙事方式。他们认为,清朝致力于建立一个跨民族、跨种族、跨文化的帝国,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建立一个“世界性帝国”。在这个庞大的世界性帝国中,帝国统治者所受到的影响不单单是由汉文明带来,而是多个文明相互影响的结果,汉文明的影响只是其中之一。
由此,帝国的统治政策也不仅仅是趋向汉化这么简单,而是要面对更多问题,因地制宜,甚至要扮演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文化下的领袖角色,用以巩固帝国在不同文化区域内的统治。
换句话说,清朝的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接受了中原汉族的传统,而是因为清朝皇帝更懂得如何平衡内亚传统与中原传统,让二者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
但在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将“中国本部”独立于“内亚地区”之外的倾向。简单来说,“中国本部”其实就是蒙古、满洲、新疆、西藏以外的区域。而满蒙藏等区域则被视为清朝治下的“非中国”区域。
当然,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不正确”。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新清史学者都持这种观点,更多的学者持有客观中立的立场,只是在学术层面上更多强调清朝治下内亚与中原传统的互动,所以对于新清史我们也不宜一杆子打死。
另外,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下,是没有这种“政治不正确”的,所以他们是没有这种政治包袱的。而以西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主义观念来看,多民族国家反而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正确,他们更倾向于把中国古代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民族压迫的产物。所以,这种政治文化上的区别也使得我们一些国内学者认定新清史语出惊人,居心不良。
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抛开个别被政治所绑架的言论,新清史的很多观点还是值得我们国内学者去学习借鉴的,我们更要学会引入新学理,以建构新的研究框架,而不是亦步亦趋,总跟在人家后面。
最后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拿出阴谋论来强调,这没必要,更彰显不出我们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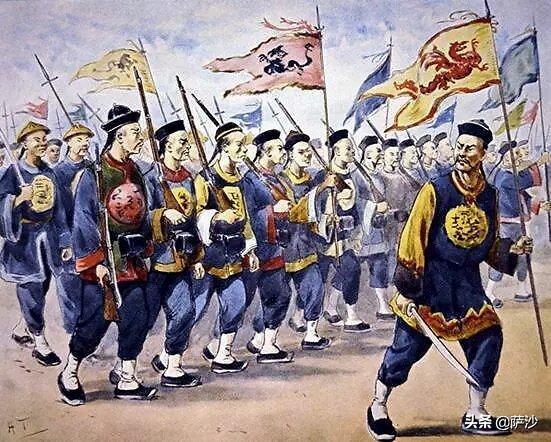
如何评价当下围绕“新清史”的激烈讨论?
在国内,我认为主流史观对清史是一分为二看待的,清朝入关时期的剃发易服、血腥杀戮、跑马圈地,国内主流史观还是持全面批判态度的。
这个时期涌现的抗清英雄比如大儒黄宗羲、史可法、秦良玉等还是普遍持褒扬、歌颂态度的。
对于清朝入关后,开始安抚、治理天下那段历史,比如康雍乾盛世,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康熙的开疆拓土、平三番、收台湾、治理黄河水患等统一国家版图,维持民生保障的行为主流史观都是持褒扬态度的。
雍正大力整治腐败、打造清明吏治的行为也一直得到肯定,乾隆早年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被主流史观肯定的。
但是,雍正、乾隆的文字狱,记得我们读小学时历史课本上都是公开批判的,在这个问题上主流史观没有任何含糊。清朝后期的吏治腐败,国家沉沦、苟且偷生、民生艰难,主流史观也是持绝对批判态度的,这个绝对没有模糊空间。邓公跟英国政府谈香港问题时都明确无误的说,如果愿意谈,我们就谈,如果拖延不谈,1997年我们就单方面收回香港,1997年我们还不能收回香港,任何执政党都应该下台,否则老百姓会骂我们是李鸿章。从邓公的态度,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出主流史观对晚清腐朽统治的蔑视!
清史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国家能够中肯、客观的写好自己的历史,我们不需要外国人帮我们写什么新清史,清史就是清史,没有什么新旧之分。国内个别人从自己的角度、观点去解读清史,只要没有无中生有、编造事实,只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独立视角的解读,我认为那只是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不赞同,也可以反对,但是不能禁言。
而且国内对清史全部持褒扬态度的应该只是个别人,你不喜欢,可以驳斥,也可以当作他胡说八道,没有必要去树立什么新清史。因为你不喜欢的那一部分人只是个别大V或者历史学者,他们不代表政府立场,更不代表主流史观。
当然,如果有扭曲、编造历史事实,没有逻辑观点为了激愤而激愤的那就不是观点,那叫别有用心或者愤青,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反驳或者举报,有很多部门会打击这种虚构、颠覆历史的人。
如何评价当下围绕“新清史”的激烈讨论?
元朝清朝肯定是中国!否定这个完全不符合史实。但是这两个朝代在文化上的倒退,将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打断也是历史史实!我们现在回顾历史,是要发现问题,纠正问题,真正将中华文明智慧发扬光大,而不是混淆视听式的否定历史。
如何评价当下围绕“新清史”的激烈讨论?
若没有阐述清朝被评为东亚病夫的章节,就是苍白无力,经不住任何分析的!东亚病夫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坚决不接受的骂名,希望“新清吏”,能给人民群众及全体爱国主义者一个满意交待!别一说别的就大写特写,甚至不遗余力的辩白;一提到东亚病夫就罢笔不写了!非常抱歉,东亚病夫的骂名贯穿清朝始末,绕不过去;若省略不写,全体中国人民不答应;轻描淡写爱国人士不同意;书写不深刻,当心爱国主义者的先锋队~明粉揭露清朝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
如何评价当下围绕“新清史”的激烈讨论?
这个问题太宏大了,一两句,甚至一两篇文章都说不清。在我看来总的来说,清史是野蛮征服文明的一部历史,清朝在社会,经济,科技,制度完全落后与明朝,入关前的满清就是个军事奴隶主集团。清史也是与儒家文化中糟粕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朝代,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雍正曲解重新定义“中国而夷狄也 ,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奴才化的思想统治结果,打断了近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让近代中国汉奸辈出,他们的对日投降理由就是这个。至于其他的不说了,光这两点就可以给清史定性为差评了。
如何评价当下围绕“新清史”的激烈讨论?
这场争论,现在看来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讨论,变成了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国家和民族理念构建争论。而后者,恰恰是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做,但还没有完全做好的一件事情。
首先看一下什么新清史。有新必然就有旧。现在没有所谓的旧清史。也就只能以传统的清史研究为例来谈。可以理解为,从民国时期一直到当代以来,中国国内历史学者对于清史研究的成果。而新清史,一般指的是部分美国学者,尤其是当代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清史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学界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学者一般强调从国际视野来看待中国从清到近代以来的历史。同时,他们不持有中原文化正统的观念,而且比较强调满族的民族主体观念和文化主体观念。实事求是的讲,这倒不一定是这帮学者包藏祸心,意图分裂中国,而是他们的这套思维模式,完全是从西方尤其是欧洲历史当中传承过来的。
其次,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和关系问题,是整个中国近代转型在政治理念上的核心问题,不是当代才形成的,而是从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新清史相关争论的核心所在。上推到晚清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两大政治势力,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也就是19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并且长期主导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争论。在这个时候,革命派代表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他明确将满清政权和满族,作为斗争对象。很显然,至少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中华是不包括满族的。而改良派基于传统的君臣理论出发,认可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们认为皇帝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象征,具有超越民族的特征,可以实现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政权构建。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修改了三民主义。开始提倡五族共和。在这个时候,汉民族的本位主义让位于现实政治需要。在民间层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主张以中华民族的概念来统一涵盖在中国生活的各族民众。这种论述虽然非常粗糙,但迎合了政治需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当时的民族矛盾。所以不仅在当时被接受,而且成为之后的主流政治论述。解放以后,苏联式的民族关系理论开始成为中国主导的政治理论。在这种理论下,形成了主导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概念。
国家概念和民族概念密切联系。在晚清革命派的理念当中,国家概念本质上等于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是将满人的政治特权全部打碎。在改良派的眼中,国家实际上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一整套的统治秩序。这两个国家概念实际上和欧洲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有很大区别。欧洲的这种国家,对内的时候具有统治管理的特征,对外的时候则体现为对本民族的一种代表性。而这种对外特性,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成为中国的特征。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还是过于松散。近年来,有些学者比如张维为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这种说法有一定新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解决国家内部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协调问题。而这是非常关键的。从本质上说,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国家是由国民依靠着共同的国家观念而形成的。
再次,同类型的争论,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界,在网络舆论上也有非常显著的体现。对于元清两个王朝性质的界定,在网上有些人一直有不同意见。本质上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关系的争论。这种政治理念构建,需要极大的社会成本以及时间成本。新清史的满族主体观,不仅挑战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王朝正统论,而且也挑战了中国当代的民族关系论。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必然会上升到政治层面。而如果单纯退回到学术层面,这些美国学者的部分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总体来看,还是有很明显的问题。举例来说,乾隆是一个经常被他们提及的皇帝。在经历了康熙和雍正两代高度强调汉化的皇帝之后,乾隆是一个反动。他高度强调满族主体性。但应该看到,乾隆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汉化的皇帝。而满清王朝的汉化趋势,实际上并没有在乾隆朝发生逆转。以乾隆在某些方面对于满族传统特色的坚持和强化作为论据,来论证满清王朝并没有能够融入中国历史,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最后,谈一谈中国人如何面对海外中国研究。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强势,海外中国研究对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总是应该由本国完成,而不应当依赖于国外。从这个角度上看,以中国视角进行中国研究,始终应当是中国研究的主体。对于外国视角的研究成果,可以加以参考,但不能让其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研究的主导。不管是新清史研究,还是中国研究领域其他方面,比如经济史领域当中的加州学派等,中国学者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呼应这些外国学者的研究。新清史当中的争论反映出的问题,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理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丧失了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的主导权问题。其实反过来想一想,美国学者会对于中国学者的美国历史研究,给予如此高度的关注?这是不可能的。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除了极少部分学者之外,大部分人受限于自身文化意识以及所处环境相关资料的匮乏,成果的质量是不高的。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学者重视,主要还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因素。对于此类研究成果,强化中国自身主体意识,推进中国自身的研究,才是最好的回应之道。无论是歇斯底里的咒骂,还是干脆拜倒在地,彻底认同西方,都是愚蠢的做法。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