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恭几十个人是怎么守住北匈奴两万人围攻一年的?是不是历史夸大了,还是真有其事?
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西域戊己校尉耿恭屯兵金满城,手下只有区区数百汉军,却遭到匈奴两万铁骑的围攻。所幸耿恭准备了大量剧毒箭矢,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逼得他们暂时后撤。
耿恭当然明白,危机只是暂时解除。匈奴人这次只是稍避锋芒,等他们铲除附近车师国的残余抗匈力量,巩固了局势,就会卷土重来。而金满城虽地扼咽喉,但地势低缓,水源也不充沛,绝非久守之地。为了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援兵到来,耿恭决定换个地方继续跟匈奴人玩儿!
图:车师古道,当年耿恭他们从这里撤离金满城
这个地方,叫做疏勒。注意,这不是班超驻节的那个西域南道之疏勒国,而是在金满城东南不远处的一个要塞。其残骸至今尚存,为新疆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汉代建筑遗址、被自治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置就在今新疆奇台县以南六十公里处半截沟乡麻沟梁村石城子这个地方。大家有空可以去瞻仰瞻仰。其实说是城堡,也就一个方圆不过半里的小土围子罢了。具体小到什么程度?南北宽138米,东西长194米,还没半个足球场大,耿恭几百人守在里面也够挤的。不过正是小城才最好守,因为需要防守的城墙短,进攻一方兵再多施展不开也没用。它还有一个优点是建在天山半腰,海拔高达1770米,北靠一面陡坡,两边都是天然的悬崖峭壁,下临万丈深渊,放眼望去,高峻险要直入云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另外,疏勒城东面傍依一条常年不绝的麻沟河,流入城中可为水源。在西域想要守城,没有比水更为宝贵的东西了。
于是这年五月,耿恭率部移驻疏勒城,积储粮食与饮水,整修军械,加筑城防,准备长期坚守。
两个月后,不出耿恭所料,匈奴人卷土重来了。这一次,北匈奴单于亲自出马,不拔掉耿恭这颗讨厌的钉子,他决不罢休。
可北单于万万没想到,就算这样,耿恭居然还是没屁滚尿流的投降,甚至也没龟缩城中,反而率领一支敢死队,又一次主动从城中杀了出来,顿时打了匈奴大军一个立足未稳,丈二摸不着头脑。
然而关于这次战役,范晔《后汉书》给我们留了一个不小的疑点,我们先看原文:“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
这就奇怪了,我们前文明明提到,按照汉军编制,耿恭和关宠这对戊己校尉手下各只有数百兵马,这一下子怎么又跳出数千人的敢死队来,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小生认为,史书这句应为笔误,可能刻错了,把“十”刻成了“千”。也就是说,这支敢死队其实只有数十人。
当然也有人说,这数千敢死队可能是耿恭在疏勒城里招募的车师民兵,可是这更不可能。车师后国是个小国,全国人口不过一万五千,军队不过三千(见《后汉书西域传》)。耿恭去哪里招数千壮丁来参战,还愿充当敢死队给汉军打先锋,这岂不是痴人说梦?再说方圆不过一里的小小疏勒城也挤不下这么多人啊!而对照司马彪的《后汉纪》:“恭募先登士四十人出城奔,斩首数十级。”可见范晔此处果然笔误。
竟然只有四十人,耿恭这锋芒初露,真是摸透了用兵之道——以小规模的最彪悍的特种部队对匈奴人进行突袭,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匈奴人还没从金满城阴影中走出来,就又在疏勒倒了大霉,遭到汉军如鬼魅般的夜袭,顿时炸营而逃,一路狂逃至山下十余里,见耿恭敢死队没有追来,这才长舒一口大气,再也不敢妄自攻城。
然而,大单于毕竟是大单于,果然比左鹿蠡王诡计多端,他见疏勒城无法一时拿下,便转换思路,使出了切断汉军水源的损招。
大单于命令,派重兵去到疏勒城下麻沟河的上游,筑起堤坝,堵塞河道,竟将这汉军的唯一水源给生生切断了。
图:疏勒城与麻沟河谷歌地图
这下耿恭傻眼了。没料到匈奴单于竟能想出这等损招,简直比汉人还要阴险狡诈。这可怎么办呢?如今又是初秋干旱时节,等到老天开恩下雨还不知猴年马月,而城中储备的饮水最多只能坚持十天,如果再没水来,大家都得活活渴死。
匈奴单于笑了,大笑。常言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但却能被水憋死,尔等还不快快投降?
图:这就是当年被匈奴人截断的水源
耿恭当然不投降。因为他还有最后一招,挖井!地表水没有了,还有地下水。咱们掘地三尺,不,三丈,还怕整不出几百人喝的水来?
然而,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汉军上下齐上阵,连耿恭都亲自上工地挖土,可大家一气挖了好几个井,每个井竟然都没有水。这不是他们挖的不够深,别说三丈,最深的井都有十五丈了,这已经是超过十层楼的高度,然而,还是不见水,一滴水都没有!
其实这也很正常。疏勒城建在半山腰悬崖峭壁之上,那地下水得在多深!又值秋七月天根水涸之时,打井?我看也这不过是将士们在求生本能的促使下,尽人事而听天命罢了,希望微乎其微。
图:疏勒城地势
一般来说,人在断粮的情况下可以存活七天以上,但是断水超过三天,大部分人就会因为脏器脱水而死亡。面对死亡阴影的一步步逼近,汉军将士们这些天是怎么撑过来的呢?
那当然是只得喝一切可以入口的液体了。包括露水、草汁、马尿,甚至到最后,史书记载:“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也就是用布从马的粪便中榨取出水汁来,捏着鼻子往嘴里灌。为了生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汉军将士誓死不降,日夜掘井不休,十五丈,十六丈,十七丈……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赫日当空,很多人竟活活累死渴死在了干涸的井边。再这样下去,大家恐怕就要“笮人粪汁而饮之”了。不到最后时刻,他们绝不杀马求生,对于一个战士来说,马是他们最好的战友与伙伴,甚至与自己的生命是平等的。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一天一天煎熬,又眼看着将士们如沙漠中的鱼儿般一个一个绝望死去,即便是汉兵如神一般景仰的最坚强的战士耿恭,也不免有些灰心了。终于,在人力无果的情况,耿恭决定求天。
说干就干,第二天,耿恭率领将士们来到枯井边,翕动干裂的嘴唇,仰天高呼:“昔苏武困于北海,犹能奋节,况恭拥兵近道而不蒙佑哉?又闻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之时,大军缺水,乃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我等岂能困死于此?”说罢耿恭整理战服,长跪于地,对井再拜,极尽虔诚,祈求苍天赐水于汉军将士。然后一个人下到井中,发疯了一般的挖,挖,挖……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啦!只见十余丈的深井之中,突然一道飞泉喷涌而出,转眼功夫就漫了上来,哗哗流动,堪比世上最动听的音乐。
井边所有将士都跳了起来,前歌后舞,欢声雷动,一个个高呼万岁,兴奋到忘乎所以。
耿恭湿淋淋的爬上地面,俯身喝了一口井水,但觉甘甜无比,醉人心脾,堪比世上最好喝的美酒。
大家全围上耿恭,一边互相泼水,一边哈哈哈哈的转圈,简直乐疯了。
清洌的泉水泼在耿恭的头上、脸上,只觉舒爽无比,他的眼前也不由模糊了,不知是水还是泪。
但耿恭毕竟是统帅,他第一个冷静了下来,止住大家,让他们暂且别忙喝水,不如趁此时机先演一场好戏给匈奴人看。
将士们心领神会,于是争先恐后的抄起水桶冲上城头,开始用水活泥来涂抹、缮修城墙,然后朝着发呆的匈奴人,把成桶成桶的水泼了下去。
匈奴人被水从头浇到脚,井水很凉,他们的心也被浇的哇凉哇凉的啊……
怎么水源断了半个多月了他们还有水,而且还敢如此浪费,这有没搞错啊!
难道汉人真的与老天同在,什么山神、水神、风神、雨神的都向着他们?
唉,算了,事已至此,咱们还是像前次那样,先撤吧,等哪天这些神仙们都打盹的时候再来!
读史至此,大家一定觉得《后汉书》这里夸大其词了,拜一拜竟然就枯井飞泉,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还是范晔一时想象力丰富把史书写成了小说?
当然不可能。范晔是个忠实正统的史家,这世上也没有神仙和救世主,一切只缘于耿恭坚持到底永不言弃的伟大精神。
其实,从地质学角度来讲,疏勒城一带植被繁茂,土壤温润,就算地表溪流被匈奴人截断,但水依然会沿着山体中的缝隙向下运动,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会立刻发生。所以,当耿恭他们挖井到一定深度,等到一定时间后,这些水才因自身压力的作用喷涌而出,成为疏勒飞泉。一切神迹,源自科学。
匈奴人虽然暂时不啃耿恭这块硬骨头了,但还有很多软骨头可以供他们啃。不久,单于领军远远绕过耿恭,穿越天山,侵入车师前国,将汉军己校尉关宠团团围困在柳中城内。与此同时,匈奴帮凶、即西域北道的焉耆、龟兹二国也同时动手,出兵围攻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陈睦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两千汉家将士,全军覆没。一时间,西域大震,北道诸国全面背汉,就连远在南道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驻节的班超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遭匈奴之北道属国龟兹、姑墨的围攻,班超以其威信,组织西域南道诸城邦奋力抵抗,但还是险象环生,局面危殆。万幸耿恭这颗硬钉子尚楔在天山北麓,匈奴主力一时还不敢放手全面南侵,否则班超也早玩完儿了。
图:疏勒城南倚博格达山脉,北控丝路要塞,易守难攻
但是,面对匈奴大军的猛烈攻势,车师人终于撑不下去了,他们苦侯救兵不至,于是全体投降匈奴。如此匈奴如虎添翼,又联合倒戈的车师前、后国军队攻至疏勒城下。
这次匈奴单于学乖了,既然耿恭有天神相助,那我就不跟你正面交锋了。把军队全撤到山下,将疏勒城远远的围起来,渴不死你我还饿不死你?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不如在这里跟你耗上了。你运气再好,你再能挖井,算你掘地一百五十丈,也不可能从地里挖出粮食来吧!
图:疏勒城遗址
但是匈奴人又错了,耿恭他就是一个奇迹的发动机,在他不抛弃不放弃的伟大精神之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不可以。从夏到冬天,耿恭兵团数百将士,竟然在孤城缺粮之几近绝境中,坚持了数月之久。
不过这一次奇迹的发生,却不是天神相助,而是贵人相助。
这位贵人,便是车师后王的夫人,一位有着汉人血统的伟大女性。正是她甘冒弥天大险,充当内应,为汉军偷送匈奴情报与宝贵粮草,这才使疏勒城得以屹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数月岿然不倒。
胡服虽然穿在身,但王后的心是中国心。祖先的教诲她一刻未忘,祖国的军队就由她来拯救。
图:车师王宫门前设耿恭台,立马提枪的耿恭雕像
然而,车师王后所掌握的资源毕竟有限,再说匈奴人的情报系统也不是吃干饭的。数月后,外援彻底断绝,耿恭兵团断粮了。但他们依然在坚持,实在饿到不行,只好流着眼泪杀死心爱的战马充饥;再后来又学起了苏武,在山里挖老鼠洞,抓些野鼠烤了吃;野鼠都吃完了,就在墙脚找些蜘蛛、蚂蚁往嘴巴里送;再不行就吃草根煮树皮。最后入冬连草根树皮都没有了,他们就只好把弓弩、铠甲上的筋革制的配件取下来,放在水里煮烂了吃。当然这需要很好的牙口,咬不动的人就没辙了。
就这样,匈奴人围攻了疏勒整整一年,耿恭等人粮尽援绝,直到公元76年正月,汉军将士终于吃完了他们最后一副铠甲,最后一张弓弩。在这最后的断粮时刻,耿恭环顾城头上他最后数十个弟兄,笑道:“恭与诸公跋涉万里至绝域抵敌匈奴,前后已一载有余矣!一年以来,历寒暑,当锋镝,我等同袍弟兄,心相结交,患难与共,情同手足,义如断金。今不幸粮尽兵穷,至于绝境,恭愿与诸位立生死之约,拼将玉碎以报国恩,何如?”
图:耿恭率部孤立无援坚守了一年多的天山支脉疏勒山
众人闻言皆感奋流涕,齐声道:“将军推诚相待我等,我等自当誓死报国,绝无二心,以扬大汉神威,气震胡虏,方不负我丈夫之志!”
耿恭大笑:来吧,我们唱首歌,给城下的匈奴人打打气。彼等鼠辈,坐拥数万大军,攻伐累月,竟不能近我金城半步,实可笑也!
于是全体将士,在城头齐声唱起了汉家战歌,其声慷慨豪壮,响彻云霄。匈奴人闻歌面面相觑,交头接耳,一片骚乱。
没想到汉军在这种时候还有心情唱歌,他们简直不是人!
当然不是人,他们是神,汉家战神!
歌罢,战神耿恭傲立城头仰天长啸,慨然吟道:“饮风吞沙可饱腹,落雪为裘拥铁骨,无有铠弩战歌护,万里天山我穹庐。”
此情此景,北匈奴单于也不由衷心佩服起耿恭来。此人节过苏武,才比李陵,智勇双全,豪气万千,杀之可惜啊!趁着现在他穷途末路,不如派个使者试试看招降他?条件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封白屋王(白屋为匈奴中一部族,后称靺鞨),妻以公主,如何?
高官美女,条件不可谓不诱人,但耿恭能被它诱惑么?
出乎意料,耿恭竟然答应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派个人进城来谈谈吧!
北单于大喜,赶紧在军中选了个能说会道的使者,让他进城去招降耿恭。
更出乎意料,耿恭见到匈奴使者后,根本不给对方“能说会道”的机会,半句不罗嗦,直接把人推上城头,当着城下匈奴单于的面,迎头就是一刀下去!
可怜的匈奴使者,直挺挺地就躺一边凉快去了。
耿恭把刀一扔,头也不回的命令:把这家伙给我放血,完了切吧切吧烤了,它再难吃总比皮革好下咽。
汉军士兵们早饿坏了,闻令赶紧动手,聚柴生火,剥皮切肉,直忙的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好像他们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猪。
一切准备停当,耿恭和将士们便用碗盛着匈奴血,在城头上开起了烧烤宴会。他们一面大口吃肉,一面开怀对饮,谈笑风生,视城下数万匈奴大军如无物。
图:疏勒城遗址正门城楼,今人在遗址上新修了一座镶嵌着狼头的城门
原野上万籁俱寂,所有匈奴人都吓呆了。耿恭营造的这个场面,实在太震撼,使他们如陷噩梦之中,千年难醒,永世难忘。从此,耿恭“吃人魔王”的称号响遍草原,传闻可止匈奴小儿夜啼。
这边耿恭正在美餐,忽然想起什么,忙站起来走到城墙边,深深向下一鞠躬道:“恭虽不降,然谨谢单于赐食!”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接着,城下爆发出一片哭爹喊娘之声。
读史至此,实赞范晔笔锋传神:“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他们不幼小但脆弱的心灵受到了巨大创伤。
匈奴单于大怒:“今不杀耿恭,本单于誓不为人!”发疯一般向疏勒城增兵,日夜围攻!然而,在耿恭将士们的顽强抵抗下,布满硝烟的汉军军旗始终猎猎飘扬在天山风雪之中——疏勒地势太险要了,匈奴的骑兵根本冲不上去,只能弃马攀爬,可爬上去也是送死。汉军虽然没了弓弩,但城里石头还是很多的,砍树做些发石机,居高临下随便一通砸,爬坡的匈奴人就得摔下去一大片。
论城池攻防战,匈奴人永远都不是汉军的对手。没有弓弩算什么呢?还可以飞石头砸,烧开水浇,用火油淋,砍大树挡,又或在城下挖几个陷阱几条壕沟,里头再插些尖木桩啥的,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总之金木水火土,什么不能拿来当做武器,只有城里还有能动的活人在,你多少部队也攻不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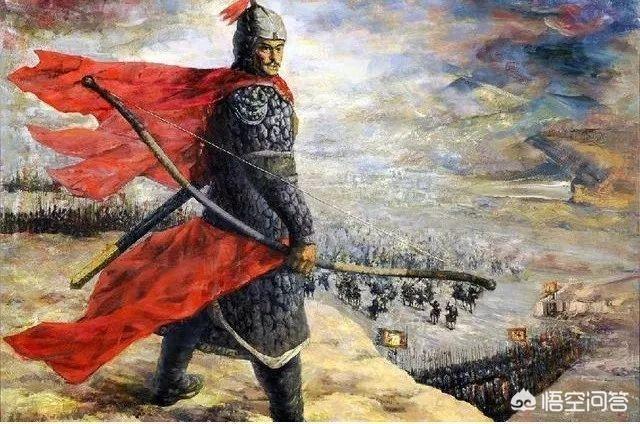
耿恭几十个人是怎么守住北匈奴两万人围攻一年的?是不是历史夸大了,还是真有其事?
自古西域多动乱,自东周到清末,这个地方似乎就没消停过。偶尔也有老实的时候,那基本上都是被中原给打怕了,第一个让西域游牧民族胆寒的是汉武帝时期的几次战争。
西汉时期,从汉武帝刘彻时起,中华疆域所至,从敦煌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广大西域都属于汉朝。公元前60年,汉朝在如今的新疆轮台设置都护府,另设戍已校尉、戍部候等军政长官,管理当时西域的婼羌、楼兰、莎车、疏勒等三十六个小国。
然而,随着西汉末年王莽篡汉使中原地区征战不断,大汉王朝虽然名义上统治着西域,其实根本无力掌控了。匈奴卷土重来,重新控制了西域。
光武帝上台,东汉揭开了序幕。
曾经的西域各小弟纷纷遣质子到中原,请求光武帝的庇护。然而大汉王朝已不再辉煌,留下的只是百废待兴,对匈奴在西域横征暴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经过了“光武中兴”,汉王朝的国力逐渐恢复,终于到了和匈奴重新盘道的时候了。
公元74年,汉明帝刘庄决定派兵重新进入西域。西征大军以窦固为主将,耿秉和刘张为副将。从敦煌出关后,一举击溃了匈奴南呼衍王的军队。汉军随后继续西进,攻取了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车师前后两国。
东汉朝廷随后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陈睦任都护。同时也恢复了戊己校尉制度,戊校尉由耿恭担任,驻屯于车师后国的金蒲城(巴里坤县),扼守天山通往北匈奴的要道。己校尉由关宠担任,驻屯于车师前国的柳中城,两地互成犄角之势。
窦固大军在西域仅仅驻扎了几个月,便在汉明帝的命令下班师回朝了。耿恭和关宠二人的驻扎地仅仅有不到一千的兵马,在他们的对面则是匈奴数万铁骑。
名义上西域又回归到汉王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西域小国经过了被光武帝“抛弃”的故事后,对汉王朝的信任度直线下降。他们对依靠汉王朝还是臣服匈奴,基本上处于观望的态势。耿恭和关宠想在西域活下去,只能自力更生。
其次,匈奴虽然被窦固大军击溃,但远没有霍去病或者后来的蓝玉对游牧民族那么疯狂。匈奴的军队是被击溃了,但政体体制完好无损,他们等待着反扑的机会。
最后,汉王朝虽然经过了“光武中兴”,但仅仅比战乱时期好一些,称不上是盛世。因此,如果匈奴重新反扑,汉王朝当时的经济和军备状况并不足以去打拉锯战。
果然,窦固大军班师回朝没多久,西域出事了!
这个事比较简单,匈奴发动两万大军攻打车师后国,并擒杀了车师后王。随即,匈奴两万大军把汉将耿恭把手的金蒲城围得水泄不通。金蒲城全城兵勇不过三百多人,怎么办?
耿恭素问匈奴人极其信神明,命将士将弓箭上的箭头涂满了毒药,并告诉匈奴人被射中的话,神明会对被射中者进行惩罚。后来,被射中的匈奴兵创口处起了脓块,对金蒲城守军的话深信不疑,顿时军心打乱。耿恭趁着连夜大雨,冒险率兵骚扰匈奴大军。在半威胁半吓唬之下,匈奴大军撤退了。
耿恭明白匈奴大军仅仅是暂时撤退,金蒲城犹如三国时代的小沛或新野,弹丸之地没办法抵挡重整旗鼓的匈奴人。随即,耿恭率领汉朝军队驻扎在了疏勒城。耿恭带人一方面屯物资,一方面修筑工事,随时迎接匈奴人的到来。
在耿恭刚到疏勒城的两个月后,匈奴左鹿蠡王的军队兵临疏勒城下。
由于疏勒城屯有大量物资并在耿恭的带领下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这里变得易守难攻。匈奴左鹿蠡王也是个行家,久经战争的他并不着急攻城,而是断了耿恭的“源”。匈奴左鹿蠡王认为,沙漠作战,水源是行军必备的物资。他觉得没必要动用兵马攻城,而是让匈奴士兵用沙袋堵住通过疏勒城的水源,并对其进行改道。
确实,这一招奏效了。疏勒城内很快水源告急,储备的淡水都喝光了,守军官兵焦渴难耐,甚至开始从马的粪便中榨取水汁来饮用。困境之下,军心开始动摇。耿恭心急如焚,此时换成了他想去拜一拜神明了。
那耿恭拜的神明又是谁呢?李广利。
当年李广利将军在遭到匈奴围困的时候,也被断了水源。他拔剑刺山,泉水飞涌而出。如今耿恭也派人凿井,他坚信虽然河流被改道,但是地下必有蓄水!果然,还真被耿恭挖出水了。在被挖出水的井边,耿恭对其跪拜。中国象棋有一招叫“耿恭拜井”,这便是其由来。
挖出水了,耿恭继续对匈奴人玩心理战。他让士兵端着水在城墙上冲着匈奴人大口大口的喝,顿时匈奴人就傻眼了。匈奴左鹿蠡王也愣住了,难道又有神明相助?结果,匈奴人又撤军了。
围攻“光明顶”的“六大派”是走了,然而江湖上不入流的“海沙帮”、“神拳门”等跳梁小丑却来了。
西域的焉耆和龟兹两个小国反叛,在他们的攻打下,西域都护陈睦所部全军覆没。己校尉关宠驻守的柳中城也被包围起来,匈奴人见到此状况又回来了,带着焉耆和龟兹再次赶往疏勒城。几个月后,疏勒城粮草都耗光了,全城将士不得不煮了铠甲或者鞭子吃。从一开始的近千人到如今的数十人,疏勒城兵将饿死的饿死,病死的病死。
匈奴见状也非常佩服耿恭所部,派遣使者进行招降。耿恭不为所动,当着匈奴人的面杀了匈奴使者,然后“壮志饥餐胡虏肉”。匈奴人大吃一惊,攻城更为猛烈了。
另一头的中原地区,汉明帝去世,汉章帝继位。
就在权力的更迭期间,耿恭和关宠的告急文书抵达朝堂。救?时间根本来不及了。不救?活活壮烈牺牲。关键时刻,司徒鲍昱发表了的意见:汉帝国从来不冷却英雄的热血,即使这次救援注定失败,也要向世人宣告汉帝国从来不会放弃为他战斗的勇士!
公元75年冬天,酒泉太守秦彭、谒者王蒙等人统率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国军队共7000人,前往西域救援。遗憾的是汉朝军队赶到柳中城时,关宠已经病死在军中。
秦彭指挥东汉援军大破敌军,柳中城成功解围,匈奴及部分西域小国纷纷撤退。在柳中城成功解围后,接下来就是要将疏勒城中的耿恭救出。援军的副将王蒙认为数百里之外的疏勒城杳无音讯,也可能已经被匈奴攻破,况且隔着天山之险,整个行军途中危机重重,主张撤军。
另一位将领主张必须驰援,他就是之前耿恭的部下,被派去求援的范羌。整个援军就此分为两派,最终秦彭见范羌态度坚决,便拨给他两千军马前去疏勒城。
此时的疏勒城外,匈奴大军因为已知晓柳中城被汉王朝军队成功解围,仅此早已撤退。而疏勒城内,耿恭军队因为被围困多时,粮草耗尽又因日夜守城,仅仅剩下26人。当范羌军队抵达疏勒城时,耿恭还以为是匈奴军队,准备继续作战......看清是援军后,打开城门,所有将士相拥而泣!早已陷入绝境的孤军将士再也没有想到还有获救的一天。
第二天,疏勒城守军26人便同汉王朝援军一道返回。北匈奴派兵追击,汉军边战边走。官兵饥饿已久,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当他们抵达玉门时,只剩下了十三人。这十三人衣衫褴褛,鞋履洞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立。
这些人获得了战友们的无上敬意,玉门关中郎将郑众及校尉们亲自为幸存者们安排沐浴更衣, 并上书朝廷说:“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耿恭到达洛阳后,司徒鲍昱上奏称耿恭的节操超过苏武,应当封爵受赏。于是汉章帝任命耿恭为骑都尉,军吏范羌为共县丞。遗憾的是耿恭母亲还没能见到自己儿子的归来,便去世了。
不为大汉耻!
英雄,不该被遗忘!
耿恭几十个人是怎么守住北匈奴两万人围攻一年的?是不是历史夸大了,还是真有其事?
不是几十人是数百人,援军到达的时候仅剩26人。而安全到达玉门关的时候只有13人了。这个故事在《后汉书·耿弇列传》中有详细的描述,叫做“十三将士归玉门”。这比所谓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要真的多,而且他们这几百人守了数月,直到援军到达,还在坚守。
匈奴围城事情是这样的,公元75年,汉朝重设西域都护。任命耿恭和关宠为戊已校尉。第二年,北匈奴大举进攻车师,车师投降后,和匈奴组成联军围攻耿恭所驻守的金蒲城。牢牢卡住天山通往北匈奴的咽喉,匈奴两万人将金蒲城围的水泄不通。
耿恭的计划耿恭明白,这数百人是守不住城池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新继位的汉章帝,能派出援军。虽然希望渺茫,但是他唯一能做就是在援军到达前不能让士兵们堕了士气。在白天匈奴攻城的时候为了打击匈奴士气,他向下面喊话:“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意思就是,汉朝的箭是神箭,只要中箭就让你生不如死。实际上就是毒箭,这是一场心理战。匈奴中箭的伤口开始溃烂,剧痛难忍,有效的打击了匈奴的士气。
打击对方士气是第一步,还有第二步就是趁匈奴士气低落,派出了百人的敢死队夜袭匈奴。匈奴这么也没想到他们百人就敢偷袭,所以毫无防备,死伤甚重。所以史书中记载匈奴单于“震怖,叹曰:‘汉兵神,真可谓也!’”至于单于有没有说这句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匈奴单于确实溃败而去。汉兵士气大振,但是耿恭明白,这只是暂时的。汉军必须要找一个更有利于防守的地方。耿恭趁匈奴退却,把士兵转移到了疏勒城,这是汉朝修筑的要塞,依山傍水,地势险要。
弹尽粮绝的汉军不久匈奴又开始围攻疏勒城,他们这次断绝了疏勒城的水源。看过贝尔荒野求生的都知道贝尔曾用大象粪乍水喝,耿恭恐怕是第一个用马粪乍水的喝的人,反正史书上有记载的也就他是第一个了。耿恭命令士兵“乍马粪汁而饮之”。但这终究不是办法,最后只好打井取地下水。但是打了十五丈深,仍然没有见到水。就在士兵们要绝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史书记载“飞泉奔出,众皆称万岁”。这次耿恭又开始嘚瑟了,他们向下泼水。单于一看,这真是活久见:“难道汉军真有神助”。
几个月过去了,援军仍然迟迟未到。城中食物也吃完了,就连弓箭上和铠甲上的皮也煮了吃,匈奴开始劝降耿恭。耿恭诱使匈奴使者来到城头。当即把他烤了吃,这就是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出处。此举一是向匈奴表达自己的决心,同时提升手下的士气。最后还是车师王太后暗中派人送来了粮草和军械,因为车师王太后是汉人。
汉章帝的抉择而此时刚刚记载的汉章帝就面临了一个重要抉择,救还是不救。以司空第五伦为首的反对救援,他认为即便援军到达汉军将士也已经尸骨无存。但是司徒鲍昱说了一段话,一锤定音。
今使人处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此际若不救,匈奴复犯边塞为寇,陛下何以使将?汉章帝当即下令命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国军队共计七千人,开始了长途救援。汉军大败匈奴军,斩首三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另有牲畜不计。此时,将士们又面临一个抉择,按说这也是为耿恭报仇了。此时退兵也不为过,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何况长途奔袭又经过一场大战的士兵还要翻越正值大雪封山的天山,如果有变,大胜变成了大败这个责任谁担的起。
范羌的坚持这时一个人站了出来,我担!此人就是耿恭派往求助的部下范羌。有些将领不愿继续北进,就分给范羌带领两千人。范羌带着两千人翻越了天山,对于这段史书中只记载了“开门,共相持涕泣”。但是此时数百人只剩下26人,在返回玉门关的途中又有匈奴阻击,仅有13人回到了玉门关。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把耿恭和苏武并列,范晔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写下了他的评价
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耿恭几十个人是怎么守住北匈奴两万人围攻一年的?是不是历史夸大了,还是真有其事?
耿恭守疏勒的事迹,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此战中,耿恭杰出的军事才能,汉军将士的忠诚坚韧,大汉朝廷的大国气魄,都值得后人铭记。
可是,由于缺乏足够宣传,其事迹知名度不高,甚至不少听过“十三勇士”事迹的朋友也未知其详,以至于以为其不过是“靠几十人抗拒两万”的西游记一般的神话。
危急之势75年,取得天山之战胜利的汉军主力在窦固的率领下班师回朝。
北匈奴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汉军主力征伐时,北匈奴回避其锋,保存实力,就是等汉军主力班师,立刻反扑!
因此,汉军主力前脚刚撤,北匈奴就以左鹿蠡王率2万骑兵攻打车师。
当时,天山附近的汉军兵力极少。
戊己校尉耿恭屯于车师后王所部的金蒲城(也叫金满城),遏者关宠也为戊己,屯于车师前部的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
汉军可以指望的,似乎只有刚刚归顺的车师后王的军队。
在一年前与汉军作对手时,车师后王的军队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
因此,耿恭令其手下司马率兵300前去支援车师。
耿恭所屯之地,总共数百人,一口气派出300人,是想倾尽全力支援车师后王抗击北匈奴。
可是,耿恭派出的援军在路中遭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
旋即,匈奴军破杀车师猴王安得,扑向耿恭所在的金蒲城。
汉军主力走了,车师后王被杀了,耿恭本就不多的兵马又折损了300!
而从300出援军(出援军应是精锐)一战即全军覆灭来看,汉军的战斗力显然没有太大优势!
耿恭想活下来,需要奇迹!
心理战大师:将微弱的技术、战术优势“神化”汉军手中,有一个秘密武器:毒箭。
毒箭,其本身不算神秘武器。
据考古发现,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人在箭矢上涂上毒,用于狩猎。
不过,东汉时,毒箭的毒性取得了重大进步。
后来,东汉末年,关羽中毒箭,久久不能痊愈,非要专门请良医(演义中是华佗)专门“刮骨疗毒”才能搞定。
汉军毒箭毒性强,一旦被射中,毒性发作,伤口糜烂,令人惊恐。
不过,毒箭毕竟不是原子弹,不是足以改变战役进程的武器。
何况,其毒性也只是“视创皆沸”,不致命,主要是起到影响敌人心理的作用。
耿恭巧施心理战,使毒箭的心理威慑力得到放大。
他放言:“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我们的箭有神助!中箭者一定会倒霉!
果然,中箭的匈奴人“视创皆沸”,出现了超出认知的症状。
对于匈奴人来说,出现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去分析箭头化学成分,自然是联想到“汉家箭神”的“传说”。
汉军又有一项战术优势:雷雨战。
或许与常年生活于大陆性气候地区以及以畜牧为生有关,草原民族普遍对雷雨有敬畏心理。在雷雨天,他们基本上不作战、狩猎(猎物也要躲雨呀)。
相比之下,中原军队对雷雨基本上比较适应,冒雨而进的作战非常常见。
所以,雷雨天作战,很长时间内是中原军队的优势。后世刘锜等人也曾以雷雨天袭击金军,赢得胜利。
很快,暴风雨来了。
耿恭指挥汉军随雨而击,杀伤甚众。
匈奴人更为震怖:“汉兵神,真可畏也”。
于是,匈奴人暂时退却了。
良将,总是能将微弱的优势放大。
金蒲城之战,耿恭以迷信说法,放大毒箭、雷雨战的优势,挫败了敌军。
更重要的是:此战,使汉军取得了心理优势,为以后的长期坚持树立了信心,创造了条件。
高明的移兵,稳固形势当然,如果靠装神弄鬼就能一直糊弄住匈奴人,那匈奴也不会如此强大了。
显然,匈奴人还会杀回来!
汉军驻金蒲城,主要是因其交通、屯田条件。
可是,金蒲城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有朋友说金蒲城缺水。其实不然,屯田之处当然不缺水)
因此,耿恭将目光瞄向疏勒城。
疏勒城,旁临深涧,地势险要,也在天山南北要冲。
其城东临悬崖,北为陡坡,南面地势稍低但坡度大,整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而且,其山间有涧,可以为作为水源。
因此,当年五月,耿恭移兵进入疏勒城。
匈奴人长于骑战,但缺乏攻坚能力,尤其缺乏山地攻坚能力。
移兵疏勒城,汉军具备了抗击匈奴绝对优势兵力的地形条件。
募兵耿恭原本在金蒲城就只有数百人,救援车师又折损了300。
因此,耿恭必须尽可能扩充队伍。
疏勒城远离中原,要朝廷增兵是不可能的。
因此,耿恭在城中及周边募兵。
东汉的边疆战争,采取的是“以战为战”的方略,即从边疆地区获取各族人员为兵源。
在与北匈奴的作战中,既有南匈奴、鲜卑等族的军队支持,也有地方各族百姓参加。
耿恭自然也紧急募兵,壮大势力。
很快,他募集的数千先登,发挥了重大作用。
士气战凭借疏勒城,汉军取得了稳固的地势条件。
可是,长期坚持,也需要稳固的士气。
古代围攻战中,因受不了长围久困,士气低落,最终崩溃的情况,比被对手强攻而破更为常见!
耿恭要想长期坚持,必须想办法提振士气!
首先,他采取了和后世合肥之战时的张辽一样的做法:主动出击!
趁匈奴军初至,立足未稳,耿恭令募集的数千先登“急驰之”,“胡骑散走”。
“胡骑散走”,也就是给与敌人的实际杀伤并不多。
不过,初战退敌,提振了汉军,尤其新募之兵的士气!
匈奴军也不是草包!他们看准了汉军的软肋:依赖深涧的水源。
因此,匈奴军在城下切断了涧水水源。
耿恭旋即令人挖井。
对于良将来说,挖井,也能挖出花样来!
汉军连挖十余丈,不得水。城中吏士口渴,只有榨马粪汁饮之。
此时,耿恭说:当年贰师将军拔佩刀刺杀,飞泉涌出;如今大汉得天助,怎么会没有水呢?
于是,耿恭整好衣服,拜井,为官吏士兵祈祷。
不久,果然水泉涌出!
显然,水泉不可能是耿恭“施法”弄出来的。耿恭不过是在挖井将成之时,赋予神圣化的仪式感,将挖井成功赋予了“神助”色彩!
“耿恭拜井”,既使自己人看到了“神迹”,也使城下的匈奴人再次见证了“神迹”!
“虏(匈奴军)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耿恭打赢了士气战!
坚持此时,外围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了。
西域的焉耆、龟兹攻打西域都护陈睦,陈睦战死。北匈奴军又围攻了柳中城的汉军。
同时,汉明帝去世,朝中大丧,迟迟未发救兵。
不久,车师也再次背叛大汉,与匈奴联兵攻打耿恭。
好在车师后王的夫人,是汉人之后,常将情报传递给耿恭,并偷偷给予一些粮饷。
不过,耿恭军所得有限,形势越发困难。
数月后,耿恭军粮食尽。汉军煮铠弩,食其筋革。
耿恭激励士气,与将士们推诚共生死,深得士心,”故皆无二心“。
困难条件下,汉军只剩下数十人!
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深处绝境,遂遣使招降:投降吧!我封你为白屋王!
耿恭骗使者上诚,亲手杀掉,放在城上”烧烤“,以示无降心。
单于大怒,增兵围攻,但仍不能克!
被“奇迹”所救的“奇迹”朝廷救兵久久不至,除了汉明帝驾崩外,还因为连年大旱灾,情况非常困难。
不过,汉章帝还是派出敦煌、酒泉的驻军各2000,前去救援。
敦煌、酒泉汉军,会和鄯善军共7000人,在交河击败匈奴军,斩首3800余级,车师复降。
不过,当时天寒,山上雪深,汉军将领多不敢去救。
此时,原本被耿恭派去敦煌的范羌,力主救援。
众将认为过于困难,但还是给了范羌2000人。
大雪丈余,行军困难。范羌的部队被迫丢弃了各类物资,仅带人赶到。
城中军听到声音,以为匈奴来犯,准备迎战,却听到喊声:我是范羌!朝廷派我来迎校尉!
城中山呼万岁!众人相拥而泣!
次日,耿恭、范羌率军撤离。一路上与匈奴军且战且走,阵亡很多。
守疏勒的将士,离开疏勒时尚有26人,抵达玉门时,只剩下13人!
大汉13勇士守疏勒的奇迹,由此传开!
汉家气魄当时大汉的情况是真的非常困难!
中原连逢大旱,又流行牛瘟,“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因此,大汉在天山地区暂时转取收缩。
大汉撤回了西域都护及戍、己校尉,又撤回伊吾卢屯兵。
不久,北匈奴卷土重来,车师等国复叛,北匈奴重占了天山地区。
整个西域,一度只剩下班超在孤军奋战!
所以,朝廷发兵救耿恭等人,并不符合其战略意图,完完全全就是去救人!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忠心护汉者,虽远必救!
汉家气魄,正是大国气魄!
耿恭守疏勒城,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个奇迹,是由将领杰出的军事才能,汉家男儿的忠勇坚持,国家“虽远必救”的大国气魄一起塑造的!
耿恭几十个人是怎么守住北匈奴两万人围攻一年的?是不是历史夸大了,还是真有其事?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真实真实历史。
说起来,耿恭之所以能面对几十倍的匈奴骑兵,坚持防御,也是可能的。
第一,耿恭驻守要塞非常陡峭
疏勒城附近的要塞,是汉军精心修建的。
要塞依山傍水,地势险要。
在古代,无论中国外国,面对这种坚固又险要的要塞,没有太多办法。
匈奴骑兵利害的是骑射,但对攻城就没意义。
汉兵最强的就是弓弩,又居高临下,威力强了一倍也不止,射程也远得多。
匈奴骑兵强攻,就要攀爬山体,成为几百名汉军弓弩活靶子。
这种情况下,久攻不克是正常的。
第二,并非一定要把汉军消灭不可
疏勒城的要塞并非扼守什么战略要道,打不打其实也无关大局。
只是匈奴王出于政治考虑,试图将汉军彻底打出西域。
但久攻不克情况下,匈奴王认为没有必要付出太大代价去进攻。
当时认为,杀光这300汉军,匈奴人要死3000人。
匈奴是游牧民族,人口稀少,一个很大的部落也不过一二千战士。
3000人的死亡太多,也没有必要。
第三,疏勒城具有长期坚守的条件
疏勒城有水源,匈奴曾经切断过但因有地下河所以没生效。
同时,汉军还存有粮食,虽然最后到了吧弓弩上用动物筋腱做的弦和盔甲上的皮革等都统统煮了吃了,甚至还吃了匈奴使者。
然而,毕竟粮食也支持了好几个月。
第四,车师人并不卖力
车师人是被匈奴打败,不得已投靠匈奴。
车师王很聪明,一旦汉军被消灭,自己就没有利用价值,恐怕要被匈奴攻击。
所以,车师人一面装作进攻,一面偷偷给耿恭提供情报和粮食,希望汉军尽量长时间坚守。
第五,大汉精兵,不是匈奴胡虏可以相比的。
很多人认为汉兵不如 匈奴人,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汉军职业军人各方面都是非常强悍的,丝毫不亚于匈奴那些牧民。
300耿恭的部队和后来救援的范羌2000精兵,在新疆转战1年多,面对数万匈奴大军。
耿恭300部队等援军翻过冰封的天山到达是,只剩26人,却无一人投降。
这些26人最后回到玉门关的时候,仅剩下13人了。
当时驻守玉门关的中郎将郑众给皇帝上疏为13勇士请功:“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耿恭几十个人是怎么守住北匈奴两万人围攻一年的?是不是历史夸大了,还是真有其事?
答: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战争史上,东汉“戊己校尉”耿恭死守疏勒城的悲壮一战,还有那“拯救大兵耿恭”的浴血时刻,都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
东汉永平十八年(75),即东汉王朝刚刚在西域恢复“西域都护”建制的第二年,不甘心丢失西域的死敌北匈奴,就发起了疯狂反扑:数万匈奴大军汹涌来攻,龟兹等西域小国也趁机反水。西域都护陈睦与两千多戍边汉军壮烈殉国。广袤的西域国土上,就只剩下班超、耿恭等人带着五百将士苦苦支撑。特别是退守疏勒城的耿恭,更是打到弹尽粮绝,靠吃铠甲与弓上的皮筋为食。疏勒危急,西域危急。
偏偏这时候,又恰逢汉明帝去世,新皇汉章帝登基。西域战事十万火急,可朝中好些“名臣”却在新皇帝面前扯皮。比如“清流领袖”第五伦就大放厥词,坚决反对救援西域,要求这些汉军将士们就地殉国。如此论调,也气的司徒鲍昱一声怒吼:“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是啊,如果大汉朝对这些忠勇将士的死活坐视不理,那就寒了天下人的心,他日国家有难,谁还会挺身而上?
年轻的汉章帝,也终于被这句话震动。然后七千汉军爬冰卧雪,向着疏勒城的方向一路前行。接近疏勒城时,周围已是一丈深的大雪。耿恭的老部下范羌自告奋勇,带着两千援兵打头阵,在疏勒城下一声高呼:“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紧接着疏勒城门大开。耿恭带着仅剩的二十六名将士,与范羌等援军们相拥而泣。再然后,又经过一连串悲壮的突围血战,二十六名勇士进入玉门关时,仅剩了十三人……
这一场“十三将士归玉门”的热血往事,以《后汉书》的评语说“喟然不觉涕之无从”。但今天也常惹来一些“历史票友”们的吐槽。以许多“票友”们的论调说:包围疏勒城的北匈奴军有好几万人,耿恭满打满算才五百人,而且没粮没装备,他凭什么能守这么长时间?难不成是吹牛?
那到底是不是吹牛?这还得事实说话,首先一个必须要看的“实锤”事实,就是汉朝在当时西域的特殊“杰作”:屯城。
东汉的军制与西汉不同,常备兵力比西汉少得多,驻守在西域的兵力,更是少之又少。这场大战爆发前,汉军在西域的总兵力,也就是三千多人。这么点兵马,分布在西域漫长的战线上,平日里怎么驻守?主要就靠“屯城”。从西汉至东汉,汉王朝在西域修筑了大量的“屯城”工事。目前已发现的汉代“屯城”遗址,就有四十五个。特别是东汉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山脉,都新修了大量屯城,如坚固的钉子,“钉牢”大汉国土。
耿恭血战的疏勒城,就是东汉的“屯城”之一,即今天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这座城池巧妙的依山而建,用夯筑技术修成。整个城池东西宽280米,南北长380米,城墙历经两千多年岁月考验,依然还能剩下3米残高。其城内西北还筑有子城,整个城池形成严密防护。这样经得起两千年考验的筑城技术,造就了一座牢固的坚城。匈奴人别看有几万人,想要啃动它,真要有副好牙口。
而且别说是匈奴人,“拯救大兵耿恭”十五年后,那至今被西方学者认为与汉朝“齐名”的贵霜帝国,也对西域动起了歪心思,面对西域都护班超麾下了一千八百汉兵,贵霜帝国以倾国之力的七万大军涌入西域,接着就在汉军的“屯城”面前碰的头破血流,落得师老兵疲。
而在“拯救大兵耿恭”一战中,匈奴军面对如此坚城,也同样打得十分难看。匈奴单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对耿恭各种威逼利诱,又是许愿封王又是许婚,却是毫无作用。
比起这“实锤”的坚城来,同样“实锤”的,还有汉军的装备水平。东汉年间,随着炒钢技术的大量应用,汉王朝早已进入了“铁器化”时代,军队装备比起西汉来,更是一茬茬升级。就连罗马人的史料里,都留下了大量对汉朝装备水平的咏叹:“没有一种铁能与来自中国(汉朝)的钢相媲美”。汉军的弓弩更被罗马贵族们视为名贵收藏品。
1974年在山东苍山发现的“东汉永初纪年铁刀”,更见证了汉军的“制式装备”。这款铁刀长一点一五米,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七,刀背厚度一厘米。砍杀效果比起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各色刀具,威力都可以说碾压。汉代的壁画更告诉我们,这款铁刀,就是东汉普通士兵们的“常规装备”。
拥有这种强大装备的汉军,战斗意志更是强悍。东汉兵力不如西汉,但常年实行精兵政策,派驻西域的汉军,都是一等一的好兵。体会过汉军战力的,何止是日落西山的匈奴?就连当时如日中天的贵霜帝国,其七万大军在汉军工事面前碰壁后,野战又被汉军修理。最后只能乖乖认错,灰溜溜走人了事。
看过这样的装备水平,也就不难理解当年陈汤“一汉当五胡”的豪迈咏叹。放在东汉保卫西域的战场上,依托先进屯城防御,且以劲弩铁刀武装起来的汉军,纵是人数劣势,但单兵作战能力和装备水平,都是绝对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血战疏勒,还是接下来救援,如耿恭班超这样的汉军将士们,面对这场战争,从来没有放弃。
其实,当时留在西域坚守的,何止有耿恭。汉朝西域司马班超,也同样依托槃橐城苦战。他能够调动的,除了忠于汉朝的西域各小国军队,就只有身边三十六名汉军子弟兵了。但就是凭着这点可怜的人马,班超真的守住了。他拒绝了汉王朝调他回去的命令,依托西域各族军民的支持苦苦支撑,竟奇迹般坚守了九年,不但守住了阵线,还反击拿下石城,还在公元84年等来了汉王朝的一千八百援兵,把最苦的日子熬了过去。
接下来,靠着这依然有限的兵力,班超等大汉将士们,继续书写着奇迹:先打通西域南道,又击败贵霜帝国七万大军,公元94年秋击败焉耆等国叛军,把勾结匈奴欠下汉军无数血债的焉耆王传首京师。西域五十余国重新回到大汉朝的怀抱。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无阻,大汉威名从此远播。而昔日嚣张的北匈奴,也在燕然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里连吃败仗,开始凄然西迁……
对于殉国在疏勒的汉军将士来说,十九年后的这一幕,当可告慰。
大汉王朝开疆拓土的荣光背后,是强大的科技与产业支撑,更是班超耿恭为代表的,无数大汉男儿的浴血奋战。看懂这一仗,也就看懂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缘由,更看懂了每一次危难面前,中国人坚韧的硬骨头——总有那么多如班超耿恭这样的人,明明面对绝境,明明孤立无援,却依然选择负重前行,抛头颅洒热血死战一场。这样的人,中华民族,每个年代,都不曾缺席,更当得起我辈敬意。
参考资料:王小甫《汉匈战争三百年》、田小红《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黎尚诚《开拓西域的班超》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