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但教育家可能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就像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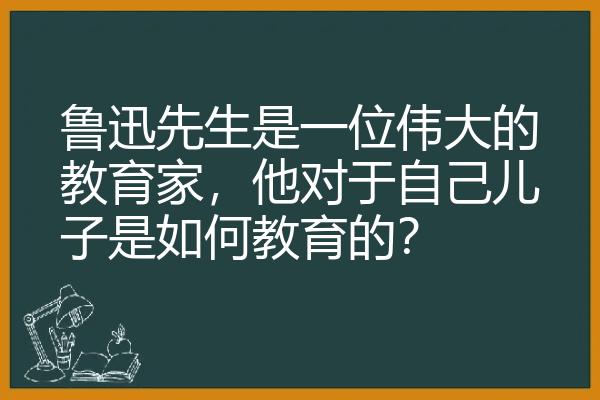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折射父母的价值取向。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能折射出为人父母者的价值取向。在这一点上,胡适和鲁迅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胡适希望他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做最上等的人”;鲁迅则较有平常心,他在文坛行走多年,见多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丑陋嘴脸,看够了上层社会的堕落,不希望孩子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他只希望孩子实实在在做人,“寻点小事情过活”。胡适一生,做的都是“最上等的人”,是皇上和总统的朋友,因而,他对孩子也有一样的要求。当年,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在苏州读书,1928年8月26日,在致胡祖望的信中,胡适写道: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个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大约是胡祖望向父亲报告考试及格了,胡适才有了“功课及格,那算什么”之说。如果功课是优呢?胡适会不会像当今某些家长,又有别的说辞?难说。鲁迅临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遗言,这就是收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叫《死》的那篇文章。对于孩子的未来,鲁迅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他说过希望他儿子做父亲做得比他还好。但是,对子嗣未来谋生的手段,鲁迅却写下了这样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宁可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胡适要求孩子做“最上等的人”,什么样的人算是“最上等的人”呢?他没有展开论述,但像胡适这样,一生大约应算是“最上等的人”吧?倘若以胡适本人为标杆,似乎不好说他的孩子完成了他下达的指标。胡适的长子是有一点出息的,蒋介石政权搬到台湾前后,胡祖望曾在他岳父驻泰国曼谷的一家公司任工程师。1953年迁居台北以后,往返于台湾、美国间,曾任台驻美经济机构代表。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读了两所大学,都没有毕业,还几乎成了“问题青年”,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是一个名人了,一生在捣鼓他的无线电,似乎不好断定是否属“寻点小事情过活”之类。周海婴写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其中谈到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嫡孙周令飞卖爆米花一事,倒是蛮有趣味的。80年代初,曾经发生一件给国人带来不小震撼的事: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从日本跟一个“身份可疑”的台湾姑娘张纯华到台北结婚去了。一时间,境外媒体大肆炒作,港台报刊称周令飞是“海峡两岸第一个闯关者”。周海婴在书中写道,周令飞刚到台北那阵,有人企图利用他。媒体一片喧哗,有的将他赴台的行动干脆名之为“投奔自由”。有的媒体企图邀他去为其工作,他立即警惕地意识到有可能被利用而予婉拒。他一向热衷于摄影艺术,宁愿改行学习经营之道,当起他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的协理,也不做“出格”的事。后来,因为修地铁,周令飞岳父开的百货公司门口临时搭起了围栏,交通受到妨碍,顾客随之大减,生意每况愈下,资金滞搁,只好关门了事。周令飞的岳父为了躲债逃去日本,只能靠周令飞这个外来的女婿料理一切后事。周令飞与张纯华夫妇一下子变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便是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周令飞也没有做“出格”的事。他们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以此度日。其实,周令飞的卖爆米花,不正是鲁迅说的“寻点小事情过活”吗?仅凭这点,我认为,周令飞是不愧为鲁迅的后人的,如果他“出格”,在台湾当个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不仅是有无才能的问题,更是有无操守的问题。依靠自己谋生存,求发展,正是鲁迅这条遗嘱的实质内容。周令飞不仅没有给鲁迅丢脸,实际上正是遵从了鲁迅的遗愿,是照鲁迅的遗嘱办事。宁可卖爆米花,也不愿做“出格”的事,这有鲁迅的遗风在,这有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有如此风骨,我相信周令飞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不过,话说回来,哪怕他永远卖爆米花吧,哪怕他永远生活在人间的底层吧,他在人格上也比那些空头文学家和美术家来得更健全,他的生活也比病态者更接近真实和自然。老舍说:“在我看来,(我的)儿子做木匠、瓦匠,或做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人人生而平等,这是西方所谓普遍价值之一,胡适在美国折腾了那么多年,怎么还会有“做最上等的人”的思想呢?这些文字,是胡适与孩子的通信,我相信他演讲做文章时,应该不会这么说这么写的。我们不能苛责胡适,胡适虽然是“最上等的人”,但并没有以人上人自居,他的朋友中,就有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尽管如此,通过胡适与鲁迅的这一对比,我要说的是,鲁迅是有平民情怀的,是有阅尽沧桑后的平常心的;同样作为“英美派”的胡适,比起徐志摩、梁实秋,要少许多“洋气”,但比起鲁迅,他确实还是高高在上的正人君子。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历史上很多名人在教育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丝毫没有含糊,今天小编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名人之一的鲁迅先生它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希望给各位家长一些启发。
1929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当时鲁迅48岁,中年得子的他是个身体力行的超级奶爸,自己给海婴洗澡,不让护士代劳。这对新手父母来说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差事,两人手忙脚乱,把孩子洗感冒了,鲁迅才同意让护士洗。
如果民国时有微信朋友圈,鲁迅估计会成为“晒娃狂魔”。有客人时,即使海婴在睡觉,他也要把孩子抱出来炫耀一番。
海婴出生20天就有照片,在同时代其他孩子中当属罕见。鲁迅每年都会带妻儿拍全家福,并在照片上认真地标注,更新儿子一点一滴的成长:海婴出生后20日、100日、6个月……习惯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甚至作了一首诗回应朋友对他溺爱孩子的嘲笑。这首名叫《答客诮》的诗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周海婴在回忆父亲时曾介绍说,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比如,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就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鲁迅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对周海婴的嘱咐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后来,周海婴遵从了父亲的遗嘱,选择喜欢的无线电专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和摄影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人们常惊叹于民国时期的思想璀璨,大师云集,才子佳人,风流倜傥。其实,那时候的很多大师也有着不凡的家庭教育思想。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周海婴在《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父亲对我的教育》一节中写道鲁迅 对他的教育理念: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还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但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钩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住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对我“拆卸技术”帮助最大的就是前述瞿秋白夫妇送的那套“积铁成象”玩具。它不但使我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象玩法,还可以脱离图形,自我发挥想象力,拼搭种种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我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斥责,只让我复原。我办到了。从此我越发胆大自信。一楼里有一架缝纫机,是父亲买给母亲的,日本JANOME厂牌。我凭着拆卸留声机的技术积累,拿它拆开装拢,装拢又拆开,性能仍然正常。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的确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 的尴尬局面,友好如初。我虽也偶然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父亲自己给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已将七岁。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的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外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我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父亲给祖母的信里常常提到我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成绩等情况,有时还让我写上几句。从存留的书信墨迹里,在信尾尚有我歪歪扭扭的个把句子。我当时是想长长地写一大段的,表达很多心里话,可惜一握笔便呆住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的信里,父亲写道:“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
父亲写信经常是用中式信笺,印有浅淡的花卉、人物和风景,按不同亲疏的朋友亲属选用。如遇到父亲写信,我往往快速地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挑选信笺,以童子的眼光为标准,挑选有趣味的一页。父亲有时默许使用,也有感到不妥的,希望我另选一枚,遇到我僵持不肯,彼此得不到一致时,他总是叹息一声勉强让步的。偶然父亲坚决以为不妥的,那当然只有我妥协了。据悉有一位日本仙台的研究者阿部兼也先生,他最近专门分析父亲信笺选用与收件者的内在关系。遗憾的是他不知道内中有我的“干扰”,使研究里渗进了“杂质”。在此,我谨向阿部先生表示歉意。
我小时候十分顽皮贪玩。但是我们小朋友之间并不常在弄堂玩耍,因为在那里玩要受日本孩子欺负。母亲就让我们在家里玩,这样她做家务时就不用牵挂着时不时探头察看。有一回,开头我们还安静地看书、玩耍,不久便打闹开了,在客厅和饭厅之间追逐打闹,转着转着眼看小朋友被我追到,他顺手关闭了内外间的玻璃门,我叫不开、推不开,便发力猛推,推了几下,手一滑,从竖格上一下子脱滑,敲击到玻璃上,“砰”的一声玻璃碎裂,右手腕和掌心割了两个裂口,血汩汩而下。小朋友吓得悄悄溜走了,而我也只顾从伤口处挖出碎玻璃,至少有三四小片。许是刚刚割破,倒未有痛感。父亲听到我手腕受了伤,便从二楼走下来,我迎了上去,觉得是自己闯的祸,也没有哭的理由。父亲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水,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话也没说,就上楼了。
后来他在给祖母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 这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二十七天。有一张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可见当时伤得不轻。
曾经有人引用一段话,说在父亲葬礼的墓前,我被人抱着不知悲哀地吃饼干,似乎是一个智力低下的小白痴。我翻拍了这张相片寄去,详告真情,祈望考虑。但这位作者却大不以为然,说他的根据是某某名人所述,根据确实,倒是我在鸡蛋里挑骨头,大不友好。试问,我这个七岁男孩长得高高大大,——次年我八岁,学校检查体格,身高已达四尺,即公制的一米二二,请问我还是手抱的儿童吗?——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现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柳亚子曾经说过:“近世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确实,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晚年得子,自然喜爱万分,但他爱子不溺子,教子有方,为周海婴日后成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是文化革命的闯将。因他擅写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为人严肃,缺少人情味。其实,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且看他1932年一首题为《答客俏》的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首诗用“於菟”即老虎也懂得爱子作比喻,说明英雄豪杰也应懂得怜家爱子,从而生动地表达了鲁迅热爱孩子的深厚感情。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喜结良缘。1929年9月,生下一个儿子,此时鲁迅已年近半百。夫妇俩人喜孜孜地为孩子起名,起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才决定叫“海婴”。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鲁迅说:“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却绝不会雷同。译成别国文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名字,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自己也是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鲁迅对海婴倾注了全部的父爱。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2时,他一定要轻轻上楼,察看海婴的睡眠情况。如果小家伙把棉被蹬飞了,就细心替他盖好。孩子睡足之后,他就逗孩子玩。孩子倦了,就把孩子抱在自己的手臂上,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哼着催眠曲,用轻柔动听的儿歌,把海婴送进梦乡。海婴病了,鲁迅更是彻夜守护。
海婴渐渐长大了,鲁迅就有选择地带他去看电影。凡是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如《泰山之子》、《米老鼠》及世界风光类的影片,鲁迅常常带他去观看。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响誉世界的“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高兴得手舞足蹈。但鲁迅考虑到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前,怕海婴受到惊吓,终究没有带他去看。海婴为此嚎啕大哭了一场。父亲知道海婴很难过,第二天便耐心地对他说明了原因,答应别找机会,白天陪他去看。鲁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海京伯兽苑。”这件事给海婴印象很深,以后每提及此事,海婴就动情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的爱,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不做空头文学家”
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小说和文章闻名中外,但他对自己的孩子,不是硬性要求他继承父业,而是“顺其自然”,并告诫孩子“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鲁迅发现海婴从小对理工知识有兴趣,便给海婴买来一套木工工具的玩具。小海婴捧如至宝,常常用它敲敲打打,那认真的神态,俨然像一个小工程师在盖房子。鲁迅还常常带海婴到郊外去玩,欣赏清清的河水,鲜艳的野花,嫩绿的庄稼,追逐漂亮的蝴蝶,捕捉有趣的昆虫。野外的新鲜空气,滋润着海婴稚嫩的心田。
一次,鲁迅好友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凝),送海婴一套苏联儿童玩具,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铁制玩具,有上百个金属零件,可以组装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小到简单的翘翘板,大到复杂的起重机、飞机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玩具盒上用娟秀的笔体,写明一共有多少零件,如何玩法。鲁迅和许广平慎重地对小海婴说:“这是何叔叔、何叔母从苏联带给你的,你可要格外爱惜。”小海婴迷上了“积铁”,一玩就是半天。他由玩“积铁”开始,迷上了理工技术,小小年纪,就能拆钟、修锁、装矿石收音机了。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谢谢邀请!
1929年,鲁迅在48岁时,迎来了自己的孩子海婴。
有了孩子后的鲁迅,很是高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的缘故,有人就说这是做人不好的缘故。海婴生性比较活泼,常常弄得鲁迅头昏。有一次,海婴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只好答道:“要吃是可以的,还是不吃的好!”
1936年新年,鲁迅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信中——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早已收到。现在是总算过了年三天了,上海情形,一切如常,只倒了几家老店;阴历年关,恐怕是更不容易过的。男已复原,可请勿念。散那吐瑾未吃,因此药现已不甚通行,现在所吃的是麦精鱼肝油之一种,亦尚有效。至于海婴所吃,系纯鱼肝油,颇腥气,但他却毫不要紧。
去年年底,给他照了一个相,不久即可去取,倘照得好,不必重照,则当寄上。元旦又称了一称,连衣服共重四十一磅,合中国十六两称三十斤十二两,也不算轻了。他现在颇听话,每天也有时教他认几个字,但脾气颇大,受软不受硬,所以骂是不大有用的。我们也不大去骂他,不过缠绕起来的时候,却真使人烦厌。
1936年的新年,鲁迅先生给他的母亲鲁瑞写了一封信。这一年鲁迅55岁,他的母亲78岁。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鲁迅的文笔是非常的辛辣而尖锐的。我们读过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等。但是在这封信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鲁迅,他的笔触非常的细腻。
在这信里边啊,鲁迅重点的介绍了自己最近在吃什么样的鱼肝油,海婴在吃什么样的鱼肝油。同时也告诉自己的母亲,海婴最近的学习状况,我作为他的父亲,经常也教他识字,但是海婴这孩子呀,吃软不吃硬,所以你骂他是没有用的,要通过春风细雨式的这样一种教育方式,才能教育他成长。这等于是在给自己的母亲汇报,自己是怎么教育孙子的。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