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为什么?
这个问题提的是有问题的,严格来说历史没有只选择了儒家,或者法家,而是儒道为表,法为骨。
汉宣帝的儿子刘奭特别迷信儒家,因为他是许平君所生,本来汉宣帝很不喜欢他,但因为这是发妻所生。因为自己在民间之时,全靠许家照顾。汉宣帝就是《乌龙闯情关》这部剧中的刘病已。
汉宣帝治下的西汉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创下了孝宣之治的美名,他不愿意废掉儿子,所以跟儿子说你不能用儒家治世。
当时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杨恽就是使《史记》重见天日之人,也就是司马迁的外孙。
这个时候刘奭说了一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这个时候刘病已表情一变,十分严厉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一句话道出来二千多年来的真相,同时指出儒家的缺陷,不达时宜是儒家最大的缺陷。治理天下就是王霸之道夹着,
霸道指什么呢?就是商鞅帮助秦孝公治理天下时用的方法,商鞅治理秦国的过程是很血腥的,有无数杀戮。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纯粹用霸道行不行,当然不行了,秦历二世而亡给西汉一个教训。所以他们以霸道为骨,也就是苛法为骨,什么为皮呢?儒或道为皮,包装一下,让别人感觉不太恐怖。汉初用道包装,后来用儒,这些就是王道。
这里需要说一下的王道不仅仅只是指儒家,也包括道家。
王霸之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手硬一手软。
霸道确定王朝权威和维护好秩序,王道用来维护百姓的社会关系。商鞅错在哪里呢?他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用霸道去维系,这就好比用力去压一个东西,压到极限自然就反弹了。
历史上有为之人无不用王霸之道治理天下的,必会陷入混乱。
刘奭有没有听父亲的话呢?没有,他真的纯用儒用治世,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西汉由此走向衰落。
他父亲时期是西汉最强大时候,而他却是西汉由强转弱的转折点。
毛主席曾经对他提出批评: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所以历史没有选择了儒家,也没有选择了法家,而是将儒,法,道三家进行组合,构成帝制之下二千多年来的治理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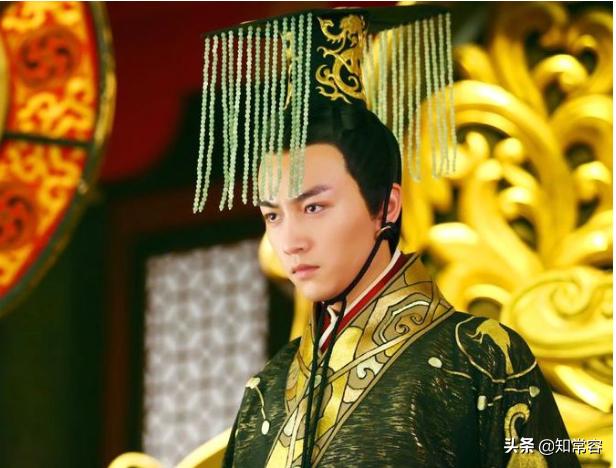
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为什么?
历史选择了通过基因改造夹杂着法家内核的儒家。
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为什么?
畅所欲言。乱侃几嘴。
…………儒家学说,——悬丝诊脉:差不多囊括了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春秋战国后,以孔子为标杆,奠定了儒家思想体系。以至穿越了之后历代朝廷,渗透了草野民间(定为和平演变也不为过);即是蒙古族统治了中华天下,也不得不“顺应民心”:尚儒,尊孔。这在封建王朝,也不失为先进的文明成果。
封建亡,朝纲毁,——此后,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及其迅猛发展,自然格格不入:儒家的“”形式”,盛不了社会的“”内容”。当下,儒家思想,只宜批判接受,不可全盘盲目推崇!传统文化里,儒家定然拥有一席之地。
随口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为什么?
好玩的国学回答的问题,既好玩又有趣。
不管你是否承认,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是已经深入到中国人骨髓的一种主流价值观。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子。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是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但是一种治国方略,是根据时代的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个时期,可能采用不同的治国方略。比如秦国自运用了法家的商鞅变法之后,运用法家的治国理论,迅速强大起来,短短二十多年便统一六国。但秦朝使用韩非子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焚书坑儒,短短十几年就烟消云散。
汉朝建立,最初使用黄老道家的无为思想,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汉朝的前期,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表面上是运用了儒家的思想,其实是对先秦儒家的一种自我否定。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权神授、阴阳等思想中,其实是儒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不过是以儒家的名义存在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其实是灵活运用了各家的思想,从来都是表面上是儒家,一手软,内里面是法家,一手硬。软的一手讲究道德教化,硬的一手讲究强化君权,使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两手都硬。这就是众多学者所说的阳儒阴法的观点。
所以,不能说历史选择了儒家,也不能说历史选择了法家,而是历史选择了儒法兼治。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上的。
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过内心的自省成为善人,即使是有法家思想影子的儒家大师荀子,纵然他相信人性是恶的,但是仍然相信,通过教育和学习,也可以让人变得善良。在这种人性论思想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德治,是善治。因此,主张个人要修养道德,在国家的治理上,要实行以德治为主。
但是,儒家并不是不强调法治,儒家也并非全是战战兢兢的在君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顺民。孔子就说臣子和君主之间应该是以礼相待,而孟子更是石破天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认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孟子同时认为,治理国家,光有德治不行,光有法治也不行,而是要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儒家并非像现在很多人误解的那样,是君主的帮凶,是统治者的走狗,是毒害中国人心灵的坏蛋。
不过,儒家的礼的思想,却又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额内在逻辑。礼不是礼貌,不是彬彬有礼,而是一种上下尊卑老幼的等级秩序。这也成为君主统治百姓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历代王朝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用儒家收拢人心,用法家巩固君权。
法家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的。既然人性是自私的,那么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人必须要相互斗争,以保证自己的生存资源。既然如此,用道德要约束人的行为,那肯定是不可能了,那么就必须用严刑峻法的外在的力量,去规范人的行为。这就是法家的理论逻辑。
如果我们把古代的法家思想,等同于现在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对法家思想的误解,甚至有故意美化法家思想的嫌疑。因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法家强调君主应该运用“法”、“术”、“势”三者的运作来控制臣下,并实行配套的国家政策管治方针,以强兵富国成达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要则。因此法家思想又称为霸道,或可称为“帝王之法”。
法是“法制”,以严刑峻法管治国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赏,有过者则重罚;
术是“权术”,国君要有谋略,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驾驭臣下,对付政敌,以彰显与保持权力地位;
势是“权威”,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与权力,才能驾驭臣下。
从这一点来看,法家思想是站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以暴制暴的思想,这个思想显得有些阴暗,有些阴谋诡计的意思。所以说统治者们不好大鸣大放地运用,只好是偷偷的运用。因为按照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君权,有哪个笨蛋君主不想借助法家思想,来统治万民,巩固自己的权力呢?但儒家的优势在于,始终是关于人的哲学,是关于人如何自立的学问,这个就特别贴近人的心理需求。儒家伦理学上儒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儒家的王道的理想设计中,对统治者也有严格的要求,他们要求统治者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实现王道。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所以,统治者也不想让自己始终扮演吃人的大灰狼的角色,因此,必须推行表面上儒家,内里是法家的治国理念。
所以,不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是实质上是法家的统治者,假装选择了儒家。
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为什么?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学说。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家思想,摒弃其他各家学说,被后人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术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
那么,真的如本题所言,历史选择儒家而摒弃了法家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统治之术从秦朝以来便是“阳儒阴法”,即表面上尊奉儒家,实际上实行法家那一套。
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人性的预设不同。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只不过由于现实的诱惑太多,引起了人的欲望,带坏了人心。儒家相信,只要经过正确的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变成好人。所以儒家重视对民众的教育,重视个人的能动性与价值。
儒家认为,君主和臣子直接虽然有地位的尊卑差别,但却不是赤裸裸的奴役与被奴役,而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要求君主像君主的样子,然后才是臣子有臣子的样子。孔子认为,统治者自身行得正,哪怕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追随你;相反,如果统治者自身不正,哪怕下了命令,百姓也不会遵从。孟子认为,君主善待百姓,让百姓能吃饱穿暖,百姓就会追随君主,战无不胜;如果君主剥削压榨百姓,百姓就可以反抗君主的暴政。
法家则认为,人性本恶,人人都是为利而相互算计、相互倾轧。比如韩非子说,哪怕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利益关系,没有什么亲情。所以法家重视用法令赏罚去约束和规范民众,让人成为君主统一天下的工具。
韩非子指出,君主要掌握三种工具:法、术、势。法即公开的法令,术是不公开的权术,而势则是君主尊贵的地位。君主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三者,才能统御臣民。所以法家的统治术主要是三点:首先,塑造君主的绝对权威,把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其次,颁布法令,奖赏那些君主鼓励的行为,惩罚那些君主反对的行为,就能让百姓服服帖帖的听君主的话;最后,君主还得学习帝王心术,用种种权术手段来调教大臣们,比如在两派之间居中制衡,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法家的方法是效率很高的,他们利用里人心的弱点,即趋利避害变成了忠心耿耿的奴仆,甚至是机器。这比只注重道德说教的儒家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所以采纳了法家学说的秦国以虎狼之师席卷天下,扫灭六国,最终统一中国。
法家那一套确实有用,但是也有很大的问题。法家只用赏罚来规范百姓的行为,就抹杀了百姓的道德感,把百姓变成了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即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百姓能因为利益而服从命令,就能因为利益而犯上作乱。而且法家强调君主的权威,又用法、术来捍卫君主的权威,这就给了君主以滥用权威的机会。如果君主是有为的明君还好,如果君主是无道昏君,就会肆意奴役、压榨百姓,让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其实,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刘邦进入关中,受到了关中父老的欢迎,说明就算是秦国人也早已不堪忍受皇帝的剥削了。
所以后来的统治者们都学乖了,他们继承了法家的政治学说,这被称为“帝王之术”。但是他们又为法家的制度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一方面,统治者用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如三纲五常,给百姓洗脑,让他们自觉维护君主统治,不愿犯上作乱。另一方面,君主又号称自己遵守着儒家的教诲,以仁爱治天下,勤政爱民。
回到题主的问题:历史真的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当然不是。统治者们只是在表面上尊崇儒家,但实质运用的还是法家的统治之术。所以朱元璋见到最纯正的儒家思想——孟子的学说后,会大发雷霆,认为孟子鼓励百姓犯上作乱。因而朱元璋把孟子搬出了文庙,还命令大臣删去了《孟子》一书中批评君主的那些言辞。
一切有为法,如梦亦如露。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梦露居士,为你解读国学经典。
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吗?为什么?
历史选择了儒家不假,然而历史又何曾摒弃过法家?
“法”之创世纪单纯从历史进程看,历史首先选择的并不是儒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周王室逐渐式微,各诸侯国坐大,华夏文明进入一个相当长的混乱时期。相对应的,由于“礼崩乐坏”,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稳定秩序的需求,自知识分子阶层发端,各种思想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史称“百家争鸣”。经过数百年的辩论以及争锋,以“法家”治国的赳赳老秦脱颖而出,最终一统华夏,建立了大秦帝国。秦帝国是中国古代史帝国时代的开端,而帝国体制则是由法家主张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为架构并由此衍生而出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历史首先选择了“法家”。
“法家”之传承“法家”的传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便是帝国体制的传承。秦帝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千多年的帝国史,秦以后各朝,无一例外的继承了大秦开创的帝国体系,虽然其间有过汉初与明朝的诸侯与藩国制,但都没有动摇中央集权与郡县(州县和行省)制的帝国权力架构。
其二便是“法”之本身。中国自战国初期便出现了成文法,秦自公元前356年由商鞅主持开始变法,在奖耕战行郡县之外,商鞅还主持了秦国法律的变革,新法在旧法基础上参考关东诸国律法编就。这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第一部成文封建法典,卧虎地出土的秦简就包括了许多秦法法条。秦以后,汉法基本上承袭了秦法,当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尤其是肉刑法条,再之后,无论唐典宋刑统和大明清律,大体上都是在承继前朝律法基础上略作修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秦法”是中华帝国一部开创性的成文法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一统之后,尤其是“焚书坑儒”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被彻底终结。但百家文化的传承却是薪火相传。直到汉朝时期,随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各家又纷纷出世几乎有重现“百家”盛况的苗头。这一现象在政治层面也有体现,比如郡国并行制,比如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清静无为之治,这是汉帝国在政治层面上作出的新的探索与试验。然而试验的结果却是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所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家学说被纳入了帝国政治体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彻底的禁绝其他各派思想,而只是在帝国的官办教育体系之内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标志性事件便是汉武帝将帝国官学太常寺内的非治儒学的太学博士全部罢黜,自此,儒学在形式上一统了帝国教育体系,并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的官僚。
但帝国对其他学说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公元前134年,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年,受诸儒生排挤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自荐并得以进入帝国中枢。主父偃本人早年修习纵横之术并百家之学,他于公元前127年主持的旨在削弱诸侯国势力的“推恩令”也极具纵横家色彩。这说明在官办教育体系之外的帝国体制对儒家以外的学说和人才还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主父偃得汉武帝任用后,曾年获四迁,官至中大夫。
最后,“罢黜百家”并不是把其他各家学说给禁绝了,而是将其中对帝国统治有利的内部纳入了“儒家”学说。比如儒家本来主张施行仁政,然而一味的仁政在实际执行中的可操作性其实是非常低的,于是汉朝的儒学吸取了法家的刑名之学,从而总结出刑德相辅的手段。由此我们可知,百家并未被完全罢黜,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改头换面后被纳入到儒家学说中。
“儒”+科举制=唯一“主旋律”“儒家”真正在帝国中占据“主旋律”,其实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其标志便是科举制的产生与完善。
科举制为平民百姓提供了进入帝国官僚体系的通道,打破了豪门大族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把控,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帝国的官僚选拔程序与庞大人口基数的结合,能够以当时最高效率与最公平的方式完成官僚的选拔,从而更好的维护与巩固帝国的统治。
由于科举制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这就确保了“儒家”学说在帝国体制——不仅是教育体系内——排他性的独特地位。
此“儒”非彼“儒”除前面提到过的兼容并蓄了其他学派的部分学说之外,儒家本身也在适应着帝国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着不断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董仲舒结合阴阳学说极大的发展了孔子的“朴素的天人感应”学说,并由此引申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巩固了皇帝权力的合法性。但对“儒学”来说,这一改变无疑是动摇甚至于颠覆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世界观。
另外,原生态儒学主张的“克己复礼”——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要求个人以“礼”的标准约束自己,二是个人遵“礼”那么社会便会回复“礼”的秩序,这里说的礼,即是《周礼》。然而帝国体制下的儒学,《周礼》的秩序被瞒天过海的替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治统治,尤其是个人行为层面更是被加入了许多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中央集权服务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儒学”被帝国体制驯化了。
非人力所能左右最后总结一下,所谓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这说法不严谨。历史并不会因为这一学说是儒、法或道而决定取舍,也不可能是某些帝王的个人喜好,而确实是有某些深层次的原因。这一原因便是国家体制由“诸侯封建制”转变到帝国体制的需求。
西周的“诸侯封建制”在初期是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但随着经济水平尤其是技术手段的提高,诸侯封建制便不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经济要更好的发展需要有更高效的统治方式,即帝国体制。这一转变是必然的,只要经济尚有向上的发展空间,这一过程就必然会到来而且不可逆。
而百家之被取与被舍,并不是因为它是法或儒,而是因为它的内容对于帝国体制来说有可取之处,比如法之郡县制,之刑名学,儒之政治伦理说,之天人感应说。而帝国体制对于思想有大一统之需求,所以才有了兼容了其他学说部分内容的新的“儒学”。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