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的“汉奸”之一,中行说为何那样死心蹋地的出卖国家呢?
他本身就是太监没有后顾之忧,中行说是汉奸的鼻祖,也是当年帮助匈奴对付汉朝,甚至用最早的“细菌战”害死了汉朝著名的大将军霍去病。原本作为宫廷太监的中行说,最终却变成了最早的汉奸,这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宗室女),说不行,汉强使行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史记·卷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中行说已经对汉文帝说了,如果他硬是要自己陪翁主和亲匈奴,那么自己将来一定会变成汉朝的心腹大患。但是汉文帝并没有理睬他,强行让他陪嫁。
汉朝开始国力孱弱,只能以“和亲”政策来休养生息。然而除了远嫁的公主,陪同前去的人也都是受尽了罪——匈奴之地终年苦寒,风俗野蛮而生活困苦,还远离亲人可能最终再也无法与家人相见,所以谁都不愿意前去匈奴。
相传,宫廷内监中行说得罪了汉文帝的窦皇后(汉景帝刘启的生母)所以才选中了中行说陪同宗室翁主远嫁匈奴。对于中行说来说,这就是非常惨了惩罚,他本身就是个断子绝孙的太监,所以他对汉廷也是充满了仇恨。
中行说在匈奴多年,挑拨匈奴对汉朝的仇恨越来越严重,胃口也越来越大。当年他对汉文帝所说的毒咒最终也确实变成了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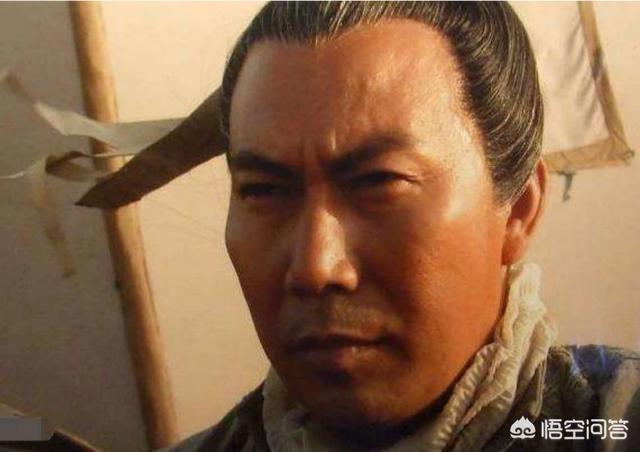
作为中国最早的“汉奸”之一,中行说为何那样死心蹋地的出卖国家呢?
中行说(zhōng háng yuè),人称汉奸之祖,汉文帝时期人物。
一个能成为汉奸,大抵不过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有人是被逼无奈当了汉奸,当着当着当真了,这是客观变主观;有人是自己打定主意要当汉奸,然后就真的当了汉奸,这是主观化为客观。中行说无疑是后者。
但中行说主观想当汉奸自然也有导火索,导火索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他因为自身遭遇,觉得这个国家、政府压榨我,我不满,我要叛国。这种想法,在历次的农民起义军也有,但人家是实在活不下去了,中行说的情况大不相同。
中行说曾是宫廷宦官,野史传闻他得罪了窦皇后,所以被汉文帝选为陪送公主到匈奴和亲的使者。中行说有没有得罪窦皇后不知道,反正汉文帝派他去是没错的。
当时匈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嗣位,号老上单于。此时汉朝仍在积蓄国力,国内的诸侯国又不老实,所以汉文帝选择再派宗室女去和亲稳固和匈奴的关系。
当时汉朝对匈奴的了解很少,只知道那里是化外蛮夷之地,自然条件艰苦,再加上匈奴的风俗习惯(继婚制等),远嫁的“公主”(一般不是皇帝的女儿)往往很受罪,陪同人员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没谁愿意去。
中行说也不想去,但皇帝派了使者点名要他去,躲也躲不过,最后只能上路。临走前,中行说已经笃定叛国了,他扬言道:“必我也,为汉患者。”(我如果到了匈奴就肯定会威胁汉朝)
就这样,中行说带着他的誓言走了,他的话很不被人重视,但其实他比很多人都更有机会去实现,因为他是宦官,没有后人,没有顾虑,完完全全一条滚刀肉。
中行说说到做到,一到匈奴就投靠了老上单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中行说先后侍奉老上单于、君臣单于和伊稚斜单于,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而他对匈奴的贡献,还真当得起这名号,只可惜,这些贡献是在汉朝的血泪上堆积而成的。
中行说教匈奴人收税计税方法,加强其战争持续能力,并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要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的储备,积极为入侵汉朝做准备。
汉文帝时期,汉匈战争汉朝处于劣势,只能送公主送东西求和平,中行说一再催促汉使按时送达,不然就威胁南下劫掠,给匈奴画好了战略大路。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讨伐匈奴,匈奴不敌,人马死伤惨重。
不得不说中行说很细心,也很阴险。他发现一些将病死的牲畜浸在池塘后,食用过其中水源的士兵,轻则腹泻大病、重则死亡。于是他建议匈奴巫师先诅咒病死的牲畜,然后把它们埋到汉军进军路线的水源上游,汉军食用后,许多人出现中毒症状,据说霍去病死因,也可能是食用了这种水,生了重病英年早逝。
中行说在匈奴数十年,为匈奴立下汗马功劳,也使得汉朝人对之痛恨不已。据野史记载,当时汉朝使臣和中行说还有一段对话。
汉使:你何苦为异族做事,出卖本族虚实,看你的计策,比匈奴人都狠,如果你痛恨文帝,如今文帝已崩。何况你中行一族都在汉族生存,匈奴一来,覆巢之下,你中行一族也难逃一死。
中行说:我早就不痛恨文帝了,我也是汉族人,我已经不容于同族,死后魂魄不能归乡,必成孤魂野鬼,我只是妒忌那些国内的人,我看不得他们过得比我好,我要他们一日三惊。
中行说究竟有没有这么说不清楚,毕竟是野史,有可能是作者自己设计的台词,不过中行说已经用行动说明了一切。
作为中国最早的“汉奸”之一,中行说为何那样死心蹋地的出卖国家呢?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曾经打得刘邦满地爪牙,横扫北亚,统一了整个大草原的匈奴史上最牛枭雄,冒顿单于病逝。敌国巨星陨落,此乃汉之大幸也,一时间,汉朝野兴奋,举国欢腾,汉文帝刘恒苦大仇深的脸上,竟也露出了一丝快意。
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继任匈奴单于,号为“老上单于”。
刘恒乃决定继续施行和亲政策,遣使送宗女远嫁匈奴,谋求帝国和平发展环境。
和亲乃关乎帝国安全之大计,刘恒不敢怠慢,他精心挑选了个最漂亮的翁主(汉时诸侯王之女称翁主,与皇帝之女称公主区别。因皇帝之女须由三公主婚,故称公主;而诸侯王之女其父可以主婚,故称翁主),又选了个最机灵的太监做翁主的仆从,然后开开心心的送他们去媾和匈奴
但是刘恒错了,他错就错在挑的太监太机灵,以至机灵的投降卖国当汉奸了。
这个太监,就是中行说。
中行说早先接到这个伟大任务的时候,牢骚满腹,非常不乐意,因为他不想去寒冷荒凉的匈奴吃苦;但刘恒考虑到中行说原系燕人,临近朔方,多少了解一点匈奴习俗,对远嫁的翁主可以多点照应,故不予理会他的不满,仍然坚持派他去。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被放逐天涯而有苦难申、且从此一生都不能再归故土,于是中行说出离了愤怒:既然祖国不要我,那我也不要祖国了!因此他在临行前立下了一个可怕的誓言,发誓自己必将成为汉廷最大的祸患。
没有人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小人物也可以掀起大风浪。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这个小人物的这句誓言,竟成为了汉民族最大的诅咒,如蛆跗骨,遗祸数世。
中行说跟随和亲车队抵达匈奴后,立即向匈奴投降,把他知道的汉朝机密一股脑和盘托出,成为一名大汉奸。老上单于对这个机灵无比、又能说会道的汉奸非常喜爱,把他放在身边担任参谋,凡有中国之事,必要向他请教。
经过二十几年的和亲与文化输出政策,匈奴人早被中国的伟大文明同化的找不着北了,他们皆以吃中国美食为乐,穿中国丝绸为荣。特别是在名士贾谊的提议下,汉文帝采取了“五饵”之术来引诱、软化匈奴人,即用盛装华车引诱其眼,用珍馐美味引诱其口,用音乐美人引诱其耳,用奴婢豪宅引诱其腹,用礼遇降者来引诱其心。总之就是要用糖衣炮弹把匈奴给和平演变了!
中行说一看这怎么行,赶紧跳出来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我大匈奴之衣食、用度、风俗之特异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则国人皆仰慕于汉,长此以往,汉只需以二成汉物收买,则匈奴人尽归于汉,成其属国矣。此皆汉人用心险恶,欲同化我族,单于不可不防。依小人之计,不如这样,今若得汉丝绸,则以之驰草棘中,衣裤必裂敝,可示不如毡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则皆弃之,以示不如奶酪之便美也。”
老上单于恍然大悟,原来汉朝人这么阴险,竟用汉之美物来腐化我匈奴人之心志,这可太糟糕了。于是他接受中行说的建议,在匈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去中国化运动”,从此只抢汉朝的子民与粮食,不再使用汉朝器物。
在人类没有步入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里,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文化弱后的民族,其独立性往往是决定其兴亡的重要因素。而民族的独立性必须要建立在顺应其地区自然特征的基础之上。看来,中行说虽然只是个死太监,但颇有见识,可称得上精通民族文化心理的大学者了。
中行说还唆使匈奴产于在和汉朝书信来往时,多用挑衅之语,称谓上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称汉文帝仅仅是“汉皇帝”,以培养匈奴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尊情绪。
后来,中行说还帮着单于记事、记账,教匈奴人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行人口普查,资产清查以及畜牧业发展状况。如此他一面反对汉化同时又在匈奴散播文明的种子,尽心尽力辅佐敌酋,并极力煽动民族仇视情绪,其种种汉奸所为,全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誓言,让自己的祖国万劫不复,让过去那些轻视自己的人付出代价!!
图:电视剧《大风歌》里的中行说
刘恒欲哭无泪,汉苦心经营数十年之和亲政策,竟一朝毁于中行说一人之手。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刘恒又接连派出汉使,向匈奴宣扬中国之礼义,欲恢复和亲,保住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机会。
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不等老上单于发表意见,中行说第一个就跳出来阻挠道:“匈奴虽无礼义,然约束简单而易行,君臣一体而可持久,不比中国繁文缛节,毫无益处。尔等中土庸人,不必多言,唧唧歪歪,面目可憎。但教把汉朝送来钱粮,留心检点,果能尽善尽美,便算尽职,否则秋高马肥,便要派遣铁骑,南来践踏,踏你个尸横遍野片土不留!”
汉使哭丧着脸说:“中行大人何出此言,你不也是汉人么?”
中行说大怒:“谁说我是汉人了。你才是汉人,你全家都是汉人!我中行说,是一个伟大的匈奴人!”
至此,汉朝以和亲及礼义羁縻匈奴之政策,全面破灭,在中行说的挑动下,匈奴几乎每年都要派兵南下袭扰汉之边郡。因中行说熟知汉境关隘险阻,懂得要害所在,又稍通谋略,教匈奴大军拆作多部,分头出击,而导致汉汉军在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捉襟见肘,防不胜防,云中、辽东、代郡等边地每年都有万余人被掳为奴隶或杀害。特别是汉文帝前元14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铁骑南下,直至临近长安的甘泉宫一带,汉军大发车骑苦战月余,也未取得有价值的的军事成果,最后仍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匈奴人带着抢掠所得扬长而去。不过,好在匈奴人对汉朝并无领土野心,他们每次南下只为劫掠牲畜和人口,这种心理大约就像牧羊人一样,把羊养肥了再杀,汉朝这边一旦在边境地区积攒够一定数量的子民财帛,也就到了他们南下“杀羊”的时候。而汉朝所奉行的和亲政策,就是延缓他们南下“杀羊”的频率,以换取宝贵的时间恢复国力。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中行说仍然没有停止他的汉奸活动,竭尽所能不断破坏汉匈两国的关系,每年乐此不疲的与汉使斗法。其实老上单于在晚年已经略显疲态,答应了汉朝的和亲,可惜他没多久就死了,他的继任者军臣单于年轻气盛狼性正勃,再加上中行说在旁推波助澜,他竟在娶了和亲公主捞了大笔嫁妆不到两年后,就出尔反尔又大举率军南侵。结果,好不容易安生了几年的汉匈边境,狼烟再起,生灵涂炭,无数百姓在烽火与兵燹下哀嚎、惨死,马踏成泥。
中行说以事实证明:卑贱之人也不是好惹的,皇权可以国家与民族之大义践踏人权,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无私奉献与忍受的,逼到极处,总有极端之人将一切忠诚与廉耻抛弃,背叛国家,背叛民族,在所不惜。
人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可恨之人也未必没有可怜之处。中行说就是一个可怜的太监,生理不全,地位低下,本来也就希望苟存于世,蚂蚁般度过一生则足矣,结果却被抛到蛮荒之地,注定服侍和亲的宗女而老死异乡。他穷极生恨,从此被仇恨迷失了双眼,疯狂报复,最终殃及无数汉朝百姓——如此一生,岂非可怜复可恨!
作为中国最早的“汉奸”之一,中行说为何那样死心蹋地的出卖国家呢?
中行说的一生由一句誓言证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这句誓言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千年流芳还是遗臭万年,这家伙是不会管的,一个如此有个性的人真的是很值得人们反思。
虽然这家伙是地地道道的“历史第一汉奸”,可他也是汉文化传统最早的反思者,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反传统斗士,而且他的见识句句在理,直指汉文化弊端。可谓一针见血。
文帝时,当时汉朝最大对手,匈奴的首领是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即位时,文帝因为国家实力问题,还没有想过要大规模开战,于是和亲成了对匈奴的政策。
宦官中行说这个汉奸,就是因为一次和亲而远走匈奴的可怜人,其实他是不想去的。可是不得不去,而他的任务也不单纯过去是要做间谍的。临别之前,中行说对皇帝说,我不适合这个任务想借故推辞。汉文帝说,非你不可,无奈中行说只好悻悻起程,临行前他曾经对人说:“我本不想去,非逼我去,别怪将来我为害汉朝。”听到这句话的人付之一笑,你算什么玩意,一个阉人而已哪知道中行说一语成谶。
出发之前的中行说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叛变,一见老上单于,就立马投诚,成单于亲信,兑现他的誓言。匈奴与汉和亲,最大好处就是,得到许多嫁妆,这嫁妆有食物有衣服,而匈奴本来就是苦寒之地,游牧民族除了牛羊肉吃,牛羊皮穿,就没见过精致衣服和可口食物,所以,每次和亲都是匈奴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衣服好看食物好吃啊。
这个时候中行说对老上单于进谏说:“匈奴人口比不上汉朝一个郡,爱穿汉衣,爱吃汉食,长此以往,汉朝物品输入匈奴十成中一二成,就足使匈奴降汉了。”(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根源)
听到这话的单于和众人都满头问号,因为文化水平太低吗?无奈中行说只能继续解释:“穿汉朝丝衣,骑马在杂草荆棘中奔驰,衣裤会挂破,哪比得上毡裘耐用?汉朝食物虽可口,哪比得上我们乳酪方便美味?”这番话说服了众人,从此就放弃了汉朝的衣食。(奢侈而舒适的生活是一个民族堕落的开始,中行说让匈奴人明白这个道理)
说完这句话之后,中行说开始确立其自己在匈奴的地位,之后他也没闲着,而是教单于还有他的助手开始学习数算,学习各种文化。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他是想自己不那么孤独,有人可以理解他说的话有何深意。
关于中行说的思想,在一次和汉朝使者的对话中可以表露出来。这段对话及其深刻而又直指汉朝弊端。汉朝皇帝和单于所通书简,历来长一尺一寸,上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字样,之后才记载赠送的物品和言语。中行说教授单于有样学样,但是回复的书简,要比汉朝打,定为一尺二寸,封印也要比汉简大,称呼也要更傲慢,“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然后才记载赠送物品言语。其实这主要是讽刺汉朝总是做表面文章。
之后汉朝使节看不惯匈奴和汉朝不一样风俗,说匈奴是蛮夷,中行说就亲自出面和汉使辩论。汉使讥讽匈奴不尊老人,中行说辩道:“按汉朝风俗,征兵时,父老岂有不置办衣食,欢送子弟的?
匈奴崇尚攻战,老弱不上阵,因此才把优渥衣食供给少壮,这样才能打胜,这是保家卫国,怎么说得上轻视老年人呢?”
汉使又说:“匈奴父子睡一个帐篷,父死,儿娶后母;兄死,娶兄妻为妻,这是逆天乱伦,也没冠带服饰礼制,又缺朝廷礼节。”
中行说辩道:“匈奴风俗是吃牲畜肉,喝牲畜乳,穿牲畜皮毛。放牧时要随时转场,才能保证牲畜按时吃草喝水。战事紧急时人人都练骑射,战事缓时人人享受生活。
人们约束轻,生活就简易;君臣关系简单,国家事务再繁,也像一个人身体一样好使。哪像你们,虽称礼义之邦,君臣却相互猜忌,大量使用劳力去修宫廷,耗尽民力。老百姓耕种本为衣食,建造城郭本是为保护自己,可这样一来,战事紧急时候没时间练习攻战,和平时候又不能休息,还出劳力。
匈奴风俗,父子兄弟死,娶他们妻子为妻,是为保全种姓。匈奴虽伦常紊乱,但也一定要立本宗族子孙。哪像你们,虽遵伦常,可亲属关系疏远时候互相残杀,改朝易姓常有。
你们这些只会在土屋里生活的汉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得说;以上论断非常深刻,是尖锐而有道理的。从此后,汉使再想和中行说辩,中行说就高挂免战牌,而且斥责汉使:“别说了!但教你们汉朝送来的衣食等物品数量充足,尽善尽美,就是你们职责;否则等秋高马肥,就大举南侵!”汉使往往无言与对。(打的赢的靠打,打不赢的才靠嘴巴)
老上单于从此以后对中行说言听计从,在中行说谋划下,匈奴屡侵汉境,成为汉朝最大边患。汉朝没法,也只好照例和亲。
老上单于死后,他儿子军臣单于即位,中行仍然辅佐他,匈奴也仍然不断给汉朝制造边患。直到汉元帝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匈奴才开始衰落下来,不仅属国都已背叛,而且内部也分崩离析,不再成为汉朝的心腹之患了。
中行说虽然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可他也是汉文化最早的反思者,最早的反传统斗士。他对汉朝礼义制度的抨击,句句在理,一针见血,阉人的卑贱身份也刺激着中行说要去建功立业。“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这句著名的誓言,一定也是中行说的心声。在他看来一个将它抛弃的祖国,并不值得留恋,这也是他死心塌地跟随匈奴做汉奸的原因,其实他说的又有那一句是错的?每句都对针针见血!
作为中国最早的“汉奸”之一,中行说为何那样死心蹋地的出卖国家呢?
老上单于上台后,汉文帝刘恒为了信守盟约,延续和亲的传统,便挑选了一位王族女子,准备嫁出嫁匈奴。
刘恒为和亲使团选择了一名随行官。当时宫内有一名宦官,叫中行说,人很聪明,能说善辨,非常机智。中行说出生在燕国,靠近匈奴,对北地的风俗人情比较了解。刘恒就差人通知中行说,要他做好准备,随时启程。
没想到中行说对这项使命不兴趣,一口拒绝了。他在皇宫中,因为能说会道,善于巴结后宫的贵妃们,左右逢源,也算有点权势。现在突然一纸命令,要他离开富丽堂皇的后宫,去到寒冷荒凉的匈奴,心里很不乐意。
刘恒大怒:你不过是小小宦官,居然也胆敢讨价还价,你不去,偏让你去。
触犯天威,中行说没得选择。他恨恨地诅咒说:“非让我去不可,我一定会报复,把汉室搅得不得安宁。”
心怀不满的中行说跟随和亲车队抵达匈奴后,立即向匈奴投降。
作为和亲随从人员,中行说的使命是促使汉匈两国和平相处。但他因为一己之私,把什么国家责任、什么民族大义,全抛到九霄云外,一心钻营如何来报复汉文帝,把汉、匈两国关系搅得一团糟。
中行说本是一名宦官,溜须拍马是他的本事,况且他口才极好,善于奉承阿谀,居然深得老上单于的宠幸。他不再以汉人自居,而是以匈奴人自居了。
从此,中行说不遗余力地攻击汉帝国的方方面面。
汉帝国苦心积虑的和亲政策,几乎毁于中行说一人之手。
当时汉帝国的丝绸在匈奴很受欢迎,匈奴许多贵族都以穿着中国丝绸为荣,同时,中国的美味食品,也很受匈奴人欢迎。
中行说不高兴,跳出来说:“匈奴的人口,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大郡,但是却可以无敌于天下,就是因为穿着饮食上,从来不必仰赖中国。现在匈奴上上下下都喜爱中国的衣物食品,以为至宝,这样恐怕中国只需输入一二成的物品,匈奴怕是要全国上下归降汉室了。”
老上单于觉得中行说所言,有些道理,所以就不再稀罕汉帝国的丝绸、美食。
中行说以前在汉宫时,粗通文书算术。到了匈奴以后,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教给匈奴人,如何建立人口簿册,如何登记牛羊数目,分别条目记事。这在汉帝国只不过是粗浅的学识,老上单于却以为中行说是个博学多才的人,非常器重。
中行说还不知足,尽出馊主意,力图破坏汉匈两国的友好关系。在以往两国文书中,汉帝国致匈奴的文书是有一定规格的,书简长一尺一寸,文书的固定格式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但是匈奴致汉帝国的文书却没有固定的规格。
中行说就搞了个花样,设计的匈奴书简长一尺二寸,比汉帝国的书简长了一寸,书简上的封印也比汉帝国的封印要大。更夸张的是,中行说设计了一个固定格式,写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俨然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可以说,中行说无所不用其极,来挑拨汉匈两国的关系。不仅如此,还极力怂恿老上单于不断在汉匈边境上挑起事端。
汉文帝刘恒当初执意让中行说充当和亲随行官前往匈奴,不想此人居然惹出这么多的是非,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作为中国最早的“汉奸”之一,中行说为何那样死心蹋地的出卖国家呢?
中行说的的确确是个汉奸,但他这个汉奸不仅做得“有言在先”,更做得“理直气壮”,因为是大汉王朝把他逼成了汉奸。当然,他在汉奸这个位置上干的也是有声有色,甚至还发明了“生物战”这种大规模杀伤模式,给汉朝军队带来重大打击。
汉朝初期,因为和匈奴的国力对比太过悬殊,无奈采取“用女人换和平”的和亲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嫁出宗室贵女,以陪嫁的方式给匈奴送去大批好东西,换取对方不劫掠边境。汉文帝即位后,仍然延续了这个政策,而陪着宗室贵女去匈奴和亲的人员中,就有宦官中行说。
嫁到匈奴的女人本来地位就不高,随行的手下身份更是低贱,更何况匈奴的生活条件远远不如大汉,去匈奴这差事实际上和送命没什么区别。中行说自然不愿意,他找到和亲的使臣直接表示:我不想去。使臣根本没在乎一个太监的呼声,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中行说当即表示:我要去了匈奴,一定做汉奸。《史记》原文记载道:必我行,为汉患者!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强迫我去,我一定会成为汉朝的祸患!
中行说到了匈奴,果然立刻就选择了被判大汉,并因为聪明才智以及对大汉的了解,受到了单于的重视。他把对大汉的仇恨完美转化为动力,连续为匈奴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建设了以下几方面的汉奸工程
谏言单于。匈奴人一直对大汉的特产眼红不已,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不惜在边境烧杀抢掠。中行说规劝单于说:大汉的东西虽好,但却不适合匈奴。他们出产的帛布穿起来舒服,但却不利于骑马战斗,比不上我们的皮甲。他们的美食的确味道上佳,但不方便携带,比不上我们的奶酪和肉干,匈奴人不该沉湎于美服和美食之中,最后堕落成汉朝那样贪图享乐的国家。
中行说的劝谏,明显阻止了汉民族对匈奴的融合,他希望匈奴永远保持本色,成为汉王朝的心腹大患。
传授技能。匈奴人茹毛饮血游牧为生,在科学技术上毫无建树。中行说将汉王朝的算数之法传授给了匈奴人(《史记》: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牧。),让他们能够计算牲口、粮草等物质的数量,这无疑为匈奴的后勤补给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间接支援了战争。
发明生物战。中行说的确是智能出众,他发现马匹等牲畜如果病死在池塘或河流里,人喝了带细菌的水也会生病或者丧命,于是建议匈奴人将病死的牲畜扔进汉军行军路线的水源地里,果然让很多汉军出现了中毒症状,这正是最早出现的“生物战”雏形。据说大名鼎鼎的霍去病就是因此而患病,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著名的贾谊曾多次上书朝廷,希望汉朝能: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将中行说的危害和单于相提并论,可见其做汉奸有多卖力!
假如当年中行说没有被逼去匈奴,以他的聪明才智,会不会成为司马迁、蔡伦和郑和那样的人物呢?
原创不易欢迎关注。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联删。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