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乌台诗案已经把旧党大佬司马光、当朝驸马王诜牵连进来。目的已经再明显不过。新党就是要把旧党一网打尽。
所以,乌台诗案,不是一般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案件。这个政治案件的关键突破口和全部要害,便是苏轼。
苏轼被重办,旧党牵连入网;苏轼被轻办,新党功败垂成。
但是,苏轼为什么能逃过这场劫难呢?
苏轼苏子瞻,必须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一个好朝廷、遇上了一个好官家。
换个时代、换个朝廷,哪怕换个官家,苏轼的结果,都不会只是贬官黄州。
什么是好时代?
一个能跟你讲理、能让你讲理的时代,就是好时代。
人都是讲理的。讲理是人的底线。所以,跟你讲理、让你讲理,应该是常态。咋还成了好时代的标志?
人都是讲理的,这个“因为”的前提成立,但推不出“讲理是常态”这个“所以”的结果。
皇帝凭啥要跟大臣讲理?领导凭啥要跟下属讲理?力量大的凭啥要跟力量小的讲理?“春秋无义战、强者定章程”,春秋诸侯们,哪个讲理了?
实力可以决定一切,那就不需要讲理。
即便跟你讲理,也要看讲谁的理。可以跟你讲理,但要讲我的理,而不讲你的理。这当然也叫讲理。简单说就是:可以跟你讲理,却不让你讲理,最后则杀人还要诛心。
那么,在乌台诗案中,新党执政的大宋朝廷与支持新党的大宋官家,到底是怎么跟苏轼讲理的?
01.乌台诗案的渊起:苏轼确实在诋毁新政苏轼到底有没有错?
必须有错。
当时,大宋的官僚系统都在学习王安石主义、实施王安石改革。但是,苏轼呢?他不讲王安石主义、也不支持王安石改革。非但如此,还要各种诋毁。
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畅销书、没有现代传媒,苏轼怎么诋毁新法?他天天在家骂新法、骂王安石,这个影响也就止于苏夫人和苏公子。即便开坛讲学,也就是影响一下自己的学生。
苏轼的手段,是发朋友圈。
我发个朋友圈,然后就能诋毁新法、阻挠新政、危害国家吗?你当然不行,苏轼却可以。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如果八大家排序,苏轼必须能进前三甲。论写诗,苏轼是北宋诗坛领袖,即便把苏轼拉到唐朝,他也能跟大唐群星比比谁更亮。此外,还有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蜀学的首席宗师,甚至,苏轼对道教、佛学都有精深的研究。
集诸多名号于一身的苏轼,完全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发个颠覆新法的朋友圈,就能引发政界、学界的一场骚动。苏轼是能够带节奏的意见领袖。
啥叫意见领袖?“别跟我讲什么王安石主义,我就觉得王安石就是个人渣,不转不是宋朝人”,然后,一百万条转发。这就是意见领袖。
苏轼到底发了什么朋友圈?
最初,被新党抓住把柄的一条“朋友圈”,不是苏轼的诗,而是苏轼单独发给宋神宗的“短信”: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公元1079年,苏轼赴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地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但是,奏表中的这句话,却刺激了新党。
啥叫“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苏轼愚昧不堪,这叫耿直;跟不上新时代,这叫不投机;没法跟弄潮儿的新党们一起玩,这叫不媚俗。
啥叫“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过分解读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岁数大、不生事,这叫不折腾;正好可以去地方牧养小民,这叫能养民。
新党不干了,然后开始弹劾苏轼,你这不是例行公事谢圣恩,而是含沙射影骂新法。苏轼啥反应?苏轼非常硬,你们说对了,我就是骂你们了,你们还能咋地?
新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这篇奏章,没啥可挖掘的;但苏轼的“朋友圈”却可以各种挖掘。
02.苏轼的“朋友圈”:他是怎么诋毁新法的在古代发朋友圈,无外呼两种形式:
一种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来,如“致司马公:王安石不是东西,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
一种是写诗填词做文章,苏轼主要是写诗,所以才叫“乌台诗案”,这就肯定算。乌台,即御史台:诗,才是案,即苏轼的各种反诗。
苏轼,到底写了哪些“反诗”?
为了罗织罪名,新党肯定要过分解读。但是,有些诗,都不用过分解读,苏轼就是在骂新法。其中,以《山村五绝》最为代表。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关键是这句“迩来三月食无盐”,七十老翁已经很可怜,咋还三月不吃盐?因为北宋搞了食盐专卖,老翁买不起。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青钱,即青苗法给老百姓的农业贷款。贷款是拿到了,但转眼之间,就在城里花光了。因为北宋政府止不住地要与老百姓做买卖。所以,搞了各种高消费的娱乐项目,进城的农民刚拿到钱,就被政府的娱乐产业给赚走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看不上新法也看不上王安石。后来他跟王安石言归于好,但那是后来。当时,这两个人就是水火不容。
新党的目的,是为了干掉苏轼吗?
苏轼只是突破口。新党的真正目的是打击不满新法的整个旧党,关键重点是旧党大佬司马光。苏轼,自己写诗发朋友圈,你只能定他的罪,怎么能打击旧党呢?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谁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谁就是在影射朝廷,然后谁就是同党。
那怎么证明点赞呢?有书信往来就算点赞。
“子瞻兄台见:你写得《山村五绝》真好,鞭辟入里,像匕首、像投枪,您就是我大宋的鲁迅!此致敬礼”。这就必须算同党了,然后牵连入案。
实在不行,那就看苏轼给谁写信了。这个也可以算。苏轼给司马光写信了,而且还写了首诗,即《司马君实独乐园》: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你苏轼这是啥意思?苏轼也坦荡:我就是想说天下人都盼着司马光出来执政,因为你们新党太垃圾。司马光收到这种“反诗”,为啥不上报朝廷?看来,司马光也是同党。然后,司马光牵连入案。
关键是苏轼还跟当朝驸马王诜过从甚密。
御史台去抓苏轼的时候,苏轼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蹲监狱了。那是谁通知的?驸马王诜通知了苏辙、苏辙通知了苏轼。这就是大臣勾结皇亲国戚了。这种问题,在哪朝哪代都是犯忌讳的事。顺藤摸瓜,还查出苏轼收了王诜的钱,而且二人也有诗文往来。也就是说王诜也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了。于是,王诜牵连入案。
新党的特点,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按照谁给苏轼点赞、谁就是同党的操作模式,那到底能折腾进去多少人?
39人。这就是苏轼的关系能量,绝对是旧党中的“名媛交际花”。所以,新党选择苏轼作为打击旧党的突破口,绝对是英明之举。
03.古代司法的高峰:大宋朝廷是怎么跟人讲理的“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程序正义。
程序,一个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概念。实际上,完全可以换成一个通俗易懂的名词,即手续。要去结婚,先到民政局领证,领证是手续;打击坏人,先要走法律流程,流程就是程序。
把手续强调过分了,难免手续异化。于是,证明你是你、你爸是你爸的问题,肯定要出现。有些坏人,即便明知道它干了坏事,但手续太复杂、流程走不了,坏人也关不进监狱。
实现正义,却非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手续太复杂、然后复杂到过度,正义还怎么追求、还怎么实现?
“努力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给这句话上画个重点,重点应该是什么?是感受。
程序或手续的意义,只是兼顾了客观的真实,主要是强调了主观的感受。真实世界是不可约的复杂,任凭谁也无法穷尽,而主观的感受却可以。
跟不跟你讲理、让不让你讲理,都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历程,而是实现主观感受的最大公约。正义也好、公平也罢,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问题。实然可以求真,但从实然跳不到应然。所以,价值判断无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这时候,就一定要以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来追求了。只有“看得见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手续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对手续、对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么讲理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台根勘所
御史台最早设立于东汉,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这里来审理。苏轼这个案子,肯定重大。因为新党一定要往大里整。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又称乌台。因此,苏轼一案,才称乌台诗案。
御史台首先发动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状,神宗皇帝诏曰可。于是,从弹劾变成案件,对苏轼的立案调查正式展开。
御史台派出官员前往湖州缉拿苏轼,然后送交御史台的根勘所,进行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专门负责审理诏狱的机构。
宋神宗不仅下旨审理,而且还派了一名宦官跟进案件。所以,苏轼一案,就变成了诏狱,即皇帝亲自下诏督办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诏狱这个层面,那苏轼不被定罪弄死,也被严刑打死。但是,大宋时代是跟你讲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诏狱也要讲理,具体表现就是讲程序。
大理寺和审刑院
御史台只负责案件的审讯。即便是审讯,也不是御史台一家说了算。因为大宋官家还要派人跟进。
皇帝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会同御史台搞联合审讯,这叫杂治。
案件审查清楚之后,审案的官员们要制作好口供,这叫供状。
审讯工作到供状这里为止。然后,御史台就可以结案了,这叫结勘。
皇帝还要派遣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进行当面问话,这叫录问。
犯人在录问的时候翻供了,这叫翻异。一旦出现翻异,那皇帝就必须另外派人重审。
录问环节,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赵高审李斯案。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赵高为什么使其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侍中”?就是担心李斯翻异。
犯人既不申辩又不翻异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吗?不能。因为御史台只有审讯的权力,却没有定罪的权力。
御史台完成供状环节之后,要将供状递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
如果把御史台类比为现在的最高检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现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序还没走完。
检法之后,要出判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这个判词,还要上报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完毕之后,再将复核后的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终裁决。
这个审刑院,是个什么机构?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个锦衣卫;信不过锦衣卫了,搞了一个东厂。宋朝皇帝呢?赵家官人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个审刑院,又称“宫中审刑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审刑院是谁设立的了。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大理寺所断案件,因为皇帝要看着大理寺,担心被大理寺的人给忽悠了。
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长出什么庄稼。明朝的专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务机构。大宋的法制土壤,却能孕育出法制机构。审刑院的设置初衷是加强皇权,实际运作却成了司法监督的一个环节。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设立的机构却不给皇帝办事,那还有啥意义?
从这一套复杂手续或程序中,我们就能发现: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准备跟人讲理的,这绝对是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
04.大宋官家很生气:法外施法也要让人讲理大宋御史台把案件审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录问了,苏轼倒也干脆,从不从宽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别无翻异”。
但是,苏轼之所以“别无翻异”,是因为新党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给查了,苏轼想翻供都没得翻。
新党这帮家伙不止要干苏轼,还要干司马光和整个旧党集团。所以,乌台诗案一定要办成铁案。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苏轼。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确实没有管住嘴,确实要做时代的匕首和投枪了。
大理寺根据苏轼的供状,总结出了三条罪名:
一是苏轼收了驸马王诜的钱,而且这个钱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所以苏轼“别无翻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诋毁新法、诽谤朝廷,这一条是新党的主要关切,但要的不是诽谤朝廷而是诽谤皇帝。
所以说,新党把持了御史台,却肯定没能把持大理寺。
针对这三条罪状,大理寺给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会怎么数罪并罚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简单说就是数罪从重,一个罪杖八十、另一个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会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钱抵罪,当时主要是向朝廷交铜,铜是当时的主要硬通货,是可以拿来铸钱的。
第三,如果是官员,犯罪的官员还可以拿自己的官职来抵罪,即官当制度。
这套量刑算法,可以说充分确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来,苏轼要承担的罪责,只是徒二年。《资治通鉴续长编》给出的记载,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如果是新党看到这份判决,想也不想,他们肯定认为大理寺收了苏轼的钱。因为这是在过分偏袒苏轼。
甚至都可以说,大理寺这帮家伙连一天牢饭都不想让苏轼吃。因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大宋一定会大赦天下。
苏轼是在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处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这中间差了两个多月,大理寺给了一个“会赦当原”的判词,到底想说啥?
所以,新党肯定不能干。
这帮家伙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百多天,然后却是这么个结果,谁也不能忍。于是,御史台上书反驳,认为大理寺定罪不当,苏轼必须按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大不敬(恭)”来定罪。
“注云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注云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苏轼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这个大不敬。
御史台瞎咋呼,却没用。因为定罪量刑,不归它管。这时候,审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到了这一步,就要区分一下谁跟谁是一伙儿了。
御史台肯定被新党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没被新党控制。那审刑院呢?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儿。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见?诋毁新法就相当于诋毁皇帝,必须要严办。但是,审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刚正不阿了,站队大理寺了。
乌台诗案持续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势力该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这期间,当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旧党翘楚,纷纷上书营救苏轼。同时,新党内部也分裂了。罢相在家的新党大佬王安石,也上书了,认为“圣朝不宜诛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临死之前劝谏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苏轼、苏辙兄弟当成宰相来培养的。但是,你这个皇帝却要杀了苏轼,你对得起你老爹吗?
于是,乌台诗案,死活也没法按照新党设计的脚本来编排了。
新党的脚本是什么?针对苏轼发动一场文字狱,然后借机把旧党一网打尽。但是,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狱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将来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狱,文字狱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个结果,任谁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风一定败坏。
那么,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气。王安石虽然罢相、王安石主义可以不讲,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必须坚持。这不是王安石的主张,而是朕的主张、朕的旨意、朕的路线。你苏轼诋毁新法,就是在诋毁朕这个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却要让苏轼讲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让苏轼讲理。但是,皇帝肯定气不过,于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过分。最后的结果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这是大理寺的意见,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责”,即法外施法,因为朕很生气、朕要任性,于是苏轼“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检校”是临时委派的意思,随时都能给你免掉,即便是副处长,但也是个临时的。
“水部员外郎”是官,在官职差遣的设计中,这相当于待遇级别,用现代表述就是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黄州团练副使”,这是差遣,是实职,相当于黄州地方武装部副部长,却是散官、没实权,一般用来安置贬官。
关键是这个“本州安置”,相当于发配。你苏轼就在黄州那个鬼地方呆着,我这个皇帝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黄州地方官也要把苏轼这个家伙看好了,该敲打就得敲打。
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责”。
如果是朱元璋这种皇帝,苏轼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个眼色,苏轼别说可能在发配黄州的路上被干掉,甚至连牢门都出不来。
最后总结乌台诗案是新党对旧党发动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满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
而旧党的”交际名媛“苏轼,恰是新党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如果乌台诗案能够按照新党的设计脚本来推演,那么此案就是一个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大宋司法机构的复杂运作,堪称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复杂的程序甚至已经超过了现代国家。
苏轼,生在了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执政的新党肯定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讲;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满意,他也要讲他这个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个让你讲理的时代。
可能这个“你”,仅是官员士大夫。但是,起码能够让朝堂权力无法肆意任性、让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为。
正是因为让苏轼讲理,所以苏轼才能逃过乌台诗案这个劫难。而旧党一众翘楚们,也才免于被权力清洗。
旧党顽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线,就不能高效率推进。旧党难道不是历史的阻碍吗?
程序正义或许比正义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义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风才不会急转直下,大宋官场才不会演变为李林甫之后的大唐官场。
历史上的发展,有两种:
一种是高效率的急速推进,开了挂、踩了油门,这是一种政治能动,比如王安石变法。
一种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档、踩了刹车,这是一种政治谦抑,比如司马光的旧党意见。
到底哪一种更好?因时而异。
初出茅庐,往往是政治能动的,自命大才而要经天纬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谦抑的,懂得了才华智慧的局限和真实世界的复杂。
也许这样的态度是可取的:有一个方向,即便方向对了,也要慢一点儿、稳一点儿,反正时间有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也就给调整留出了时间和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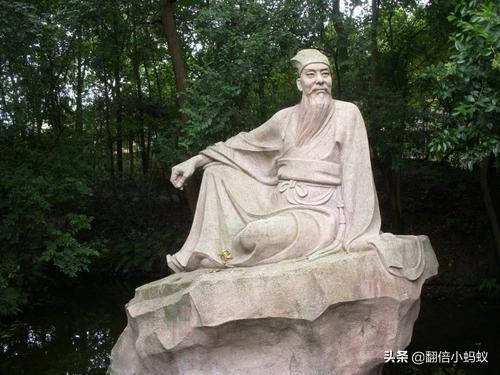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苏东坡是个有理想的好官,但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客。因此在这场新旧党派的斗争漩涡中,苏东坡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当初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十分欣赏苏东坡的才华,打算拉他入伙。结果这位老兄和他那个二愣子弟弟苏辙,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当然了,只是反对其中的一部分观点而已。
王安石很气愤,就把他们俩打发到地方上做官了。相对来说王安石对苏东坡,算是仁至义尽了,并没有加害他。
可是多年以后王安石下台了,苏东坡可就麻烦了。宋神宗变法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他把所有气都撒在了旧党文人身上,苏东坡自然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这下完犊子了,宋神宗要收拾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所以说要查你根本不需要理由,宋神宗只需要一个眼神,底下的御史们就知道该咋整了!
一、乌台诗案,本身就是新党对旧党的打击。当时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惯例,这个时候地方官都要写一份谢表给自己的大领导宋神宗。于是苏轼就写了一份《湖州谢上表》,本来也没啥,就是一份普通的例行公事的谢表而已,可御史们却从里面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文中有这么一段: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说,宋真宗您是真厉害啊,知道我跟不上变法的形势,只能在外地做做地方官,不能到朝中担当大任。
有了这么一段话,那苏轼的罪名可算是坐实了!这种与变法决裂的态度,几乎是公之于众了!宋神宗是越想越气啊,二话不说就让人把苏轼给抓回来了!
此后御史们又把苏轼家的诗文全都搜罗了一遍,从中强行找出了一些有可能影射朝廷的诗文,这下完犊子了,苏轼彻底坐实了藐视宋神宗,藐视新法的罪名。
犯下如此罪过,基本就是杀头才能解决问题了。那么真的是苏轼的诗文有什么问题吗?其实不然,从乌台诗案所牵连的人来看,这就是一场新党对旧党的打压。
司马光、驸马王诜等39名与苏轼互赠诗词的人,都受到了乌台诗案的牵连。很显然,这帮人大多是旧党成员,即使不是,也是保守派。
二、苏轼是如何躲过一劫的呢?按照当时宋神宗的想法,苏轼这回是铁定完犊子了。因为查出了大量诗文是直接抨击新法的,这是击中了宋神宗的要害。
当时御史李定曾经上报宋神宗,表示苏轼名气太大,不敢动用刑具。气得宋神宗破口大骂,狠狠收拾了苏轼一个月时间,居然连退休的王安石,都跟苏轼有过书信来往。
这下子宋神宗稍微有点清醒了,这哪里是在收拾苏轼啊,这是在砸自己的招牌有没有?宋朝善待文人,那是出了名的,现在这帮御史已经到了穷凶恶极的地步了。如果连王安石都牵扯进来,这事儿可就不好收场了。
于是宋神宗开始冷静分析这件事,御史们再次找到某些诗词中有哪些隐喻的时候,宋神宗也出现了不以为然的想法。可是就这么饶了苏轼,未免太丢面子了吧?必须要有一个导火索才行。
这个时候,体现苏轼人脉关系的时刻到来了!当时新党成员们,非要怂恿宋神宗弄死苏轼,可苏轼的朋友们却开始提出反对意见。
比如说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就曾经上书给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曾经上书给宋神宗:愿意削职为民,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
还有一堆文人分封上书劝说宋神宗,这下子宋神宗终于找到台阶下了,于是就搬出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言,饶了苏轼一条小命。
可以说,苏轼这个人虽然做政客,没什么水平。但是在交朋友这方面,一点儿毛病都没有,绝对是典范。
三、宋神宗变法不顺,本打算拿苏轼作为突破口。王安石在任的时候,变法进展迅速,虽然阻力很大,可王安石的气场更大,因此挡住了若干压力。可是宋神宗却挡不住内外的压力。
当时若干因为变法而伤害到自身利益的王孙贵胄们,找到了宋神宗诉苦,纷纷指责王安石不是人!此外太皇太后和太后,都纷纷跑到宋神宗这儿哭诉王安石变法的祸害。
这下完蛋了,因为王安石顶得住,可宋神宗却顶不住了!于是宋神宗出卖了王安石,罢免了他的宰相之位。这件事对变法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啥?因为实行变法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老大都被搞得下岗了,那这事儿还能办得下去吗?所以说此后宋神宗再想变法,已经变得千难万难了。
王安石下岗以后,宋神宗那叫一个后悔啊,索性自己担任了变法的领头人。结果遭遇了各种挫折,再加上此前朝令夕改的问题,变法急需一个催化剂才能继续前进。而乌台诗案就是最好的催化剂。
当时底下的人都不敢随便实行新法,担心第二天就换了个说法。因此大家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宋神宗把那帮反对变法的旧党揍一顿,岂不就是给摇摆不定者敲响了警钟?政客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那啥服务的!
总结:经此一役,苏轼性情大变。过去的苏轼,那就是一个愤青,有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看不顺眼就用笔写下来,骂两句。这种性格实在是太可爱,但是也太容易得罪人了。
乌台诗案过后,苏轼立刻老实太多了,轻易不下笔,下笔也不敢轻易去谈论国事了。他可不想再经历一遍牢狱之灾,想起当日的情况,苏轼依旧瑟瑟发抖。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
宋神宗派来的人,抓苏轼这个太守,就跟抓一只小鸡仔一样,实在是狼狈得很。或许这就叫,经历使人成长吧。
参考资料:《宋史》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很多人只知道,被贬黄州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却不知道比被贬黄州更可怕的是,他曾经面临死亡的威胁。
相对于被处死,所谓的“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 乌台诗案
个人觉得,“乌台诗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狱了。
这个乌台,就是御史台。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御史台是古代的监察部门,对官员进行弹劾,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吧。
其实,“乌台诗案”的直接起因不是苏东坡写的诗,而是他到任湖州知府后给皇帝写的谢恩奏章。本来,这种谢恩奏章只是例行公事,就说自己过往业绩一般,但是皇恩浩荡,感谢组织信任,又给小臣换了这么好的职位,将来自己一定要鞠躬尽瘁,永远忠于皇帝等等。
只是,苏东坡不是写这类文章的人,即使文中有部分内容是这样,他的文章总要说些真正的事情的,
“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其中,“新进”就先让人皱眉头。这里面的新进,不同于现在的意思,当时北宋为王安石变法新政引起的党争里,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所以有固定的代表含义。
我们一般人以为,苏东坡给皇帝写的奏章,骂了一些人就骂了,怎么样?皇帝还能看那么仔细,给挑出来?这皇帝也是小肚鸡肠,闲得慌。
是的,我记得我们之前上课,老师讲到“乌台诗案”,苏东坡因为写的奏章开始吃亏,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们想错了。苏东坡写的奏章,实际上是要上报纸的。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报纸了。苏东坡的文章,谁不抢着看?这次的谢恩表,就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的笑柄。
苏东坡过往的生活态度,一直都是嫉恶如仇,碰到不好的人与事,“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之前九十九次一直没事,这次吐到一百次的时候,就被那些小人抓住了。
杀与不杀,是个难题。但是,抓起来,关进御史台监狱,是最起码的待遇!
2.死亡威胁
古代全能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这家伙还是苏东坡的旧友,他说:苏轼许多诗词都是泄愤之作,意在讥讽朝政。
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当时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两人在杭州畅叙旧情,沈括顺带搞了苏东坡近期的很多新作,带回开封。回京后,沈括认真研读苏东坡的作品,并用附笺把自己认为的有诽谤朝廷嫌疑的诗句做了详细的注解。
《湖州谢上表》爆料后,沈括赶紧地,把这些做过注解的诗词送给监察御史舒亶。
舒亶则是个坚定的倒苏派,他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最终筛选出诽谤朝廷嫌疑最大的几首,公之于众。
比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明显是在讽刺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在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公开和朝廷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最有分量的是“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苏东坡,你是有多恨当今圣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真龙,当今圣上可没死呢!在古代,诅咒皇帝,这是要掉脑袋的吧。
古代,说到御史,是不是眼前浮现出一批耿直的人,向皇帝直言进谏,比如魏征、包青天、海瑞、左光斗等等。
可是,北宋那时的御史台,有自己的特殊性,已经因为之前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清洗过,换上了李定、舒亶等小人。
那些当政的小人把苏东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除了而后快,更要借这个机会把反对派一网打尽的。舒亶奏请连同司马光、范镇、张方平和苏东坡另外5个朋友,一律处死。甚至副相王珪在御史的逼促下,还想着在皇帝面前给苏东坡加上谋反之罪。要知道在古代,这样的罪名,一给定上,只有死路一条,只是理由太过于牵强,竟然说苏东坡在一首关于柏树的诗里说龙在九泉,好在皇帝不信他这么牵强附会的控告。
3.逃过一劫
乌台诗案的最终处罚,苏东坡被贬黄州,降职,充当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无权签署公文。
这个相对于御史台要求的处死、流放等,简直不是事。
“乌台诗案”由于案情重大,最终判决是皇帝亲自决定的。当时的宋神宗,在御史台的强大压力下,也还是轻判了苏东坡,原因有几个,说来让大家判断判断。
第一个说法是宋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
这时候身染重病,她对当时的神宗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位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在受审,其实都是小人针对他。小人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就想由几句诗入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又说大赦天下为她祈福的话,不用赦免那些凶恶之徒,把苏东坡赦免就行了。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第二个说法是,定罪时候,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王安石的上书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个说法,审问完毕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话不说,有人走进苏东坡的监室,往地上丢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苏东坡以为他是个囚徒,不管他,自己也躺下睡了。四更时分,苏东坡觉得有人推他的头。那个人向他说:“恭喜!恭喜!”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皇帝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去观察苏东坡。那个人到了苏东坡的屋子之后,苏东坡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 回去报给皇帝说苏东坡睡得很沉,很安静。这样,皇帝就判定苏东坡是问心无愧的。
还有,苏东坡在狱中以为自己要被处死,给弟弟子由写了两首诀别诗,其中一首,《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如果解析这首诗的话,措辞方面极为悲惨,手足之情愿世世为手足。也足够呈于御前,因为诗中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自己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这次的事情别无他怨,都是自己的过错。
而这首给子由的诀别诗,最终传到皇帝手中,神宗皇帝看了后十分感动。苏东坡也坚信自己写的这首诗会传到宋神宗手中!
这也是虽然御史施予强大压力,苏东坡却最终判得很轻的缘故。
4,乌台诗案,里面都是哪些诗?
很多人都会好奇,“乌台诗案”,里面都是苏东坡的哪些诗文惹了事情?
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中说:“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既然林语堂先生写的时候提及这本书,按道理是还有存于世的,只是,我在某当,以及广州图书馆搜索此书,都没有找到,在深圳图书馆搜索,感觉有,叫做《乌台诗案研究》,但只限馆内阅读,应该是非常稀缺的。
《乌台诗案》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北宋在苏东坡逝世25年后,于靖康元年(1126)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金人攻入北宋京城后,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作品、书画。因为苏东坡活着的时候,他的诗文其实也已经驰名域外了。反正,这批资料是逃过金人的魔爪,到了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的日记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看过《乌台诗案》的话,就可以全部找到当时的肇事诗文吧,重点是还有苏东坡对自己诗句的解释。
毕竟,苏东坡从湖州任上被押送到京城,他的家人惊慌中,认为都是他写诗惹的祸,焚烧他的手稿,烧了三分之二,这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大的遗憾了。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苏轼是文人,如果杀苏轼就动了当年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这是所有文官集团所不能容忍的;
公元1068年,宋神宗登基,宋神宗为了实现汉唐荣光,立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要富国强兵。但是王安石本人过于拗执,措施非常激进,引起朝野议论纷纷。此时苏轼上疏批评王安石有些策略中过于激进的方式,于是给一些新党人员记恨,开始罗织罪名给苏轼好看。
苏轼也看到了自己在朝中没有立足之地,开始上疏请求外放,并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后来苏轼又去了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见到了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端,开始上疏。在湖州的时候,苏轼在《湖州谢表》中写道了“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里面就说了苏轼要与新党对着干了。本来新党就看他不爽了,他外放了也是眼不见为净,现在好了又来惹事,好就专门来搞你。
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苏轼的好友沈括在下面视察新法的时候发现了苏轼的诗稿,首先呈现给宋神宗,宋神宗没有重视。不久,苏轼的《湖州谢表》上疏之后,百官开始弹劾苏轼,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其“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就是说苏轼妄议朝廷,两面人之流。
于是朝廷御史台(旧称乌台)就开始派人去缉拿苏轼。苏轼被押到东京汴梁,关进大狱,审讯随即进行。文人相轻,进而相轮相害,从来都是毫不手软的。当然,苏轼也不是没有把柄可抓。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传诵一时,影响不小。
主审官本身就对苏轼有意见, 此时苏轼又撞到枪口上,就打算杀一儆百,名为弄苏轼,实际上是弄整个旧党。于是他们就开始捕风捉影,将苏轼诗句中的一些话语开始上纲上线,说他们是为了反对变法, 同时是诽谤圣上的。例如苏轼的《咏桧》有一句这么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们就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蛰龙,不是想造反吗?”不过宋真宗不傻,他看了苏轼整首诗回答道:“怎么能胡乱解释,他是歌颂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
前途险恶,生死未卜,苏轼思想相当悲观。在去东京汴梁的途中,苏轼曾经想要跳江自尽,最后没跳。入狱之后,他将许多毒药狱中,准备一旦得知自己将被处死,就先行自杀,免得在菜市场上丢人现眼。苏轼与儿子约好,每天往狱中送饭﹐都要有菜和肉,如果听到自己将被判死刑,就撤掉菜和肉,改送鱼。他儿子每日给他送去肉菜。
有一天家里粮食不多了,他儿子去郊外买粮,托亲戚代为送饭菜,但忘了关照不要送鱼。亲戚正巧送了鱼。苏轼看到鱼,心想这回完了。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嘱咐狱吏转送其弟苏辙。他知道狱吏不敢擅自为犯人送信,必然会将此事上报。果然,宋神宗读到此诗,心中不免有所感动。
因为苏轼的文学一直不错,名满天下,使得很多人开始去营救苏轼。新党如果流放苏轼还能说得过去,如果真的要杀苏轼的话恐怕就会得罪天下人了。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鉴于五代时期武人多次篡位,立下了一个誓言,就是“不杀士大夫”,给士大夫权力来遏制武人,这样就会使得文人充斥朝廷,武人就无法干政了。
同样宋神宗时期,因为对西夏用兵失利,宋神宗想要将一个管理后勤的官吏杀害,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宋神宗说能否琼面发配,章惇此时说道士可杀不可辱,还不如杀了呢,左右临之际宋神宗只好放了这人。可以说不杀大臣是一种政治原则,蔡确说这是祖宗以来,而章惇直接讽刺,虽然章惇蔡确对于这事情有分歧,但是“祖宗家法”是俩人共同需要维护的,也是那种看破不说破的潜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不杀士大夫”只是一种政治原则或传统,而不是“一律不杀”。而且,这种“不杀”更多的是表现为“政治”方面、“言论”方面,至于贪赃、枉法、投敌、造反等,就不全在“不杀”之列。例如宋太祖时期对于刑事犯罪,尤其是贪赃罪处置得相对严厉。尽管如此,“不杀士大夫”的政治原则也还是有所体现的,一般说来,中下层的官吏,基本都被处以死刑,而高级官吏,即可以入“大臣”行列的则往往是罢官或流放,几乎没有判处死刑的。谁要是破坏这个政治规则,谁就会遭到整个文人士大夫阶级的排斥。
果真苏轼出事之后,很多人开始出来为他说情了。吴充就上疏宋神宗说曹操的品行如何,宋神宗说曹操乃奸佞之徒,吴充说奸佞狡诈的曹操都能容忍祢衡的狂妄发癫,陛下是圣天子,自比尧舜,难道还不能容忍苏轼的几句牢骚话吗?一听此言,宋神宗只好打马虎眼回答道:“我正打算放了他呢。”
此时宋仁宗的皇后曹氏也出面说情了,对于曹氏宋神宗一直很尊敬,不敢违背。此时王安石也说,既然是太平盛世,为何杀这么一个有才能的人呢?这么一来二去,宋神宗的耳根子就软了,而苏轼的事情调查来调查去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好调查的。最后匆匆定了一个妄议朝廷的罪名将其流放黄州,此时苏轼终于幸免于难。但是与苏轼平时有往来的人,包括曾巩、司马光、李清臣(李清照他爹)、黄庭坚等人都或多或少被处罚了。可以说这其实也是新党以苏轼为引子来给旧党的一次下马威。
苏轼出狱那天,狱卒将其那两首绝命诗还给他。看着这两首绝命诗,苏轼感慨万千。可是日子一长,苏轼又开始得意起来认为自己在狱中的那两首诗赞扬了……。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苏东坡在仕途上一直郁郁不得志以至于一贬再贬,大概就是因为他这样恣意耿直又单纯的性格。
他生于北宋年间,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 、苏仙 、坡仙等 。一生豪迈放达,为人率真,道家风范十足。好朋友, 好美食, 好品茗, 亦雅好游山林。他除了是我们熟知的是文学家书法家,他还是个画家,墨竹,枯木,怪石都擅长;他不仅是个画家,他还是个美食家,有名的“东坡肉”就是他被贬期间在黄州、杭州等地自烹调制,把当时大家都不要的低价猪肉买回切块红烧分给大家,后来大家吃后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取名“回赠肉”也叫“东坡肉”。还有“东坡凉粉”,是他于凤翔东湖避暑时,炎炎夏日下特命人取滨豆(也称作小扁豆)研磨成粉,熬制成糊状,盛入石头器皿中待其冷却后,切成条状,配以盐醋等佐料凉拌。入口爽、滑、并有清凉解暑之功效,之后流传于凤翔民间。后人为纪念他称其为“东坡凉粉”并流传至今。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实行“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变法期间王安石确实雷厉风行,也因为确保变法进行打压排挤过不少反对派官员。苏轼上书批评王安石在一些策略中过于激进,讽刺新法。这就给一些新党人员抓到了把柄,到处罗织罪名给苏轼。随着神宗将王安石罢免,变法主持者已经变为神宗本人,只是,单纯的苏轼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后来外放杭州多年的苏轼被调任到湖州担任知州。他上任以后,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来是当时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新官上任都是要写这么一篇文章的。但我们这个可爱的老头儿是很有个性的,所以在这个文章中流露出很多自己的情绪。他在文中写道:“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等,这意思就说苏轼是不同意新党那些做法。本来新党们和他就不合适,加上宋神宗当时也是想推进新法。他现在又来说这些,那百官就开始弹劾苏轼,还从他以往的诗作中摘录了大量的句子,说这些都是他发泄不满的证据。一时之间,兴起了一阵倒苏之风。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宋神宗下令御史台抓捕苏轼,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乌台诗案”事发当时,大家很担心苏东坡,觉得他可能会被处死。那时候苏轼已经名满天下了。很多人都尝试去营救苏轼,开始出来为他说情。吴充就上书宋神宗说:“奸佞狡诈的曹操都能容忍祢衡的狂妄发癫。陛下是圣天子自比尧舜,难道容不得苏轼几句牢骚话。”一听此言,宋神宗只好打马虎也回到说:“我正打算放了他。新党如果流放苏轼能说得过去。可如果真的要杀苏轼,那就会得罪天下人了”。
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立下过一个誓言,就是不杀士大夫,给士大夫权力遏制武人,这样会使文人充斥朝廷,武人就无法干政。苏轼一介文人,如果把他杀了,那是动了宋太祖当年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这是所有文官集团不能容忍的。
后来苏轼被关到监狱中,他的儿子每天都去监狱探望送饭。于是他和儿子约定,平时只许送蔬菜和肉,如果有坏消息,才能送鱼。不巧的是有一天他儿子有事,就让他朋友去送饭,但是忘了告诉他朋友不能送鱼这个约定。然后他的朋友送的恰恰是熏鱼。苏轼看后大惊,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便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诀别诗写得极为悲惨,但又不忘感谢皇恩浩荡。
这首诗后来被狱卒收走,交给监狱最高层查阅。然后就传到了皇帝手里。皇帝看到了这首诗后有所缓和。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说情,因为曹氏一向支持苏轼。宋神宗一直很尊敬曹氏,不敢违背。此时王安石也说,即使太平盛世,为何杀一个这么有才能的人?并且苏轼的事情调查来调查去,说实在的没什么好查的。恰在这时,天皇太后染病而死。她在死前还对皇帝说:“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而不抓了起来。这都是一些小人和他作对。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曹氏去世,国家要大赦,按照惯例,苏轼也应当被赦免。皇帝已经无意杀害苏轼了,加上这么多人为苏轼说情,所以最后匆匆定了一个妄议朝廷的罪名,由他亲自裁定,将其流放黄州。苏轼也是终于幸免于难。但是和苏轼平时有来往的人包括曾巩、司马光、李清臣,还有黄庭坚等人,都或多或少被处罚了。可以说这实际上是新党用苏轼作为引子要给旧党来一次下马威。
“乌台诗案”至此落下帷幕。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怎样逃过一劫的?
“乌台诗案”缘由
“乌台诗案”的出现其实和苏轼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苏轼一向嫉恶如仇,遇到不平时的事,他总是不吐不快。
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任湖州。按照惯例,到任后,要写谢恩奏章。
问题就出在了这份奏章上,他写了这样的几句话:
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赔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出现了“新进”这个词,这个词在当时指的是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这样就得罪了那些“新进”。
这一年的六月,“新进”的报复就来了。
一个御史把这份奏章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从而开始弹劾他。
几天之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
在得到神宗的批示后,他们派遣官吏到湖州,先免去了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
最终,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监狱被称为“乌台”,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作“乌台诗案”。
苏轼如何“化险为夷”苏轼在7月28日被捕,8月18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而审问期又比较长,前后40几天。
他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1.一个故事
苏轼被关到监狱中后,他的儿子每天都去监狱探望,并为其送饭。
苏轼和其子约定,平时只许宋蔬菜和肉,如果有坏消息,才能送鱼。
有一次,其子有事,便将送饭的任务交给了朋友,但忘记告诉朋友他和父亲的约定。
而那一次,他的朋友送的恰恰是熏鱼。
苏轼看后大惊,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便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诀别诗写的极为悲惨,但又不忘感谢皇恩浩荡。
这首诗后被狱卒收走。
这就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按规定犯人写的任何东西,狱卒都要交个监狱最高层查阅。
而苏轼和其家人也认为这首诗会传到皇帝手里。
果不其然,皇帝看到了这首诗,并大受感动。这也是他能“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
2.仁宗皇后
皇后一向支持苏轼。恰在这时,染病而死。她在死前曾对皇帝说:“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而不抓了起来。这都是一些小人和他作对。你可别冤枉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
皇后去世,国家要大赦,按照惯例,苏轼应当被赦免。
但是,御史们想置苏轼于死地,不停的向皇帝进言。但也没有得逞。
3.最终
皇帝无意杀害苏轼,他亲自裁定,把苏轼贬往黄州,充当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也无权签署公文。
“乌台诗案”落下帷幕。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