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关于打油诗和诗的界限
诗词创作,必须遵循严格的写作规则,有固定的格式、韵律,遣词用字讲求平仄对仗,词还有固定词牌和字数的限制。
人们常把一些以俚语俗话、甚至方言土语入诗,根本不讲究诗词的创作要素的格律严整、平仄对仗,多含相声艺术中的“包袱”似的诙谐幽默词句,类似“顺口溜”的诗作,称为“打油诗,这些都是打油诗和诗的区别所在。
打油诗,不似“阳春白雪”雅诗,也难得文人雅士的欣赏,登不上文学“大雅之堂”;但是,打油诗深得泥巴腿子的大众喜爱,可以说是“下里巴人”文化范畴;也有文豪创作打油诗的,如文学大师鲁迅,下面将述及。
打油诗,因为唐代名为张打油之人所创,以至这类诗竟冠以他的名字称之为打油诗,张打油也因而成为历史名人,彪炳青史!
说起打油诗,还有一段轶事;是年冬天,一位当朝官员去祭奠宗祠,刚进庄严肃穆的祠堂大殿,便看见粉刷雪白的照壁上,竟然被人“涂鸦”,仔细一看,上面写了一首诗:
“六出纷纷降九霄,
街前街后尽琼瑶,
有朝一日天晴了,
使扫帚的使扫帚,
使锹的使锹。”
胆大包天!
竟敢在朝廷命官大人,供奉祖宗的神密庄严的圣地,随意“涂鸦”乱写画,大不敬!!
何人?
官员大怒,立即命令左右随从卫士,查清作诗“涂鸦”之人,重重治罪。
官员随行人员中,有位师爷上前禀道:“大人,不用查了,作这类诗的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张打油。”
官员闻听,立即命卫士把张打油抓来了。
张打油听了这位官员的严历呵斥,上前深深一揖,不紧不慢地回复:“大人,我张打油确爱诌几句诗,但本事再不济,也不会写出这类诗来嘛。不信,小的情愿面试。”
官员一听,口气不小啊,决定亲自出题面试张打油,以辩其言真假。
正好时值“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军围困南阳郡,于是便以此为题,要张打油作诗。张打油也不谦让,脱口吟道:
“百万贼兵困南阳,”
那位官员一听,说道:“好气魄,起句便不平常!”
张打油微微一笑,再吟:
“也无援救也无粮,”
官员则又说:“差强人意也,继续。”
张打油马上一气呵成了后三句:
“有朝一日城破了,
哭爹的哭爹,
哭娘的哭娘!”
后二句,与墙上“涂鸦”之句:
“使扫帚的使扫帚,
使锹的使锹,”
分明如出一辙。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就连这位官员也被惹笑了,于是大开网面,饶恕了张打油。
张打油从此远近扬名,“打油诗”的称谓也就不胫而走了。
张打油,不过是一般的读书人,中国古代历史的盛唐社会,产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唐诗”的文化氛围下,是个无名小卒。
但他的这首《咏雪》:
“江上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此诗描写雪景,由全貌而及特写,由颜色而及神态。虽然通篇写雪,却是不着一个“雪”字,而雪的形神跃然。遣词用字,十分贴切、生动、传神。用语俚俗,本色拙朴,风致别然。格调诙谐幽默,轻松悦人,广为传播,无不叫绝。
张打油,可以算得上一鸣惊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体“打油诗”,名垂千古,成为历史文化名人。
打油诗,起源于唐代民间,以后瓜瓞绵绵,不断发展,表现出活跃的生命力,而延续至今,仍有广阔的生存市场,旺盛的生命力。
打油诗,这类诗一般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有时暗含讥讽,风趣逗人,深得“下里巴人”大众的喜爱,也时有文学大家作品问世,如鲁迅先生的《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免责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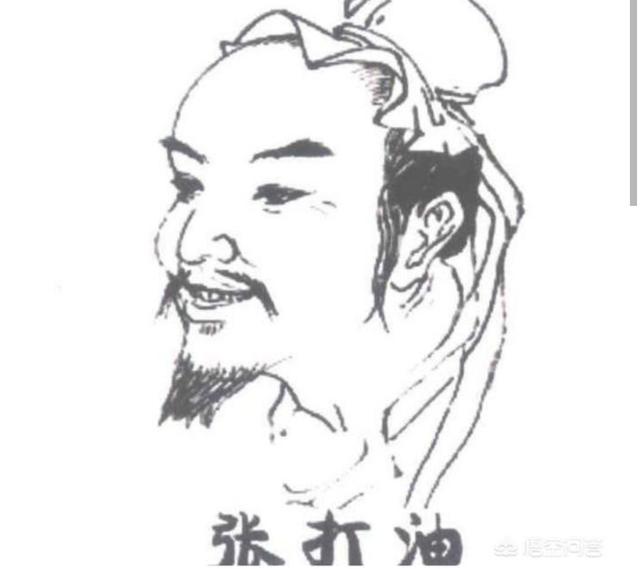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谢邀。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比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就是诗, 可是你如果改成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婆娘。它就成了打油诗。 那么诗和打油诗的界限在哪里?
首先我们确定一点,打油诗也是诗。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别打油诗呢?这也就是题主的问题,区别诗和打油诗的界限在哪?
是有界限的,但是这个界限相当的模糊。诗的特征我们就不说了,即可高雅大情怀,又可悲伤小情调,好像并没有什么不适诗歌不适合表达的,为何又多出一个“打油诗”的类别呢?
打油诗有哪些特征,我们罗列几首出来和一般诗歌进行对比,看能否找出不同。
首先看打油诗宗师张打油的开山之作:
咏雪
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还有诗僧王梵志的关于“土馒头”的诗:
王梵志:馒头诗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近代打油诗之王张宗昌司令的一些打油诗:
咏雪
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灰呀筛石灰。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打油诗的特点无非是:通俗,诙谐,机心。
其实我们从写法结构上是无法区分打油诗的,我们只能从语言的浅白上来做出判断,但是打油诗虽然不避俚俗粗陋,却有一种流于表面的幽默,甚至还有机巧的灵思。
而幽默诙谐和机心其实和绝句律诗并没有什么差别(写苦情的除外),那么就只有从通俗上来辨别了。说简单些:一字改半天,捻断数根须的就不算;俚语俗腔开口即来,人人一听就懂,并且会心一笑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了。
打油诗也不简单,要有灵机一动,要有幽默诙谐,才能是众口相传。而流俗正是打油诗和诗的最大区别,但是这个区别的界限是模糊的,随着社会变化的,雅俗也是在不断转换变化的,这种东西没有一个成文的标杆理出来,全靠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
无非就是意境与文笔。其实这也就是写诗最基本的东西,还是那句话,打油诗和好诗没有诗体之分,只有雅正和流俗的区别。
有很多东西,一旦真正高雅起来,就没有了。像二人转一样,上了大雅之堂,就没人看了。
打油诗也差不多,你要真把他整精致、高端了,他就不是打油诗了。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评论。
喜欢请点赞并关注,谢谢。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笔者作为编辑,经常收到许多诗歌爱好者写的诗,这其中就有些诗是打油诗。
打油诗确实曾被定义为旧体诗的一种。但是,随着诗歌的发展,打油诗的核心特征也会大量在现代诗歌中出现,人们的认识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时再把打油诗的概念限定在旧体诗中就妥了。今天,若从更全面的角度看,打油诗也可以是现代诗歌,不仅是旧体诗。
至于打油诗和非打油诗间,则感觉过度通俗特别是俚俗的就是打油诗,感觉不过度通俗尤其高雅的就不是打油诗。两者之间同样也存在模糊地带。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谢邀!我觉得打油诗和诗之间就像是糖和糖水一样,界限模糊不清。前者直白顺口 简约随意。诗是甚么大家都晓得,必须要讲平仄韵律,一字千金,情景交融,赏心悦目。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打油诗是∵唐朝诗人張打油在赏雪景时,即兴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咏雪很快被传送,不管是谁都可伩口拈来,有的人仿照此种格式创诗,慢慢形成了一种诗体,.由于原创是张打油,所以命名为打油诗。从上述可见,打油诗是一种结构简单,用词朴素,形意传神的诗体。而诗是移情入景,万物有灵,意境高远,言犹不尽,在有限的篇幅中蕴藉无限的内容,常常引人遐想余味不散。如风吹荷叶中诗人笔下是感性的[风吻荷香]。再如佳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等。由此可见,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就在于;打油诗简单直朴,自由,大众化。而诗夸張,联想,真实又梦胧,欲露又掩,十分令人陶醉!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
题主您好。个人觉得打油诗和诗的界限主要在于:平仄、押韵、遣词造句、意境的模糊性等四个方面。我们常见的打油诗有古体诗体裁的、有近体诗体裁的,还有自由诗体裁的。现以近体诗中的绝句和绝句体裁的打油诗作比较,以点带面来分析打油诗和诗的界限。
一、诗(古体诗和自由诗除外)在平仄上要求严格,但打油诗不太注意。1、以五言绝句为例,诗(古体诗和自由诗除外)的平仄必须按标准句式来写,任何的近体诗都是这四种标准句式的排列组合。这四种基本句式即: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七言在五言前加两个相同的相反平仄)
古人使用这四种基本句式来写绝句时,虽然也可以有变动,但基本秉承一三不论,二四五分明的原则。意即写绝句时,一句诗里面,除了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可以不论平仄以外,其他的都要严格按照平仄的规定来写。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例: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诗的平仄为: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白”为古入声字)
仄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一”为古入声字)
这首诗除了第三句的第一个字,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字与字平仄相间,句与句平仄相对的原则来写的。
2、以五言打油诗为例,打油诗平仄自由。以张打油的《咏雪》为例:
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这首诗的平仄为:
平仄仄仄仄 仄仄仄平平 (“黑”为古入声字)
仄仄平仄仄,仄仄平仄仄 (“白”为古入声字)
从这首打油诗可以看出,这首诗是字与字之间不讲平仄相间,句与句之间不讲平仄相对。
二、诗在押韵上要求严格(自由诗相对宽松一点),但打油诗不太注意押韵。仍然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和张打油的《咏雪》为例,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第二句、第四句入韵,“流”、“楼”押韵,都是平声韵(绝句只能押平声韵)。
张打油的《咏雪》的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入韵,“统”、“窿”、“肿”押韵,其中“统”、“肿”是仄声韵,在绝句中属于押韵大忌,不仅如此,“窿”还是一个平声。所以,《咏雪》这首打油诗在押韵上只讲韵同,但在平仄上完全不讲究。
再以王梵志的打油诗《馒头诗》为例: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从这首诗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看来,“头”、“里”、“个”、“味”四个字之间是不押韵的。这就更说明打油诗不太讲究押韵。
三、诗在遣词造句上多要求用词典雅脱俗,但打油诗不太注意,用词多平白俗俚。1、人们写诗时,用词多典雅秀奇、清新脱俗。比如,写诗时称兄弟不叫“兄弟”,而叫“棠棣”,称荷花不叫“荷花”而叫“菡萏”,多喜欢用代称等修辞手法。如古代咏菊,一般诗中很少直接出现“菊花”这个称谓,如宋代范成大的《重阳后菊花》:
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屋照泥沙。
世情几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
宋代陆游的《九月十二日折菊》:
黄花芬芬绝世奇,重阳错把配萸技。
开迟愈见凌霜操,堪笑儿童道过时。
这两首诗都是在咏菊花,但是一个以“东篱’代称菊花,一个以”黄花“代称菊花。
2、人们写打油诗时则刚刚相反,句意一般追求平白,用词多俗言俚语,甚至不乏粗俗之词。如张宗昌的《咏雪》:
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灰呀筛石灰。
再如:
仿佛昨天才恋爱,转眼青春就不在。
当年那个万人迷,如今已成老太太。
打油诗在表达上比较喜欢直白,因为直白才有诙谐、幽默的效果。
四、诗在意境上追求模糊,而打油诗的意境则非常直白。1、诗非常讲究意境,尤其注意意境的模糊性,喜欢塑造一种朦胧美,任人想象。如《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从这首诗的四句话来看,每一句都在写自然山水,但是仔细琢磨,山色分明,但流水却无声;花开四季,鸟却不怕人。人们只有从“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反常中琢磨才会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一幅山水花鸟风景画。
2、与诗不一样,打油诗虽然也勾画意境,但意境大多非常直白,读完了人们就明白了,不用想象。如《咏塔》:
远看石塔黑乎乎,上面细来下面粗。
有朝一日翻过来,下面细来上面粗。
再如朱元璋(相传)的《金鸡报晓》:
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日,扫败残星与晓月。
以上罗列四点就是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古体诗和自由诗不太讲究严格的平仄,但是押韵和遣词造句还是比较注意的,在诗歌意境的塑造上也非常讲究。古体诗和自由诗体裁的打油诗和古体诗、自由诗的界限,莫过于这三个方面。
由于个人见识有限,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可能还有很多未尽之处,欢迎大家指点补充。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