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这是文人相轻还是肺腑之言?
范曾狂到无知,以至品德丧失,为一投机钻营画手,我最瞧不起这种人。艺坛立足,先要做人,次为技艺。人品不行,画艺终无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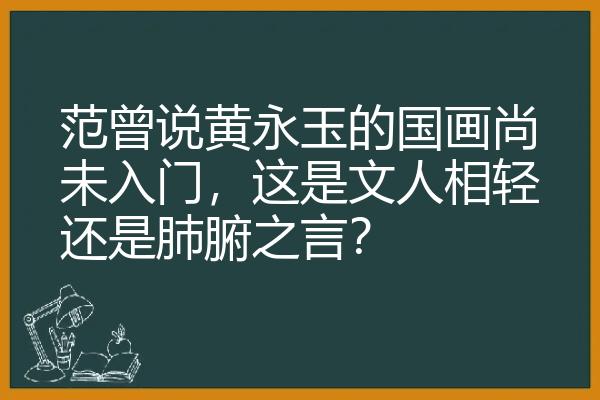
范曾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这是文人相轻还是肺腑之言?
谁都可以评价别人。但就这个案例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先谈一下。
第一是国画的入门问题。究竟怎样才算入门?尽管没有标准答案,但搞专业的人总有一些基本共识。具备一定笔墨、造型、构图能力,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能够对传统绘画精神有基本的掌握和领悟,并在创作中有所贯彻体现,应该就算是入门了。从这个角度看,黄永玉先生显然不是没入门。
第二是谁评价谁的问题。如果是一个不相干的外行作此评价,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但一个老学生如此跳脚骂街般地评价老师,是不是文人作派,有没有客观公允,显然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去赘述这些与艺术无关的事情了。
还是谈谈黄永玉先生的艺术。在我看来,黄永玉先生是对中国画有传承、有发展的艺术大家。对于中国画现代性转型问题,多数画人还处于无感的状态,他们以为有些笔墨能力,牵强附会地用传统文化装装门面,在前辈大师的作品上动点脑子、变变样子,就是名家大师了。这种浅层思维很可悲,在几十年浮躁的社会中造就了许许多多浅薄的笑话。黄永玉不然,他走出了传统文人画的条条框框,创造了多样的艺术面貌。他的重彩荷花、山水,无论是在色彩、笔墨、造型、图式等方面的提炼与再造,还是在审美境界的拓展,文化情怀的呈现等诸多方面都是卓有建树的,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具备了承前启后的意义。
黄永玉先生的水墨画,不拘泥于刻板的旧程式和晦涩的文化趣味,而是用轻松自由的笔调,幽默诙谐的情趣,现代文人的机敏与旷达,呈现给人们一种别样的艺术趣味,这是对那种古典的、晦涩的、为少数阶层所把玩的“文人画”的挑战与颠覆。既有中国画的笔墨情趣,又有现代社会喜闻乐见的大众情感,可以说是现代“新文人画”。
那种把国画狭隘地理解为古典文人画,看到别人的作品稍有不同便大加伐挞的人,应该想想,自己是否可以拒绝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搬到博物馆里与他们崇尚的千年不变的文人画厮守一生。
范曾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这是文人相轻还是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相较范曾,黄永玉明显弱了。弱在中国画技法和情感上,虽然,范也不是绝世高手。
黄的特色在漫画或版画,他的画脱不了此两类风格
但在人格上,范输了。
一,范和沈从文的关系:
1.文革中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最多的居然
是他曾经帮助的范曾,范曾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于是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表达观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2.一九六二年范曾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家门:“昨晚梦见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3.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先生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党中央批准的,你靠边站吧。”于是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后来不再提范的名字。”
4.沈对范有师生之谊。
二、范曾的去国
对一个在特定时间内,严重伤害过国家的叛国者来说,这个坎是无法绕的。
三、范的不认女儿,在社区上反响极坏。
而黄不同,一和范交手,就打着为表叔沈从文申张正气的旗号,其实,在人心中,范已经败给黄了。在中国,重人格甚于艺格,所以,大众置疑范就不稀奇了
范曾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这是文人相轻还是肺腑之言?
要我说,这一准是文人相轻。可李敖评价范曾,却是肺腑之言:范曾人品有问题,当属可信。他的画,乍看不错,但看多了,千篇一律。他的字,做作讨厌,帐房的毛笔字而已。他那些画,真是只适合给小学语文课本当插图使啊。
范曾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这是文人相轻还是肺腑之言?
黄永玉是艺术家,天赋灵性,多才多艺;黄的画很有味道。
范曾是个科班出身的画家,名声很大,自视甚高;范的画不耐看,鬼神仙子的神态雷同,自诩为中国第一的线描技艺,仿佛连环画,并无引人入胜之处,并无神来之笔,勾魂之韵;画面构成单调,无论众人像单人像,总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乏味,无趣,仿佛看连环画的感觉。
可能,水平所限观点偏颇,请有识之士指正。
范曾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这是文人相轻还是肺腑之言?
“文人相轻”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圈非常普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真实人性的自然流露,很难用对错好坏去评价它的存在。
因为人性中多多少少都有自私自利的成分,每个人在遇到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都会不由自主地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对他人无端轻视和诋毁,而对自己竭尽所能地抬高和吹捧,在商界这种情况很多。当两个文人之间因为一些利益产生矛盾,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文人相轻”的现象。
黄永玉先生和范曾先生都是当代著名画家,前者比后者年长14岁,实际上,两人有师徒关系。20世纪50年代,30岁出头的黄永玉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画家,被聘请到中央美院做教授,而范曾在此时还是一名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
看到范曾是可塑之才,黄永玉对范曾非常器重,经常指导范曾怎样画画。范曾也是聪明人,有空就去黄永玉家里帮忙干些杂活,把师徒关系处理得很融洽,这种做法让范曾的绘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
后来,在某次学术讨论会上,两人因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范曾虽然不认可黄永玉的观点,但他说不出有说服力的观点把黄永玉驳倒。
因为这件事,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缝。年轻气盛的范曾一怒之下画了一幅画,画面内容为:一只哈巴狗叼着骨头,脖子上拴着铁链被一个秃顶外国人牵着,外国人看起来非常傲慢,用左手撩拨着狗头,似乎随时可以断掉狗粮。
范曾并不满足自己欣赏这幅画,在后来还把这幅画公开发表。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幅画的真实用意,他用绘画讽刺了黄永玉先生。
黄永玉看到后很气愤,随即回敬范曾一幅,画了一张名叫《永玉画猪》的漫画,画面是一个长相怪异的人光着上身,叼着烟斗,握着毛笔正要给笔尖敷色,却心不在焉,眯着眼,并不看颜料盒,神情有些傲慢。
两人相互用画诋毁对方后,导致两人的关系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几乎在一些公开场合见了面,也不跟对方打招呼。
再后来,随着范曾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有些自我膨胀,心血来潮时常常口无遮掩,在一次公开场合,当别人问到黄永玉的画怎么样时,范曾直接说: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
当然,在2008年,范曾和黄永玉“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又是后话了。
如果抛开两人的个人恩怨来看,我觉得,范曾这句话说得有些狂妄自大,也有些本末倒置,完全是“文人相轻”的体现。
众所周知,黄永玉先生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版画和漫画的创作上,他在这两个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
黄永玉在版画创作上,广泛吸收了农民画的特点,线条流畅,黑白对比关系突出,物象造型夸张有趣,有极强的装饰趣味,开启了版画创作的新高峰。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中后期,很少有人在版画创作上能达到他的高度。
他的漫画同样很出色,风格诙谐幽默,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趣味,让人看起来很轻松。同时,他在漫画创作中,吸收了“文人画”的许多特点,比如,对笔情墨趣的使用,对托物言志的运用,驾驭笔墨在画中嬉笑怒骂,把自己的真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毫无疑问,黄永玉先生是自丰子恺先生后,在漫画领域成就最高的大家,到目前还没有人能撼动他在版画的地位。
艺术是相通的,以黄永玉在版画和漫画上的造诣,他画起国画也是轻车熟路,但他并不墨守成规,故意跟传统国画拉开了距离,
传统水墨画追求“计白当黑”,黄永玉偏不这样画,他喜欢用浓墨重彩来表现物象厚重的体积感,以及充满生机的力度感,进而展现出物象绚丽灿烂的生命情调。
从本质来看,黄永玉的国画在技法上虽然跟传统国画有区别,但在精神层面的表达上,并没有偏离国画的内核,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新式文人画,认真欣赏他笔下的重彩荷花,就能明白他在国画上的真实水准。
深谙国画传统,却不按照传统的套路来,始终遵循创作上的自由,能做到这一点,试问国内画坛还有谁?
擅长用“勾填法”古代人物的范曾,肯定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说,范曾评价“黄永玉的国画尚未入门”不是肺腑之言,是范曾对自己国画不够自信的虚张声势的表现。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