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宋江有称帝野心吗?
宋江浔阳楼题反诗,其实并不是说自己,也不是说当时,而是两首“预言诗(词)”。而且,宋江题写反诗的地方不是江西九江,而是江苏镇江。因而,“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说的不是宋江有称帝野心,而是另有所指。
心在山东身在吴《水浒传》中,宋江发配到江州牢城,吴学究启用卧底戴宗,十分的关照宋江。于是,宋江经常外出下馆子。江州城中有琵琶亭、浔阳楼两大豪华大酒店,宋江、戴宗、李逵三人,后来还加入了张顺,时不常的到此打牙祭。
文本说得很清楚,宋江喝酒的酒楼就是在江西九江。而且,九江古称浔阳,“浔阳江”就是长江流经江西境内那一段的特别名称,《水浒传》的江州不是江西九江,难道是江苏镇江?
但是,假如倒回去看,情况就不对了。
宋江从山东郓城县出发,一路前行,经过了揭阳岭、揭阳镇,施耐庵说,揭阳镇就在江州的对岸。然而,九江的对面却找不到这两个地方。到了江州劫法场时,宋江又智取“无为军”。“无为军”在哪里?安徽境内!今安徽无为县无城镇。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建无为军,领巢县、庐江二县,属淮南道。北宋时期以军、州为行政区划,《水浒传》中说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讲的就是这件事。
然而,施耐庵说,无为军也在江州的对岸,隔着一条浔阳江。那么,假如说“江州”因为浔阳江而跑到江西去了,无为军便也在江西?
施耐庵这是在移花接木,掩人耳目,要隐写一段秘史。在不断以浔阳江、琵琶亭、浔阳楼等是否明确的信息吸引了读者(当时的读者)的眼球后,不经意的通过宋江的诗,点明了“江州”在江苏境内。
“心在山东身在吴”,宋江是山东郓城人,因不幸刺文双颊而飘蓬江海,来到了“吴”地。很明显,江西九江属于赣而不在“吴”。所以,《水浒传》中的江州写的是吴地中的一个州。那么,为什么能确定是镇江呢?
江州知府蔡九蔡得章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既然点到了历史真实中的人物,那么,这个蔡九知府就有可能找到原型了。
蔡京有八个儿子,其中,老三蔡翛做过镇江留守。施耐庵巧妙的以“三”、“九”这两个数字的关系,隐写了蔡九知府的原型就是蔡翛。
大致可以无疑问的说,《水浒传》宋江题写反诗的江州,应当是江苏镇江。那么,施耐庵为何要写得这般纠缠,直接写明白多好,总可以避免后世读者说施先生的地理是体育老师教的。
他年若得报冤仇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写的一首词,一首诗,读来毫无道理,此时,宋押司跟谁有如此深仇大恨呀?江州的人谁又招惹了及时雨宋公明呢?
杀了阎婆惜,是宋江自己招的祸事,私通梁山贼寇,难道还不许别人索要封口费?阎婆惜乘机敲诈固然有错,但宋江确实有错在先,不能怨恨他人,何况,阎婆惜已经被杀了,还报什么冤仇。
此后,朱仝义释宋公明,流落江湖时,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燕顺等人格外的爱戴跟随,浔阳江兄弟更是追随得紧,宋江应当心怀感恩才对,怎么陡然心怀冤仇了?
赵能赵得固然是恶吏,抓了宋江,让他发配江州,这也怨不得,要怨就怨宋太公,装死骗了宋江,让儿子服法。宋江总不能因此怀恨老父,写诗要报冤仇吧。
《西江月》词上阙写了宋江自己的经历,倒是看得出来宋江因科举仕途失意,又遭刺文双颊而“潜伏爪牙忍受”。刺文双颊怨不得别人,科举失意只能怪自己是学渣。况且,宋江在郓城县押司职位上干得很欢实,哪里看得出押司哥哥跟谁有冤仇了?何况,这与江州又有何相干呢?宋江是不是迷糊了?
书中也确实写到,戴宗说起宋江题诗被黄文炳告到了蔡九知府那里,被定性为反诗。宋江此时显得有些装,说自己喝高了,不记得了。然而,书中题写反诗过程的细节却出卖了宋江。
当时,宋江喝了几杯酒,回想自己的遭遇,幻想“他日身荣”,便乘着酒兴题写了两首诗词。而且,宋江边写边手舞足蹈,写完《西江月》还嫌不过瘾,又写了一首七绝。书中说,宋江在事后落了款:写罢,掷笔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饮过数杯酒,不觉沉醉,力不胜酒。
完成了诗词创作,又喝了数杯酒,宋江这才“不觉沉醉,力不胜酒”的。所以,搞创作的时候,宋江仅是达到了高度亢奋的状态,并没有犯糊涂。
宋江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因而,明白无误的寄托了自己的志向,“敢笑黄巢不丈夫”。不过,宋江说的是“他年若得报冤仇”,并不是当时就要搞事情。
宋江跟谁都没有冤仇,属于典型的无病呻吟。《水浒传》前七十回书中,也没写到宋江“血染浔阳江口”。江州劫法场连同官军百姓,也只死伤五百多人,怎么好意思夸口“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题写反诗毫无由头,《水浒传》也没有更多的情节,甚至没有故事来印证宋江反诗要做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只是为了写宋江上梁山而平白生出来的故事呢?肯定不是。如题主所质疑的那样,宋江是不是要学黄巢,妄图称帝呢?
宋江题反诗原来如此上文讲到,宋江浔阳楼的反诗实际上是“预言诗”,说的不是当下,而是将来。也就是说,宋江发誓要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以赶超黄巢,将在七十回书之后才有故事照应。
《水浒传》中有三大预言诗,即:林冲在朱贵酒店题写的五律,“京国显英雄”、“威震泰山东”说的是林冲与梁山好汉参与东京保卫战,以及在泰山之东抗金的故事。假如不是这样,林冲的这首诗又作何解读呢?施耐庵难道顾头不顾尾,胡乱写林冲“京国显英雄”?前七十回书中,林冲在东京显英雄了吗?林冲又威镇过泰山东吗?
第二首预言诗,就是智真长老的四言偈子,预言了鲁智深追寻“汝等皆不及他”的正果过程。前七十回书中,鲁智深的正果是没有得到验证的,必定要到梁山大聚义之后才有故事予以印证。
第三首预言诗(词),就是宋江在浔阳楼酒店粉壁上题写的《西江月》和那首“敢笑黄巢不丈夫”的七绝。
其他诸如九天玄女的四句“天言”,罗真人的八字真言,都涉嫌续书作者所为,大致是不能当做《水浒传》来读的。比如,九天玄女的“外夷及内寇,四处见奇功”,就是续书作者不断篡改的。罗真人告诫公孙胜“逢幽而止,遇汴而还”,公孙胜却违抗了师命,打完辽国后,继续跟随宋江去征田虎、剿王庆。公孙胜胆子可够大的。
《水浒传》的写作手法极其高明,以预言设置悬念,从开篇故事起便屡屡如此。这是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吸引读者,增强故事的可读性,尤其是以这样的悬念把故事很好的串联起来,形成严密的文本逻辑。这种写法,也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大开大合,纵横捭阖,是长篇小说必备的套路。
那么,宋江的反诗又预言了怎样的故事呢?
从蔡九知府原型蔡翛来解读,宋江反诗所隐伏的故事,就是宋江在招安之后,将再度回到江州,以兑现施耐庵的“诺言”。这个“诺言”就是向宋徽宗讨还冤仇,梁山好汉再次造反,然后“血染浔阳江口”。
《宋史》及相关史料(《童贯传》、《蔡攸传》、《皇宋十朝纲要》、《纪事本末》等)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压境,宋徽宗仓皇难逃,到镇江复辟。
宋徽宗的南逃,是童贯、蔡攸、蔡翛共同策划的。事前,蔡氏兄弟商议,宋徽宗下台,蔡家就将衰败,蔡攸便把蔡翛从礼部尚书的位置上调任至镇江做留守。童贯则从太原抗金前线逃回,宋钦宗诏令他做东京留守,准备御驾亲征。但童贯拒不受命,与蔡氏兄弟裹挟宋徽宗复辟以自保。
《水浒传》的主题是“替天行道”,梁山好汉发誓“保境安民”。宋徽宗在国难当头之时分裂朝廷,在镇江以截留北运、阻断南北通信、阻止北上勤王军队,实际上就是谋反。这等国恨家仇,才当得起宋江反诗中所说的冤仇。
直接造了皇帝的反,宋江不想称帝,实际行动却不亚于黄巢。但是,宋江绝对不会有称帝野心。“敢笑黄巢不丈夫”的人不是宋江,而是宋徽宗。黄巢打下长安便称帝了,宋徽宗镇江复辟,试图再一次称帝,由此,引来了“血染浔阳江口”,黄巢在宋徽宗面前算什么真皇帝、真丈夫?
《水浒传》中除了宋江的反诗隐藏着宋徽宗复辟的历史外,九天玄女庙中的“二龙相戏”隐喻的也是这件事。
这么讲,问题来了。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写北宋历史根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其实,施耐庵在书中一击双鸣,还隐写了一段大明朝的秘史。
《水浒传》中真正敢笑黄巢的是谁“洪太尉误走妖魔”故事中,除了讲北宋妖魔出世外,同时还隐写了朱洪武放出了妖魔。朱洪武放出的妖魔,就是“孙立”,孙子越过叔叔辈,做了大明朝第二任皇帝。
施耐庵笔下的“妖魔”是与“替天行道”对立的关系,《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的主要含义是“天下太平”。朱洪武放出了“妖魔”,导致四年内战,天下还能太平吗?
于是,施耐庵以锦毛虎、雪花大蛇来预设了一场“龙虎斗”,这也是另一个版本的“二龙相戏”。洪太尉在龙虎山上遇到的锦毛虎就是燕顺,清风山的三个头领隐写了“燕王英武真天授”。而那条雪花大蛇隐喻的就是生于冬月的属蛇的朱允炆。
靖难之役以及朱允炆神秘失踪,在《水浒传》中不时的被隐写,其中,最集中的一处就是三打祝(朱)家庄。这个故事,我在图文中有专门文章解读,此处不再啰嗦。而潘金莲、潘巧云这两个背叛家长的不贞女性,也是靖难之役的两个重要符码——关于这一点,我将另外撰文解读。
另外,还有黄信的“丧门剑”,宋江被出籍,以隐喻朱洪武放走妖魔,导致“孙立”被逐出太庙,丧门奔逃。
总而言之,《水浒传》隐写了大明王朝在当时而言的高度隐秘,施耐庵能写得很明显吗?
朱棣于1402年攻破南京,朱允炆在大火中失踪(对看祝家庄被攻破,栾廷玉失踪的情节)。然后,朱棣派出搜寻队伍,出海密访建文帝(攻打祝家庄用水军,孙立先是琼州军官,后来又调任登州提辖,都是靠海之地,登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而在攻破南京之前的重要一役,就是击败守将盛庸,然后从瓜洲渡江,抵达镇江,由镇江攻至距南京仅三十公里的龙潭。随之,李景隆开城投降。
镇江不过是靖难之役的一个小节点,原本没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因为北宋时期的宋徽宗复辟就发生在镇江,所以,施耐庵一击双鸣,以一个地名隐写了两个朝代的“二龙相戏”。
朱棣夺位成功,当然就称帝了。如此,他才是真正的“敢笑黄巢不丈夫”的人。
现在,我们能读到的《水浒传》只有前七十回书是施耐庵写的,后面的故事都是续书。原来,《水浒传》在明朝时就被腰斩了。腰斩的原因,应当就是施耐庵隐写了建文帝的故事。
所以,宋江“他年若得报冤仇”、大有隐喻朱棣被建文帝削藩逼得装疯(宋江江州装疯),起兵靖难以报冤仇。
因而,《水浒传》中宋江在浔阳楼的题诗不是“诗言志”,而是在隐写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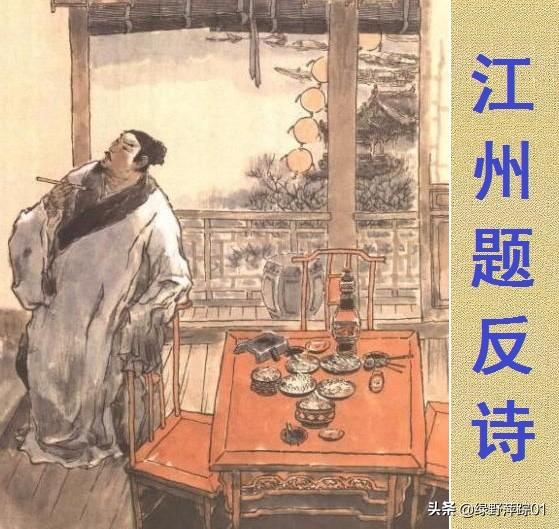
《水浒传》宋江有称帝野心吗?
大大地没有。
《水浒传》宋江有称帝野心吗?
宋江就是朝廷派去的卧底
《水浒传》宋江有称帝野心吗?
当然没有。
如果宋江有称帝野心,怎么会首倡、坚持、排除万难去招安呢?
当然,即使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即使是在今天,你吃饱喝足躺在沙发上,也可能偶然跟媳妇说一句“我要是皇帝就好了,不用只守着一个媳妇,可以有三宫六院”的玩笑话。这能算“称帝野心”吗?
光有想法,不能叫“野心”。有想法,并付诸行动,那才叫“野心”呢。
宋江“敢笑黄巢不丈夫”(题主写错了,不是“不仗义”),的确有对黄巢的鄙薄。黄巢也的确造过反、称过帝。但是不能只拿这一件事说话。
黄巢起义,规模很大,但是很快失败,本人也被部将所杀。也就是说,黄巢虽然做了一番事业,却不能很好地驾驭下属。至少在这一点上,宋江比他强:梁山好汉中反对招安的很多,可到宋江决定招安的时候,并没有人离他而去,更不用说与他刀兵相见了(武松等人退出、归隐,是以后的事了)。
宋江只是一个半官府、半江湖的中下层人士。“敢笑黄巢不丈夫”也只是他醉后所写。“酒后吐真言”,这句诗的确反映宋江有“凌云志”。可是醉后话,怎么能那么严谨?
《水浒传》宋江有称帝野心吗?
没有,压根一点都没有,他是那个时代“忠君爱国”思想的典型代表。不然也不会不顾后果也要呗朝廷招安,结果一杯毒酒就能赐死的人,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水浒传》宋江有称帝野心吗?
在水浒世界中,宋江领导的水泊梁山确实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过,从其确立的政治纲领看,从最开始,宋江就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
宋江成为梁山一把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梁山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布,尤其是向梁山众位兄弟宣布,他宋江想走的,并不是造反起义,黄袍加身的道路,而是效忠皇帝,效忠国家之路。
换言之,在梁山安身,只是宋江集团的权宜之计。他最终希望的是恢复合法身份,在朝廷谋求一份官职。
当然,一个人的目标是随着实力不断变化的。曹操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也没想到自己会一统中原,更没想到自己会独掌朝纲。实力越大,自然野心也就越大。
只是,宋江在扫平辽国,击破田庆、王虎之后,宋江的理想并未发生变化。
没有改变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是宋江在军事上虽然一路凯歌, 但是对于梁山集团的掌控上却渐渐有些力不从心。
梁山一百零八将明显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大阵营以宋江为首,包括花荣、戴宗以及关胜、秦明、呼延灼等一大批朝廷投降过来的将领。这部分人在梁山排位很高,在征讨四方时大多数活了下来。
很明显,宋江在刻意保全这部分人的性命。也可以说这些来自官场的老油条在保命神通上远超江湖草莽。
这些人与宋江更多的是合作关系。一旦宋江要起兵自立,许多人比如关胜、呼延灼等人便会与宋江分道扬镳。
第二大阵营是反对招安,比如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他们并不同意招安,但是看在宋江的情分上跟随宋江南征北战。这些人乐意的是大块喝酒,大碗吃肉的自由生活,对于什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没什么兴趣。
第三大阵营是像混江龙李俊那一帮江湖山贼水匪。这帮人到哪里都是混饭吃,其实根本没有融入梁山,更不会跟着宋江走到黑。于是,后来李俊这帮人都悄悄离开了。
梁山一百零八将看似兵强马壮,其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宋江能够将其短暂融合,但是,缺乏共同的目标,最终只能是分道扬镳。即便强行起兵,也注定了最后失败。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