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淳安和建德知县被砍头时直喊冤枉,他们到底冤不冤?
《大明王朝1566》真是一部传世佳作,不知道五十年内能否再有这样的好作品呈现。它以浙江“改稻为桑”这一件事,把大明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惨烈,以及人性的美与丑刻画得淋漓尽致,也照见了帝制王朝没落的必然性。
淳安县令常伯熙和建德县令张知良,候刑时痛苦流涕,期期艾艾地向李玄喊冤的场景,恐怕只能博得少数同病相怜者的眼泪。如果说他二人冤枉,请问李玄冤不冤枉?马宁远冤不冤枉?沈一石冤不冤枉?还有后来的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他们冤不冤枉?
如果再深一点说,高翰文呢?海瑞呢?甚至胡宗宪呢?每个人都有喊冤的理由,就连严世蕃都扯着嗓子,青筋暴凸地喊冤,似乎大明王朝就是个冤魂遍地的地狱。
常伯熙张知良的“冤”:利益团队随时抛弃的替罪羊官场上的事,难办就难在不光有黑白,还有灰色,而且绝大多数时候呈现灰色,甚至明显的黑白,一旦夹杂“人事”就变成“鬼事”,黑白也成了灰色。
所以,慢慢地常伯熙再也没有“熙”(光明),张知良再也不“知良”,像很多浸淫官场的老油条一样,他们只坚信一个“真理”——抱大腿。抱住了大腿就永远正确,甚至不需要再去分辨黑白,目盲比“熙”,比“良”更可靠。
于是,嘉靖王朝的天下,由几条大腿,形成几大派系:
- 严嵩这条腿下面,聚集了严世蕃、鄢懋卿、罗龙文、胡宗宪、郑泌昌、何茂才等核心骨干,和常伯熙、张知良这些基层“领导”;
- 裕王这条腿下面,聚集了徐玠、高拱、张居正、赵贞吉、谭纶、王用汲、海瑞等人;
- 吕芳这条腿下面,聚集了黄锦、杨金水、李玄、沈一石等。
常伯熙张知良的逻辑很简单:改稻为桑是国策,中央由严阁老支持,地方由胡宗宪领衔,郑泌昌何茂才主导,顶头上司马宁远“秉承”胡总督的意思,全力推进。从上到下,一体同心。另一条线,杨金水直言:你们地方怎么办我不管,我只要一年生产出五十万匹丝绸。
一个毫无争议的决策,作为执行人,严格按领导意思办就是“正确”。包括“决堤淹田”,手段虽然恶劣了一些,还不是为大局服务嘛。
决策是小阁老下达,执行令由郑泌昌何茂才下达,还有杨金水在场拍板,万无一失的事,怎么就办成了“堤坝豆腐渣工程”事件?自己还得莫名其妙背锅,有这么黑白颠倒的事么?
头一年修堤,明明是固若金汤,竟然要为决堤买单。常伯熙和张知良觉得冤,工程负责人李玄更冤,他连喊冤的资格都没有就“畏罪自杀”。
常伯熙张知良的第二个冤屈:我们忠心耿耿执行命令,出了事为何没有一位领导出面替我们扛一下,而是直接把屎盆子扣我们头上?这不符合“抱大腿”的规则嘛!
本着“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常伯熙和张知良无非是吃点碎渣渣的狗仔,棒子打下来,他们觉得自己顶多是从犯。结果却是,主犯不问,从犯杀头,还有天理吗?
这件事体现出常伯熙张知良的愚蠢,郑泌昌何茂才就想得明白,无非就是替罪羊嘛,自救啊,要完蛋一起完蛋!杨金水笑了,你们也是蠢蛋一枚,想同归于尽你们还没那本事!
沈一石也笑了:杨公公你既然清楚这一点,何必活受罪呢?你看我一把大火,干干净净,到地下,冷眼看你们咬得血淋淋!
常伯熙张知良的“该”:失去灵魂必遭天谴的作孽人在《大明王朝1566》中,常伯熙和张知良不光愚蠢,也是最没有灵魂的人,助纣为虐都毫无知觉。
深陷政治斗争的人,虽然难逃站队,可是并不代表要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
比如海瑞,表面上他是裕王的人,骨子里他只为自己的信仰活着。所以,他能顶着压力,管你是哪路鬼怪,一律迎头痛击。在“改稻为桑”上,他的思想与裕王派切合,他按自己信仰做;“改稻为桑”后,他上万言书痛斥嘉靖帝,其实并不符合裕王的利益,他还是按自己的信仰做。
再比如胡宗宪,身子站在严嵩一边,心里却装着一个超脱于私利的“国家利益”,所以,连严嵩也夸他“公忠体国”。
甚至连沈一石,就当所有人认为,这就是个黑透了的奸商时,他却在火光中让人为他流泪。
相对于这三个人,常伯熙张知良面临的难度,一点不比他们高,二人就活不出高度来,自愿当别人利益的攫取者,下场活该!
即便马宁远,表面上跟常伯熙张知良一样,都是抱大腿之流,可马宁远的结局,多少还能让人报以同情。因为马宁远至少有一点值得赞许:他所做的事没有私心杂念。
马宁远做事只有一个念头,替胡宗宪排雷,为了胡宗宪不受伤害,他甘愿冒杀头的风险。事实上他这么做是一个格局很低,视野很窄的愚蠢行为,往往帮倒忙,可是其初衷值得肯定。
常伯熙张知良连这点“愚忠”都没有,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与利益集团之间,只是利益交换,所以,其作恶行为,不全是被动,说到底还是利益驱使。
从这个角度看,常伯熙张知良死得一点都不冤,不说他们治下的百姓,利益集团抛弃他们都不会觉得有所亏欠!
常伯熙张知良的“痛”:漫天飞雪没人躲得过寒夜看《大明王朝1566》,常常会让人迷茫: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叫智慧,把简单的事复杂化,那叫什么?愚蠢吗?可是嘉靖王朝的政治核心人物们,都是在做“化简为繁”的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利益需要!
大明帝国有一个最大的蛀虫——嘉靖皇帝!严嵩集团的生存,恰恰就是利用了嘉靖皇帝的自私。严嵩集团打着为君父分忧的旗号,四处搜刮钱财,乘机往自家银库里划拉银子。
嘉靖帝心知肚明,甚至公开说:一两银子他们得五成,朕认了,甚至他们得六成,朕也认了!无利不起早,这种给老大打野食的事,只有贪嘴猫才能干得出来,你不让他乘机渔利,谁替你起早带晚?
不光严嵩集团,杨金水其实也是充当这个角色,只不过他们相对于严嵩集团,对皇帝的忠更纯粹些。
为了防止猫太贪嘴,嘉靖帝又刻意培养徐玠,虎视眈眈盯着严嵩一党。有意思的是,无论哪一派,都不敢点破矛盾的实质,形成一明一暗两条线的较量。
明线上,严嵩一党打着改稻为桑,为国家解决财政危机,同时强国富民,把自己打扮成忠君爱国的模样,指责徐玠等人不顾大体,破坏国策。
暗线上,严党借着改稻为桑,大搞土地兼并,乘机对中小商人敲诈勒索。他们一边与嘉靖帝分赃,一边贼喊捉贼。
徐玠一党也不纯粹,为了扳倒严党,他们一边挥刀砍黑手,一边小心翼翼地躲避触碰嘉靖这只尊贵的爪子。因为难度太大,所以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阻止赵贞吉借粮给浙江,逼浙江百姓造反,让严党走进死胡同。
两头受气的是胡宗宪,离开严嵩的庇护,他一事无成,学常伯熙张知良,他自己必然是严党攫取利益的工具,逃不脱被抛弃的命运。所以,他身在严党,却要跟严党“作对”,与徐玠不是一条战线,却被迫与徐玠虚与委蛇。
这就是局势由简化繁的原因,谁都知道根子在哪里,谁都不愿意,也不敢说破,都努力地在恶劣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只有一个人例外——海瑞。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一现的纯粹的人。当他看清了大明王朝的病根后,不躲不藏,一封奏疏直抵嘉靖的御案,让这个大明王朝的腐败之根无处躲藏!
当然,帝制文化的大环境,注定海瑞的努力化作泡影,连海瑞自己也摆脱不了愚忠的紧箍咒。
所以,常伯熙张知良的下场,其实是帝制文化结构下的必然,嘉靖皇帝就是大明的严冬,它降下的雪花没人能躲得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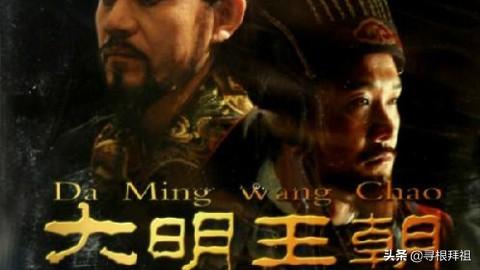
大明王朝:淳安和建德知县被砍头时直喊冤枉,他们到底冤不冤?
他们冤?
他们俩最该死了!
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就真难了!
其实翻遍史书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个贪官是一心只管贪的,大都上任时,也是胸怀天下,也是想造福百姓的。毕竟是人,又是有头有脸的人,还是饱读诗书的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
可以说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是一心跟在杭州知府马宁远后面跑的。而马宁远又一心要报答浙直总督胡宗宪,胡宗宪又是严阁老的人,正所谓一环扣一环,扣在最后还是一环。
包括严嵩,当首辅的这些年,也是一心要管好大明朝,也没想过一定要陷害忠良,除非他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可是,人往上爬,就得踩到别人,爬得越高权力越大,也就越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也就越想掌握更大的权力以获得安全感,也就越往上爬,最终爬到顶峰,无路可爬。
自古权利跟义务是划等号的,严嵩掌握了明帝国一人之下的权力,那就得享有一人之下的义务。所以,当大明朝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最担心的不是嘉靖帝,而是严嵩!
要解决国库空虚问题,严党提出了“改稻为桑”国策,并得到了嘉靖帝的赞同,随后便严格推广起来。可以这样说,这条政策的出台,单从设计的路线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了最终落实政策的基层上面。
也就是浙江地面,以及地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级官员,他们怎么去发动老百姓推行这项政策的执行是关键!
二、
“改稻为桑”国策的制定是在正月,杭州知府马宁远带着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军士去踏苗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份了。
可以说,这期间的三个月,马宁远、常伯熙和张知良没少对百姓费口舌,至少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出踏苗的损招,不然马宁远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
甚至,他们还把新安江的堰口给堵死了,当然,他们此举并非是为了毁堤淹田,而是为了不放水,迫使百姓放弃种植水稻。
其实当时胡宗宪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如果百姓自愿改稻为桑,那最好,如果不能,那也不能逼迫百姓这样干。
到这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都还是比较理智的,面对不够理智的上级,常伯熙还劝他回去再商量别的办法,别跟百姓硬刚,结果被马宁远威胁拿了他乌纱帽:
“怕死了?怕死就把纱帽留下,你们走。”
从马宁远的话中可以看出,常伯熙和张知良俩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基本没有发话的权力,只能被马宁远裹挟着向前走,除非俩人的知县不要当了。
既然不用这两位知县出面硬刚,有上级在现场亲自指挥,他们俩自然也就没有退缩的可能性。尤其是马宁远,总是在放狠话,什么人都死绝了也得改,什么自己就站在这:
“本府台现在就一个人站在这里!敢造反的就过来,把我扔到这河里去!”
三、
可以说,到这时候为止,淳安知县常伯熙和建德知县张知良都不用负责任的,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俩人也被砍了呢?
就是因为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
为什么说,这俩人参与了毁堤淹田后,必死无疑呢,下面听杨角风来给大家进一步分析:
毁堤淹田的命令是严世蕃下达的,就是因为胡宗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希望朝廷逼着老百姓改稻为桑。所以,这条命令并没有直接下给胡宗宪,而是瞒着胡宗宪下给了郑泌昌和何茂才。
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想让计划落地,首先得拉拢朝廷派到浙江的一条“狗”——杨金水,这一点两者利益一致,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其次便是找执行者,以及日后东窗事发后的替罪羊,也就是杭州知府马宁远。
因为他们要淹的就是杭州府的地界,当然得跟当地的最高指挥官达成一致意见啊。参考后来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他如果不配合,郑泌昌和何茂才都拿他没办法。
记住,到此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是跟马宁远捆绑在一起的,真正让马宁远下定决心干蠢事的是杨金水的这句话:
“忠上司认主子是你的长处,但是我问你,你听胡部堂的,胡部堂听谁的?还不是听严阁老小阁老的?那么你听严阁老小阁老的,还能有错?”
但后面两个知县的做法就彻底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四、
不管胡宗宪按哪种方式汇报毁堤淹田之事,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都必死无疑:
按照小阁老的想法,这次新安江决堤,把责任归结于天灾。可是,遍观史书,任何一个地方发灾,不管是什么原因,父母官是必须要到现场赈灾的。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官不足以处理大灾,那么省级,朝廷都得派钦差前来处理,没有例外。
而这次新安江决堤,按照后来海瑞查实的情况是:
“一夜之间,整个淳安半个建德全在洪水之中,死亡百姓三千余人,无家可归三十余万!”
这已经是大灾了,一夜之间就死亡了三千多人,马宁远尚知道跟郑泌昌和何茂才要求:
一是不能饿死人,二是不能让胡部堂下不了台,当然,他肯定没有预料到后来胡宗宪是掘开了淳安建德两处口子。虽保住了其他几个县,但水都去了淳安和建德,自然就导致大水淹死了人更多。
可是当胡宗宪跟谭伦在前线赈灾的时候,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跟郑泌昌和何茂才喝酒庆功,这就是找死,日后不管这场灾难是怎么发生的,他俩必死无疑。
尤其是这句神来之笔,当马宁远讲自己如果还在这里喝酒,那就是没了心肝,扭头就要去找胡宗宪时,常伯熙和张知良还在问:
“我们要不要去呀?”
做人愚蠢到这个地步,还指望能保住命?
五、
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小阁老的理论,把决堤按天灾来算,淳安和建德两位知县也难逃一死,除了救灾不力以外,还有另外一条理由,这一条后来胡宗宪也讲了:
同样的暴雨,同样的江河,临省的江只花了新安江一半的修堤款,人家那固若金汤,我们这里这个谎怎么圆?
不仅胡宗宪不信,当时的河道监管李玄也不信啊,当时他就找杨金水了:
“干爹,干爹,九个县,九个县的堰口都,都裂了,一定有人要决口,这是要害儿子,害干爹您呐!”
他都清楚,这种桃花汛根本不可能让新安江决堤,肯定是人为的,肯定是有人在害他。
那么作为淳安和建德两县,修堤到自己管辖范围时,必然会经手参与。光修堤不力的罪名,也可以砍了他俩的头,事实上也是以这个理由砍了他们。
这还是在天灾的前提下,如果是人祸,那他们俩更是无处可逃,因为这个堤就是他俩参与决开的,还是后来海瑞的审讯何茂才时记录的口供:
“据查,原杭州知府马宁远,原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知良,在端午汛到来之前便带着你臬司衙门的官兵,守在九县每个闸口,五月初三汛潮上涨,九个闸口同时决堤,你的官兵一夜之间全部撤回。”
记住,这俩知县竟然糊涂到带着士兵,挖开口子,淹了自己管辖的地盘,这种父母官,不杀怎么安抚民众?
历来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百姓遭殃之后,先干掉的就是地方官,以便给百姓交代。
那么淳安和建德的这两名知县,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说服马宁远,停止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说服不了,可以当场辞职不干,以马宁远的脾气,会批准的。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命,除此之外,只要存在了毁堤淹田的这个动作,只要有百姓因此而死亡。那么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大员,都不可能这样轻易放过去,即使是他们刻意为之,也必然找出几个替罪羊,以平复民怨。
既然是找替罪羊,那么谁会首当其冲呢?
必然就是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幸亏胡宗宪牺牲了这两个县。如果没有处理,任由九个县被淹,那么其他七个县的县令,脑袋也就跟着一起落地了。
淳安知县常伯熙,还有建德知县张知良,以及杭州知府马宁远的死也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胡宗宪以他们三个的供词,逼迫郑泌昌、何茂才、杨金水在自己报的河堤失修奏折上签了字。如果没有他们三个的供词做威胁,他们三个哪里肯这么容易就范?
常伯熙和张知良临死前,还在哭哭啼啼地喊冤:
“李公公,我们冤枉啊!”
你们冤枉?
你们最该死了!
大明王朝:淳安和建德知县被砍头时直喊冤枉,他们到底冤不冤?
这两个县令和马宁远 发生决堤后无论如何都要死,按剧情来讲那两个县令辞职都会抓回来处死,谁都知道是毁堤淹田,但定罪是河堤失修贪没修堤款,
要么多杀几个泄愤。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