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平淡的语气写出虐到让人喘不过气,或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惊的感觉?
参考:
-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纸短情长,古人最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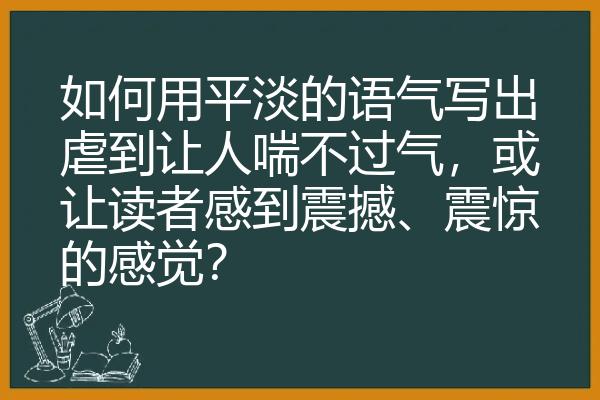
如何用平淡的语气写出虐到让人喘不过气,或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惊的感觉?
说个这两天在建筑工地上遇到的事吧
新建楼高十一层,
建筑垃圾往外清。
工地塔吊特别忙,
要求人工窗外扬。
粉尘污染不允许,
沙土堆好用水涂。
一切准备都妥当,
拿起铁锨向外扬。
这时又有新情况,楼下有个大‘平台,有人正在做防水施工。按距离推算,都在安全范围以内,其中一彪悍女子,抬头向楼上高喊,要我们停止工作,避免伤害到她们。对这种无理要求,公司领导也告诉她,双方各自施工,都不受影响。怎奈女子仍不算完,不让我们施工,让我们离她再远点即可。
领导也很无奈,也很犯难。我对领导说,让她带根绳子上楼来。女子一会气喘吁吁地上来了,让她看一看周围环境和距离。领导和众人都规劝,女子执意说不行。
我来出个主意吧,对女子说,你把绳子拴在楼前面,你体格建壮在前边拉,我在后面推,咱俩把楼往前移动一下,啥位置合适,你就停下,咱互不干扰。众人哄堂大笑,女子无趣离开。
建筑工地,项目繁多且复杂,要互相谦让,安全第一,不能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相互影响,就会减缓工程进度;互相关照,项目就能提前完工,何乐而不为呢。予人方便,自己也方面,凡事应顾全大局,不可小肚鸡肠。
如何用平淡的语气写出虐到让人喘不过气,或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惊的感觉?
余华在他的名著《活着》的前言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他说作家写小说时,应该“对善和恶一视同仁”。
事实上他的《活着》就是这样写的,很多古今中外的大家也是这样写小说的。
作家越是保持中立,越能触发读者的情绪。
作家如果拉偏架,立场鲜明,读者反倒可能无动于衷。
人总是自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是非、道德立场,不信任说教,不喜欢被强加。
真正伟大的作家是没有利益的考虑的,他们只有是非、善恶的判断和一颗公正的心。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是哪一个大作家说过,“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能大量产生才情”。
此外,作家对于所有人物、情节、场面、细节的描写,应该是客观的、真实可信的,所以尽管描写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但总是以真实为前提,不管你夸张渲染还是淡淡道来,读者发现作者说假话,描写失真,是会无动于衷甚至反感的,更不会如你所言,感到喘不过气来,震惊、震撼。
《红楼梦》里全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真实,但读者会感到震撼。
《红楼梦》的语言是淡淡道来,从不呼天抢地,即使写到人生最大最大的悲剧。
曹雪芹淡淡说道,“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可是,读者的心灵,似有破裂之感。
真实的力量无可匹敌,不管你用哪种语言说出。
学生作文或平庸作家的作品才会全力突出中心思想或曰主题,生活复杂到让你无法抓住它的主题。
所以有的后现代小说因为价值多元价值解构碎片化表达,更主题模糊到不知所云,须让读者参与创作。
最后,要让读者喘不过气来,感到震惊、震撼,首先类似于作者笔下所写的人和事,应该曾经让作者有过同样的感觉。
所以有些作家写着写着会哭起来会彻夜难眠。
如何用平淡的语气写出虐到让人喘不过气,或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惊的感觉?
用平淡的语言写出触动人心的句子,建议题主看看王了了的《你是温暖,逆光而来》,这本小说写的是温柔男主因为母亲而失去女主,霸道男二强势上位的故事,男女主是青梅竹马,女主其实很喜欢男主的,但是男主因为不是女主的良人,所以终究需要告别。女主从小被妈妈教导要好好和男主相处,女主妈妈去世后,男主变成了她对妈妈情感的寄托,她以自己的方式护着男主,也许有一点儿霸道,惹得男主反感了,但男内心深处是喜欢女主的,只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主女主爸爸破产,女主要离开这个城市。她最后一次跟在男主身后,男主下地铁后,女主在地铁车厢里,男主在车厢外,报站的女音掩盖了女主说不出口的告别,车动了,就这样两个人离别,那个场面文字很平淡,但很催泪。还好,“嚣张”的孔不离,最终有最适合她的龙千秋,爱你,千秋不离!这本小说我高中时看的,现在仍会偶尔回味,去体味什么是适合的爱情。
如何用平淡的语气写出虐到让人喘不过气,或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惊的感觉?
哈哈排比句,气贯长虹,喘不过气,有气势
如何用平淡的语气写出虐到让人喘不过气,或让读者感到震撼、震惊的感觉?
这是个语言风格的问题。我以为只有文学(语言)大师才能抵达这样的语言境界。先请读者欣赏一下下面这段文字:
“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
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这是“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的结尾部分。博尔赫斯的早期小说带有巴洛克风格,而晚期则喜欢“直截了当”的叙事。
匕首,恶棍,旷野,死亡,一触即发的械斗。这一切似乎就要在一次偶然事件的瞬间发生了,却又戛然而止。博尔赫斯是那种语言抵达事实速度极快的作家,就像武侠里传奇的“小李飞刀”:拔刀,掷出,刀子的飞行路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刀子一闪,已射进了你的身体,鲜血渗出。
博尔赫斯的小说总像诗一样精炼,优美,而又不失史诗般的故事性,将往昔的某种生活方式梦幻似的呈现。
一首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读;而一个故事,我们居然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首诗来读。(这难道是一种奇怪的阅读现象?)小说,是故事。但好小说,伟大的小说,本质上却是诗。然而,博尔赫斯笔下的小说(或诗),却富有哲学、美学的魅惑力。这种魅惑力被卡尔维诺概括为,“我在博尔赫斯的身上发现一个概念,亦即文学是由智性所建造、支配的世界。”(见《卡尔维诺评博尔赫斯》)
只要一接触博尔赫斯的小说,你就会被他的文字勾引进那个“由智性所建造、支配的世界”。我阅读博尔赫斯的感觉,被略萨用文字准确捕捉:“我一边翻阅,一边感到惊奇,如同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那样,为他行文的优美和简洁、故事的精巧和善于结构故事的完美手段惊叹不已。”
博尔赫斯最精致的小说,我以为集中体现在:《玫瑰角的汉子》,《小径分岔的花园》,《马可福音》,《埃玛·宗兹》,《南方》诸篇。其中,《南方》被博尔赫斯自诩为“最得意的故事”。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