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虽然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但也不是十一万明军片甲不留好不?
按《三朝辽事实录》里的记载,明军“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阵亡……等官共三百一十余员名……阵亡军丁共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名,阵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头只,今阵回见在并招集官军共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余员名。 ”
依据这则记载,萨尔浒之战,出征88,550名明军,阵亡46,180名,生还42,360名。
至于为啥明军会在萨尔浒大败,这个话题可以说是讨论烂了。
很多历史爱好者都知道是“分进合击”的四路明军遭遇“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后金军主力各个击破。但其实“分进合击”一种很常见的战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战术,是因为古代条件下,后勤运输手段有限,导致长距离后勤补给效率低,单位地理区域的补给输出也有一定限度的,故而组织十万级别的大规模进攻时,古人往往习惯把大军分开,以分担后勤的压力。
另外,参加过集体活动的读者肯定都会懂得,在道路宽度有限的情况下,大量人员一起移动,往往会形成一条很长的人流,军队行军更是如此。比如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鲁士一个包含42,512人、13,802匹马、90门炮、1,385辆运输车的军,要占用43.5公里长的道路。这个在军事术语方面被叫做行军长径。而明代根据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里记述, “ 路狭,挨次每一营鸳鸯阵双人行……前路宽一丈(约3.2米)……是二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一丈之外……是三鸳鸯阵平行……前路约宽二丈……是四鸳鸯阵平行”。根据其记述推算,明军行军时单人的宽度大约在0.8米。另外,根据对近现代部队行军的研究,步兵行军期间前后的距离大约在1.5米左右,而骑兵则是2.5到3米左右。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总兵力为88,550人,朝鲜盟军的兵力为13,230人。这十多万步骑兵,就算按步兵6人、骑兵4人并排行军估算,明军行军长径将达到36公里以上,即前军已经走到萨尔浒、而后军尚在抚顺城刚出发。显然,这样的一字长蛇阵,即无法作战,也无法保证行进速度,更没法保证后勤供应。
而且,赫图阿拉周边群山环绕,山谷之间河流弯延,不利大军行军与展开。比如《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 五岭特为险峻 ” ;兵部官员董承诏奏报 “ 越三关、逾五岭,闻其险隘之处,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驰 ”;扎喀关, “ 两山对峙,沟深峭陡,地势极为险要 ” 。
总之,受限于地理和后勤条件,明军要想执行攻击赫图阿拉、进剿后金这种外线作战任务,只能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没有合兵一处滚动前进的可能,即没必要也没有可以实现的地理环境(对于明军而言)”。
而这种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功的关键点,在于各支部队能够按照战前约定的时间,准时抵达应该抵达的地点,彼此呼应,相互掩护。
对此明军在出战前也进行了相关纪律的申明。比如违期逗留、观望不救援,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等纪律。但是即使三令五申,如果军队缺乏足够执行战术行动的能力,所有的纪律也就等于没说。
首先,成问题的是,这次明帝国出动八万八千人左右的明军是从各地抽调过来的。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精骑六千;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很多明军因为被抽调到千里之外的异地作战,求战之心不强,甚至“伏地哀号不愿出关”。
另外,明朝当时的制度是武官不能担任大军主帅,而是由更高阶的文官调度全局。四路的率军总兵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声望地位相仿、互不隶属。同时,明军为了弥补兵源短缺,不得不让一些有临阵脱逃劣迹的官兵也参与作战。比如,曾经对后金军望风而逃的抚安堡备御毛凤文、游击郑国良、白家堡备御周守廉、三岔儿堡备御左辅,都没有被严肃军纪,相反获准戴罪立功。而这种行为,其实本身就是对军事纪律的一种破坏。
士兵来自各地,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士气不振;主官又缺乏合作的基础,更没有建立应有的指挥序列;军纪又没有得到。这样一支军队,要求他们在人生地不熟、地形复杂的敌占区,实行对时间、地点与行军速度要求很高的“分进合击”战术,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辽镇明军素有轻敌冒进的风气,现在军队里又有临阵脱逃不受处分的逃兵,其结果自然是“勇者独进,怯者独退”。
其实面对缺乏地利与人和,准备又不够充分的“分进合击”战术,其实领军的总兵也大都看出问题。比如马林表示,“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刘綎则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到四五月份出兵为好。他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所组成的明军战力表达了不信任,希望能抽调川贵士兵两万,就能“独挡奴酋”。然而,辽东经略杨镐只答应让他调八千川兵,结果到出发前,刘綎麾下的川军也只有不到五千兵力。而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然而,当时明军的体制,武官只有列席议事资格,却没有军事决策权,只能被动执行文官的命令。结果,那几位总兵的意见与建议,全都被杨镐置之不理。
而明军原定二月二十一日出兵。之后由于十六日开始降大雪,只好推迟出兵日期。可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大臣,却认为等待下去是耗费钱粮,于是一再催杨镐进兵。结果,明军就在准备不充分、内部问题重重的情况下,贸然开赴人生地不熟的辽东作战。也就是说,明军这次出兵,中国传统兵家所重视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存在问题!
说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明廷之所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还选择分进合击战术并贸然进兵,其实主要源自于轻敌。明廷复制的是明宪宗时期“成化犁庭”的战略布局。但“世易时移”,此时明军所将要面对的则已经整合了建州女真力量、建立了政权,并且拥有极强军事指挥能力的后金开国之君、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而且,后金政权拥有六万人级别的战兵,军队规模甚至能达到十万人。所以当初进剿松散的女真部落时很有效果的战略布局,很明显已经不适用了。但明廷丝毫没有意识到面对敌人的变化。那些朝廷大员,无视了一线军事主官的合理建议,还以剿匪的心态,将八万多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推向了萨尔浒战场,去执行那个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分进合击”战术。而明军也在种种不利条件的作用下,将“分进合击”战术执行成了“分进独击”,结果给予了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对其各个击破的机会。
相对于由于进行外线作战而困难重重,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明军,努尔哈赤的后金军由于处于内线作战,占据地利,后勤与行军压力要小得多。比如杜松以两天半的时间从沈阳抵达萨尔浒,要在崎岖山路上行军140多明代里(80多公里),而且还有浑河与苏子河两条河流的阻隔,最后还要面对坚固险要的界藩城。而从赫图阿拉到萨尔浒,军事地图的平面路程只有大约66.7公里,即116明代里,并且地形一马平川、路途平坦。加之后金军多为骑兵和骑马步兵,机动能力要远高于明军。所以后金军可以以逸待劳的更好集中兵力,执行“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
天时方面,17世纪时,北半球正处于寒冷周期,即著名的小冰河时期。而辽东本就是严寒之地。考虑到此次出征的明军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方,自然不可能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战斗力也必然大打折扣。而后金军作为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渔猎民族,对于当时的严寒气候更具适应能力。
人和方面,努尔哈赤此时已经通过铁腕手段整合了后金势力。比如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因为保持亲明立场,结果被他幽禁折磨了两年多后,悲惨死去。(1609年三月到1611年八月十九日,也有说法是被努尔哈赤秘密处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和一些亲信也被处死。
同时,后金军军纪严苛,作战时设有督战队,不守纪律者一律处死,“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
另外,努尔哈赤在辽东经营多年,根深蒂固,特别善于使用间谍和内应。当时,努尔哈赤号称“奸谍满辽阳”。明人评价为,“奴酋最狡,善用奸细”;“奴酋狡黠异常”,“间细广布”;“其用计最诡,用财最广,最用最密”;“奴最工间谍,所在内应”(《三朝辽事实录》)连《明神宗实录》也得承认,“辽人举动兼辽兵、辽马、辽饷,奴皆习知”,“奴酋狡诈机警,内地一举一动无不周知”。后金军攻陷抚顺、沈阳和辽阳等地,都大量依靠内应和间谍。比如,朝鲜史书《谍海君日记》记载:“奴贼攻城非其所长,(辽阳)陷入城堡,皆用计行间云。”
具体到萨尔浒之战,大量后金间谍使得明军“师期先泄”,也让后金军“得预为备”。而具体到作战中,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对明军实行各个击破战术,靠的也是战场情报上的单向透明。而相比之下,明军在萨尔浒战场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从杜松和马林部覆灭之后,刘綎部队仍浑然不觉就可见一般。
由此可见,以杜松部为代表的明军,在正式的战斗展开前,已经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相对后金军都处于下风,在战略上已经处于相当被动和不利的态势。此战还没开打,明军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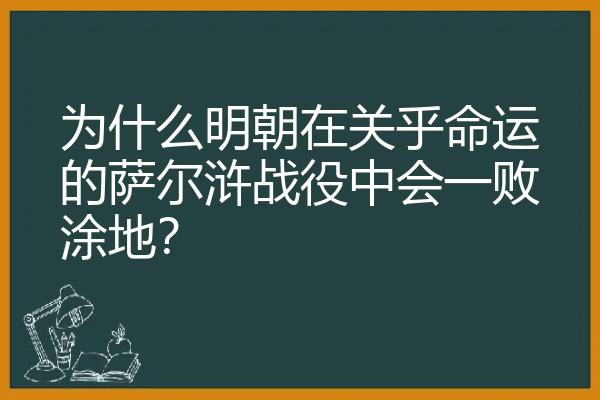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说起古代,好像就离不开战争,确实,时代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战争。也许这种说法有点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古代战争更多的是以粗鲁厮杀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如今,时代在进步,所以战争的方式也就随之转向了经济等多种无硝烟的方式。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是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恰巧生活在了和平的国家而已 。言归正传,明朝时期的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关乎明朝命运的一战,但是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归结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时的萨尔浒在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一带,1619年时,明朝万历皇帝派遣十多万征讨大军血战当年的满洲酋长努尔哈赤,但是就在如此局势下大明王朝却还是输给了努尔哈赤的六万大军,从此中国历史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导致一场战役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明王朝错误的战术,萨尔浒战役采用了“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战术。其实“分进合击”的战略技巧也并没有错,只是明朝将领错用在了这场战役中。没有分清楚当时的战况局势就盲目的将战术生拉硬套,没有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导致统帅掌控不了复杂的战争场面。兵分四路没有办法更好的指挥,因此导致作战乱了套。
再就是此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兵力,也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原因。如果当时明军依靠数量上的优势集中兵力稳扎稳打,说不定在此次战役中失败的就是努尔哈赤了。当然历史不能改写,后世也只能就事论事罢了。
其次,话又说回来,战略失误还不是统帅之过吗?当时的统帅是杨镐,万历帝任命杨镐为明军统帅去对抗后金的努尔哈赤,可以说这简直是个灾难性的决定。虽然杨镐在朝为官也有三十多年,但是他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也不是什么雄才大略之士,因此他拟定的“分进合击”最后以失败告终。(欢迎关注第一军情,若有其他问题,请在评论区留言。)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淮海战役国军怎么输的,国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就怎么输的。相差四百年的两场战争中,国军和明军的指挥居然如出一辙,也算是一大奇迹。
先来说淮海战役国军是怎么输的。
淮海战役中,国军进入战场的前后达到八十万人,而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合起来,也就六十万人。
但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解放军大获全胜,国军被歼灭五十五万人,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五个兵团被全歼,距离战场最近的国军李延年部观望成败,不敢来援。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就是因为国军指挥不统一,虽然人数很多,但是除了徐州的三十多万人是杜聿明统一指挥的,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都是被分别歼灭的。
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国军黄维和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救援都不算积极,杜聿明更是认为毫无机会取胜,所以只想把部队带走。
结果是黄百韬被全歼,积极救援的黄维兵团又被包围,杜聿明业无心解救黄维兵团。
这就是说,国军虽然看上去人多,但是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心不齐,没有协同作战,所以解放军粟裕能够先从容围歼黄百韬,然后掉过头来协助中野围歼黄维,再回过头来围歼杜聿明集团。
虽然粟裕手下的解放军数量比国军投入战场的数量要少,但是粟裕每次都能抓住机会,在局部地区形成兵力优势来围歼对手。最后是国军的三个部分被分而击之,一个都没能逃走。
萨尔浒之战同样如此。
虽然明军名义上数量达到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人,清军只有六万人。但是清军指挥统一,兵力集中,相互之间协同做得很好。
而明军得十二万人却分为四路进兵,除了杜松一路达到六万人之多在,其他三路都是二万人。
正是因为明军分散平均配置,所以在进军时步调不一致,进攻积极性也不一样,推进速度不一样。这样,清军就可以抓住明军各部推进速度的时间差,形成局部优势,加以歼灭。
也就是说,虽然宏观上清军处于明军得包围之中,但是明军的攻势并不统一,所以让清军有机会对四路分别发起攻击,逐个击破。而且,在单独面对每一路明军时,清军都是有兵力优势的。
粟裕围歼黄百韬兵团时,还需要中野配合进行打援,牵制黄维兵团,围歼黄维兵团时对杜聿明集团也是围而不歼,但是清军在分别与各路明军作战时,连阻援都不需要,只需要派出小股部队打探消息就行。
而作为明军主力的杜松所部的六万人,也在过河时被清军分割开来,分别消灭。所以,虽然参战总人数上,明军始终占据优势,但在局部战场上,明军始终处于劣势,不仅士气不如后金军队,连人数都不如对手。
从战术上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的指挥和表现只能算是浪战,缺乏有效的统一指挥和相互协同,主次也不分明,清军能够轻松自如的穿插到明军后背发起攻击,这种打法,明军输了一点都不奇怪,不输才奇怪。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事实上,明军出兵萨尔浒,开战以前,所有人都认为稳操胜券,努尔哈赤不过是一个东北酋长,女真部落都还没有统一。
只有200多个牛录,从满文老档看,努尔哈赤实际披甲只有2万人。大明此战,几乎所有精兵强将尽出,杜松,刘廷,李如柏等人,各个都是百战百胜,从打日本,讨伐蒙古,到征战西南地区,每一个人都是常胜将军的角色。
杜松和蒙古人作战超过100多次,百战百胜。属下将领赵梦麟,刘遇节,王宣,桂海龙,王浩等人各个都是狠角色。刘廷就不用说了,从15岁从军开始,就没失手过,部下的祖天定,徐九思,康应乾,姚国辅也都是真正的勇将。
李如柏打日本,败蒙古,麾下战将尤世功,张应昌,李克泰,戴先裕都是辽东明军的精英。马林部队更是明军辽东镇精锐“跳荡铁骑”。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最强火器军,最强骑兵部队,还有几乎所有名将都聚集在了萨尔浒大战的战场上。但是,结果却是惨败,正是这一战精锐几乎全灭,打掉了其他明军的士气,从此开始患上了后金恐惧症。
明军确实勇敢,被誉为勇冠三军的潘宗颜冲进敌营,血战疆场,被后金军的箭雨密集射击,最后“骨糜肢烂”。其他明军也是“奋呼冲击,胆气弥厉”,确实是精锐部队的表现。
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最后的蒙古大汗孛儿只斤·林丹巴图尔。在1632年,皇太极讨伐林丹汗,一直从蒙古追杀到青海,林丹汗被打的毫无抵抗能力,最后死去。
林丹汗正妻娜木钟,被皇太极纳为妃妾,此后还为皇太极生下一子一女。侧室芭德玛瑙,窦土门福晋,变成了皇太极的“衍庆宫淑妃。侧室俄尔哲图,嫁给皇太极的兄长阿巴泰,为其侧室。侧室苔丝娜,改嫁给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其侧室。
四十万蒙古之主,黄金家族出身的蒙古大汗都被后金碾压式打击,横穿整个蒙古逃到青海,还是被追杀而死。可以说明后金初期爆发时,确实在战斗力上,对蒙古,对明朝,都有着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可以说,萨尔浒之战是大明与女真的战略转折点, 至此以后,明朝转入战略防守,而女真进入战略主动。主动权的丧失彻底让大明整个辽东全面撤退。在公元1619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大明在杨镐为主帅带领下。兵分四路出征,(实际上是三路,朝鲜那一路就是打酱油的)但西路军首先遭努尔哈赤攻击,全军覆没,总兵杜松战死;随后北路军遭受攻击,全军覆没,总兵马林狼狈逃回;最后东路军被女真军偷袭,全军覆没,总兵刘铤战死;杨镐得到消息后匆忙撤兵,女真军趁势追击。整场萨尔浒打完,也就五天时间而已。明军损伤惨重。女真完胜。
这次战役是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此役明军12万人,努尔哈赤大约6万人。但必须指出的是,明军的战斗力和兵员素质并不弱。但明军主帅杨镐文官出身,不是武将领兵 。但兵分几路合围进击,就是以三路包抄作为诱敌之兵,以杜松领导的西路军三万人作为主力,进攻抚顺。也就是所谓的“犁庭扫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军事部署。但就实际而言。大明根本不了解女真,真正了解女真的李成梁已经去世。但努尔哈赤对明朝却是了解的,大明朝廷的腐败无能,军事架构臃肿。更是明白的很,女真不仅做好军事准备。还部署大量间谍、对整个战场动态可谓了如指掌,而且杨镐的作战意图被努尔哈赤发现了。否则他也不敢带着队伍在几天内连续高强度奔袭作战。从战略上看,明朝一开始就就输了,而在战术上,假如杜松这一路能够抵挡住努尔哈赤近几天,或者拖住女真。其他两路一定会围歼努尔哈赤。但杜松当天全线溃败。明军的三路围剿计划就此破产。这是努尔哈赤击破明军分进合击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胜利。可以说,在战术上,杜松应该承担萨尔浒之败的主要责任。马林部队应该立即全线撤退,却想继续进攻。但还是失败、东路刘挺所部被间谍欺骗,导致全线在萨尔浒溃败。指挥全军的杨镐得知四路大军两路溃败。急令其他两路撤军但为时已晚,刘挺所部已被后金歼灭,只有李如柏安全撤退,后来自杀。杨镐因此次兵败,在崇祯二年正法。
凭你几路来,我就一路去,各个击破是努尔哈赤战胜明军的军事战略原则。也就是集中了八旗兵优势兵力,采取突然的袭击的方式使得明朝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辽宁抚顺附近两方展开激烈交火,努尔哈赤亲自率领八旗兵45000人进攻明军。歼灭了杜松所部。主将杜松被杀死,西路军三万人全军覆没。随即努尔哈赤立即率军攻打北路军,全歼。数日后,努尔哈赤调兵进攻东路军,大败之。女真一路打三路。是出色的运动战。女真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而明军四路进兵,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按约定时间行动,彼此联络不畅。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好遇上了后金兵的“合进分击。明军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萨尔浒之战,充分展现了了努尔哈赤的大军事家风采和能力,也衬托出明军主帅的无能、努尔哈赤可以亲临一线作战,而杨镐连女真兵都没有见过。实在是贪生怕死。萨尔浒的失败,是一个腐朽落后的老大帝国,和一个强大冉冉升起的强大部族的决战,明军从开始就怯战,准备不足。而新兴的后金却是同仇敌忾,从努尔哈赤到女真兵敢于冒着枪炮往上冲,女真兵作战勇敢、到头来就是明军一次次败亡,后金兵节节胜利。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失败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是指挥失败,再就是明军的怕死,愚蠢、无能,怯懦所造成了明军的失败。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为什么明朝在关乎命运的萨尔浒战役中会一败涂地?
这个提问里“明军本来可以稳操胜券”一说非常的奇怪,明军就压根谈不上什么稳操胜券,不如说是明廷的大部分人以为这是必胜之仗,而最后结果是全军覆没。
事实上,早在萨尔浒战役开始前,明廷就有有识之士对这场战争战法和时机的选择上忧心忡忡,这其中也包括参战将领刘綎,但是这样的声音太微弱,直接被忽略了。
反对者之一,徐光启在战前就对杨镐的四路进兵策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他还断言尤其是杜松一路凶多吉少,恐怕要全军覆没,后来果真被其言中。
时方东顾,四路进兵,光启疏上,此法大谬,策杨经略镐必败。且曰:“杜将军当之,不复返矣。”反对者之二,熊廷弼早在杨镐担任辽抚的时候就反对轻率浪战,面对辽东残破的情况,提出对内应该“高城深池,息民养士”,在边防上应该修边筑堡,以守为战。他与杨镐在辽东防务上意见相左,最后被“坐勘家居”。
反对者之三,萨尔浒之战担任东路军主将刘綎,刘綎对此次仓促出兵深感焦虑,他在奏疏中指出了自己的担忧,提出了此次作战的军队训练不精,而自己的川军并未全部到齐,火器铠甲准备不全等弊端,顺便还说这场战役的指挥者,根本就没有成算,抓瞎指挥(这不是在骂杨镐嘛!),希望能再准备一些时间。附图。
除了以上三位外,反对者还有另外两路的主帅杜松、马林和兵部员外郎董承诏,尤其是董承诏指出辽事有六难“将多而难调、病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将多而难调”,希望能从长计议,最后结果是啥?就是“不报”。
所以在萨尔浒之战前,战局形势就对明军不利,何来“稳操胜券”之说。
萨尔浒之战最让人诟病就是兵分四路,四路军队相隔太远,而主帅杨镐却坐镇沈阳城遥控指挥,诸军难以联系和协调,给了女真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而杜松一路的兵力略多于其他三路,兵力平均分配,难以给敌军以重大打击。
关于这个兵力布置的原因有三:
一、参照了平播州杨应龙之役,将西南战场的成功经验搬到了东北,在平杨应龙的战役中,明军就是24万军队兵分8路,每路3万人,进行向心攻击,最后大获全胜。所以,这回不管不顾依样画葫芦再来一遍。
二、成化犁庭的成功经验深深的影响了明廷的高层,当年赵秉率领2万军队,兵分五路,摆平了建州女真。11万大军自然是绰绰有余,有一种天兵一到,努尔哈赤服诛的既视感。
成化间,李秉征建虏分五路,杨经略仿之为四路,叛建虏昔脆而今劲。三、之所以四路分兵,那是因为这回出征的明军体系不同,如果合为一路也是有可能导致大败的,宣、大调过来的杜松、还有东路军主帅刘綎以及辽东系的李如柏,不是赫赫有名的主帅,就是老资格,而主帅杨镐坐镇沈阳,又威望不足,不为众人所服气(刘綎都在奏折里骂他,见上文),如果合为一路,肯定大事不妙,这件事江西御史张铨就看的很清楚,提出杨镐这位主帅一定要严加约束,只可惜杨镐没那能耐。
李如柏、杜松、刘綎俱宿将,不相下,必天语严切,责成杨镐约束。所以,明廷这回兵分四路,选用分进合击之策,既有客观失误,又有无奈之举。
失误在于:第一、对以往的成功经验生搬硬套,不顾辽东战场的实际情况,要知道八旗军得战斗力比苗兵强不说,其行军作战靠马匹机动,其突击力和运动战能力比杨应龙军强的多。第二、虽然对努尔哈赤实力增长有所认识,但是认识程度有所不足。第三、此次出征的军队体系完全不一样,合兵弊端甚大,难以指挥。
所以,萨尔浒战役是战前准备不足,战役策划如同盲人摸瞎马,这样根本就是胜算极低,“胜券在握”那是没有的事。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