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高俅,在人们心目中的恶名,源于小说《水浒传》,将其描写刻画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臣,与蔡京、童贯等“北宋六贼”同列,实际上,高俅,并不在“北宋六贼”之列。
高俅,原为中国文学史“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苏东坡的“小史”,类似现今私人秘书的家童,聪明机警,略有文识,诗词歌赋皆通,善蹴鞠,既今日足球的前身,会使枪棒,是一个多才多艺,用今天的话说,“文艺青年”!
苏东坡外放地方官时,将其推荐给皇亲小王都太尉王诜,因而结识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深得赏识。
徽宗即位后,有意提拔,奈其无科举正途,这是提拔任用的首要条件,皇帝也奈若何;于是,发挥其善枪棒的特长,派其到北宋名将五元帅之一刘锜父亲刘仲武军中,以期获取军功予以提携,这是无科举正途的旁门佐道,“曲线救国”,后位至掌控禁军太尉高官。
小说《水浒传》中,将高俅列为奸臣,大笔墨渲染,但也没有什么实质劣迹。
其实,高俅不在“宋末六贼”之列,只是其善于奉迎徽宗,取得信任,非科举正途而升迁,使人不悦。估计,《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作为屡试不弟的书生,愤愤不平,而将其描写成奸臣,也有点泄私愤吧!
据史载,高俅为官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似蔡京专横跋扈,仅在任太尉时,军事训练搞些非实战的花架子,取宠徽宗而已!
而且,高俅为人,知恩图报,位居高官,手握重权后,对老主人苏东坡、刘仲武家多有关照帮助,提携刘仲武之子刘锜,成为北宋抗金主力五元帅之一。
高俅,在金人入侵,随徽宗南逃时,与“宋末六贼”之一童贯,发生矛盾,托病返回开封,真的因病而亡,也是善终的了!
仅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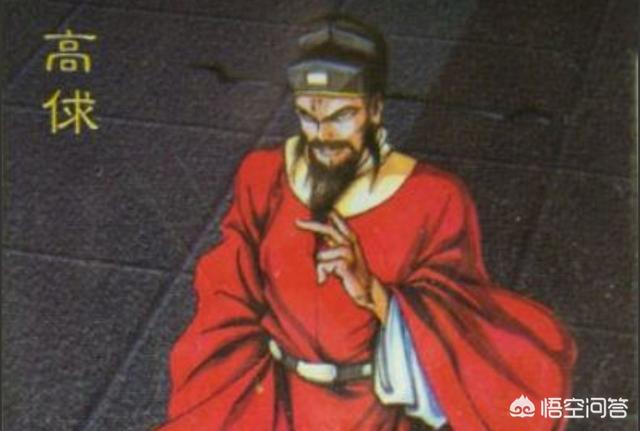
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在《水浒传》里,真正的小说开头,是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而在这一回,除了交待时代背景的文字之外,开篇就是写高俅:“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这里其实透露出很多信息,一者高俅好使枪弄棒,有好武艺;二者踢得一脚好球;三者擅长诗词歌赋。这一看,是个全才呀。虽然在高俅投靠的在东京开生药铺的董将士眼里,他“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但在那个一般人没有读书机会的年代,不但会武艺,还能写诗词,这就是个文武双全的人啦,这样的人,到哪都有用武之地。当然,学好,能德才兼备,学坏,遇到臭味相投的,也能够上天入地。
而高俅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玩,“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样样精通,这样的人,只要遇到爱玩的权贵,便能攀上高枝,青云直上。但董将士怕高俅是个灾星,带坏了子弟,推荐给学士苏东坡。苏东坡因嫌他是个“帮闲浮浪的人”,又将他推荐给驸马小王都太尉(王晋卿)当亲随,理由是:“他便喜欢这样的人。”
其实,不独小王都太尉喜欢这样的人,他的妻侄端王赵佶更喜欢这样的人。有一次,小王都太尉让高俅到端王府送东西,正好端王在玩球,高俅最擅长踢球,随便踢了两脚,端王喝彩之余,便将高俅留在了身边。后来,赵佶继位当了皇帝,是为宋徽宗,高俅还继续陪他玩球,因此一路升迁,官至太尉。
高俅的经历给了我们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在封建社会,只要有一定的独门玩乐功夫,就能找到接近权贵的机会;二是一个人只要能够接近权贵,又有吸引权贵的才能,凭借自己的独门绝技,无论陪玩、陪跳、陪唱、陪踢,让权贵高兴了,就能解决就业问题,不愁找不到工作;三是如果这个权贵是皇帝,那么无论你读没读小学、初中,无论你有没有文凭,都能够破格录用,并且设计一条升官路径,让你三五年就能当上大官,人家十年寒窗苦读,得个进士,然后到地方工作,五年一个岗位,最多也是个地方州官,京城郎官,但他踢几脚球,就能踢出个太尉来,当上副国级,可见行行都能出状元。
高俅这样轻松地当上了副国级高干,他手下得有多少状元、探花呀。所以,高俅的经历也证明,那些读书破万卷的人,无论你走得多远、升得多高,最后一般都要给不会读书或不读书的人打工。
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一议再议,说明书中的故事情节引的各领域大佬及普通民众的追棒追溯。书中既有官场现形迹的丑陋腐朽权臣奸臣等当道的现象。情节跌宕起伏,将奸臣权臣的丑陋嘴脸刻画的淋漓尽致,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蔡京,童贯,扬戬,高俅
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相信凡是读过水浒传的各位大佬友友们对高俅基本无好感哈,这家伙一路走来攀登人生高峰时,没做过甚有益百姓的好事,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从一个街头混混地痞流氓混入当朝的高官厚碌,干尽坏事,逼得禁军两任八十万教头妻离子散,天人共愤。
这厮擅长吹弹歌赋,踢蹴鞠技术无人能及,凭此技靠上端王成就了他人生的颠峰。也成了梁山英雄的最直接、最凶恶最持久的对立面,不守信用,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他身上演绎的淋漓尽致[酷拽]只因踢得一脚好球被昏君徽宗看好。害苦了千百万劳苦大众哈。
看名著,议名著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明镜,警示后人哈!惩奸除恶,严惩贪官污吏……。
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水浒传》中的高俅,不是历史真实中的高俅,而是以这样一个人物暗藏了朱元璋,以及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因而,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不是评价北宋的高俅,而是“评议前王并后帝”中的帝王。那么,《水浒传》中又是如何评议帝王的呢?咱们且从高俅的故事说起。
历史真实中的高俅大节不亏《宋史》中并无高俅传,高俅也不是所谓的“北宋四贼”。假如没有《水浒传》,没有《水浒传》续书《征四寇》,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历史人物了。《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发迹”,大致取材于《挥塵后录》,几乎与宋史无关,只是在“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故事中,借用了高俅做殿前太尉的时间节点,以隐藏“宋金海上之盟”。
即便是高俅的故事取材于《挥塵后录》,但也是掐头去尾,按照《水浒传》的故事主题重塑了一个新的文学形象。《挥塵后录》中说,高俅原本是苏轼府中管文书的小吏员,大概类似于《水浒传》中的“押司”。因苏轼即将遭到谪贬,担心影响高俅的前程,便把他推荐给了宋英宗的驸马,也就是宋徽宗的姑丈王冼王晋卿。
有一天早朝,端王忘了带篦子,便借姑丈的篦子一用。王晋卿见端王喜欢这件小用具,便复制了一件,派高俅送到了端王府。就这样,高俅来到了后来的宋徽宗身边。
相关野史中说,高俅在端王(徽宗)身边玩了很多花样,深得宠信。但是,高俅做到“使相”,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据《宋史·徽宗本纪》说,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如此,距离端王登基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而做到《水浒传》中所说的殿帅府太尉时,也是在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也是经历了十七年时间才做上这样的大官,并不是施耐庵说的:“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因而,《水浒传》中的高俅并不是历史上的高俅。历史上的高俅虽然也有随波逐流,在宋徽宗追求享乐时迎合了“圣心”,但史家评价高俅“大节不亏”,尤其是在童贯企图分裂朝廷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高俅很是知恩图报,对待苏轼的家人非常好,还报答曾经的长官刘仲武,举荐他的儿子刘锜,为南宋抗金预备了一员大将。
施耐庵写《水浒传》是非常尊重历史的,故事中所隐藏的真实历史,恐怕有很多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么,在“高俅”这个人物身上,施耐庵为何又虚构了这么多假历史呢?其原因就隐藏在“高毬”这个名字上。
王燕则诸侯毛,高俅原本叫高毬《水浒传》中说 ,高俅原本是汴梁宣武军的浮浪破落户,家中排行第二,就叫做高二。因“踢得好脚毛球”,汴梁人便叫他“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毬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段描写说明,高二是家中的小名,大名就是别人叫出来的“高毬”。
施耐庵为何要给高俅虚构这样一个大名呢?仅仅只是因为要为后文因踢毬发迹的故事伏笔吗?
高毬这个名字一直要用到进端王府发迹之后,这之前的故事便都是“高毬”在书中活动。高毬因为教唆“生铁员外”的儿子在瓦肆使风流钱,便把他的父亲(高大或者高二)状告到了开封府。开封府将高俅脊杖二十,跌配出汴京城。
这其中的“生铁员外”,说的是“升天员外”,铁,在《水浒传》中是“天”的代名词,比如栾廷玉的铁棒,其实就是紫微宫中的“天棓”星。“生铁员外”的文本意思,是说这个员外一毛不拔。所以,儿子花了几个钱,便闹到了高家,高老头无奈才状告了儿子。
施耐庵为何不惜笔墨反复写一个毛字呢?其原因是《周礼·秋官·司仪》中有这样一句话:“王燕而诸侯毛”。这句话的本义大致是说,周王到了燕国,诸侯以毛发状况朝见周王,也就是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依次排座次。《水浒传》中写的不是周朝礼仪,而是借用了“王燕”颠倒作“燕王”,燕王就是明朝的九大塞王之一的朱棣。《水浒传》中,这九大塞王都有暗中出场。
为何说燕王一定就是明朝的燕王呢?《水浒传》写的是因“孙立”,也就是朱元璋立孙子朱允炆为皇帝引发的靖难之役。其次,高俅的“高”出自朱元璋的谥号: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这个谥号,也是“太祖武德皇帝”的出处之一。其中的“高”,就是《水浒传》所有的“高”,包括高俅、高衙内、高廉、刘高。
书中说,高俅是汴梁宣武军人,这是一处故意错写,应当是“宣武军汴梁”人。这处错写的寓意在于点出了高俅真正的籍贯,他就是“濠之钟离东乡人”,这是“高皇帝”朱元璋的祖贯。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本号在专栏中有详细解读,此处便按下不表,只说这样的一个寓意以“评价”高俅。
高俅被跌配出汴梁城,然后去了临淮州,在临淮州呆了三年,又回到了汴梁。这段故事,其实暗写的是燕王之藩。
临淮州在哪里,柳大郎、董将士又是谁高俅不是刺配,而是跌配,“跌配”这个词专属《水浒传》,是施耐庵发明的。这个“跌”字,照应了“洪太尉误走妖魔”中,伏魔大殿大门上的描写:“重重迭迭使着朱印”。这段故事中,上清宫住持真人说,这些“重重迭迭使着朱印”的封皮,是八九代张天师所贴。于是,便暗藏了九重、重八,使着朱印,那就是朱重八。
龙虎山伏魔之殿中有朱重八,高俅一路跌配中有没有这样的符码呢?当然有,柳大郎、董将士都是朱重八,怎么讲?
史上没有临淮州只有临淮县,简单来讲,临淮县大致可以代表凤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改中立县为临淮县,属凤阳府。中立县,在元代时曾经叫做钟离县,所以,朱元璋是“濠之钟离东乡人”。这个隐喻,又在“三打朱家庄”时出现,就是那位免除了祝家庄洗劫厄运的钟离老人。燕王夺位成功后,确实没有在南京屠城。
洪武三年,朱元璋除了改钟离县为临淮县,还办了一件事,那就是封皇子为藩王,老四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九年(1376年),为了历练朱棣(朱榑、朱桢)等人,朱元璋让他们回到老家凤阳体验民间疾苦,学习做个好藩王。经历三年多历练,洪武十三年,燕王之藩北平。
简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再来看看《水浒传》是如何描述高俅这段经历的:
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 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我在专栏中,解读了“赌”字,又解读了“柳”字。此处,单讲“柳”字的寓意。柳,是《水浒传》中很常见的一种树,也经常写成“杨柳”。其实,施耐庵是借“柳”写的是柳宿。《水浒传》中,但凡隐姓瞒名者,都喜欢冒充姓张的,这是说的张宿。柳宿、张宿,同属南方朱雀七宿,南方朱雀隐喻的就是在南京立国的明朝。同时,也隐藏了靖难之役的双方燕王和朱允炆——其中的细节不再详述。
如此,柳大郎,岂不就是第一代皇帝“高皇帝”朱元璋?皇帝之位代代相传,明朝也绝不例外,柳世权就是这个意思。
三年之后,高俅遇到皇帝大赦,便要会汴梁,柳大郎便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东京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朱元璋所封的藩王中,还真出了一位“开生药铺”的藩王,他就是第五子,朱棣同母弟周王周橚。朱橚的封地在汴梁,因为犯事,被朱元璋惩罚,他的儿子朱有炖代理藩事,曾拟汴梁八景,其中便有“金梁晓月”。所以,柳大郎便把高俅推荐给了董将士。故而,这一笔写的就是明朝燕、周、楚、齐四大藩王之藩的历史。
“董”,草字头下是“重”,加上朱橚家的事,也就与“跌”字隐藏了重八,这也说的是朱家的事。“董”在书中还会出现,几处细节总汇到一起,这个字隐藏的也是“朱重八”。
既然“高俅”隐藏的是皇帝,那么,《水浒传》中又是如何评价皇帝的呢?
施耐庵如何评价高俅《水浒传》的开篇词总共两首,一首是《临江仙》词,另一首是《南吕宫·玉娇枝》曲。这两首词曲中,核心主题讲的就是一个,以“霎时新月下长川”为基点,“评议前王并后帝”。新月,就是刚刚建立的明朝,“前王并后帝”就是书中涉及到的“高皇帝”,李世民,以及五代两宋的皇帝,加上朱元璋子孙三代皇帝。
朱元璋的谥号中,包含了“高皇帝”,施耐庵以“芒砀山公孙胜降魔”这回书,讥讽大明太祖,你老人家哪里能与斩白蛇起义的高皇帝相提并论?同时,又以此高皇帝暗喻彼高皇帝,这两个隔代高皇帝都是因为分封皇子藩王,导致了削藩和藩镇之乱——《水浒传》隐写的就是建文帝削藩,燕王造反夺位。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揭露“皇权天命”的大谎言。朱元璋以“火德运”为大明国运,正是效仿了汉高祖之“炎刘”,以及宋太祖的“火德王”。这团火,最终将熄灭于“水浒”、“水泊”。
“开篇引首”中,施耐庵写了这样一段存在严重历史常识错误的话: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传位与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太子即位,这朝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
这段话明写的是北宋皇位传承,暗写了明朝的“孙立”。北宋建立于猴年,明朝也建立于猴年,其中漏写宋真宗,就是说的“孙立”。当然,漏写宋真宗还暗藏了北宋的“金匮之盟”、“烛影斧声”,与后来的靖难之役一样,都是弑君篡位的勾当。
因此,施耐庵在“开篇引首”的结尾处写道:“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梁山好汉是要造反的,造北宋的反,造“宋国”的反。“宋国”,其实说的是“明承宋祚”,朱元璋原本就是宋徽宗八世孙韩山童的部将,又涉嫌谋杀了韩宋皇帝小明王韩林儿,其国号用的是“明”。
第一回书以王维《大明宫早朝和贾舍人之作》,暗写了大明皇宫。又让宋仁宗驾坐大明宫紫宸殿,引发“误走妖魔”故事。大明宫是唐朝的宫殿,紫宸殿则是大明宫中的宫殿。这一笔,暗写的是明朝的靖难之役实际上就是唐朝的玄武门之变,这个隐喻在书中多次呈现,此处不多讲。
简单举这些文本便足以证明,《水浒传》中的妖魔都是皇帝放出来的,而所有的妖魔几乎人人都贴着皇帝的符码,他们与高俅一样,象征了弑君篡位的皇帝。因而,《水浒传》隐藏的深刻主题就是:世上哪有神仙皇帝,他们都是为了争夺皇位而谋朝篡位,破坏天下太平的妖魔。
《水浒传》就是一部反皇帝、反封建帝制的超现实主义伟大巨著,皇帝都是妖魔——这就是《水浒传》对高俅的评价。
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最著名的贼臣是高俅
《水浒》一书中被梁山英雄称为“赃官污吏”或“贼臣”的人,我们可以将他们列一个谱系出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高俅,但首先出场的却不是他,而是“误走妖魔”的洪太尉。洪太尉只在第一回书中出现,后来就完全没有他的故事,也不见他的名字了,这样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他的作用只是充当官方腐朽无能可笑的普遍性的象征,他只是一个打开场锣鼓、揭开序幕、预先在你眼前放许多角色到后台去的人,至于这些角色以后将如何登场、上演什么可怕的好戏,他是不管了,他只管他在皇帝面前说了谎、领了奖、回去享受他的荣华富贵。天下即使没有高俅这些“强硬派”,洪信这样的人也会弄得天下崩溃大乱的,但在洪信们当中,却一定会有蔡京高俅这种“能人”从内部产生出来或从外部“抬举”进来。
《水浒》赃官污吏系列中最高的官,还不是高俅,而是蔡京,号称蔡太师,但蔡太师隐蔽较深一些,高俅是突出在最前面、最显赫的“贼臣”。
他的简史是《水浒》读者众所周知的: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最是踢得一脚好气球,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诗书词赋,什么都会一点,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因为帮闲着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吃喝玩乐,被王员外告了一状,官府里打了他二十大板,逐出京城,“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后来到外地投奔在一个开赌坊的柳大郎家住了三年,再后来回到东京,一个偶然的机会,加上偶然飞来一球,被他“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了一脚,结识了端王,这位端爷号称“九大王”,“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真是一拍即合,赏识了高俅,后来端王做了皇帝,竟将高俅“抬举”到了“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上,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如王进、林冲这样有本领的人,性命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的就不用说了。
在《水浒》里,“高太尉”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击报复王进。当时,“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名之后,发觉王进未到,一查,己经请了病假,但“高殿帅大怒”,喝道,“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快与我拿来”,于是王进“只得捱着病来”,说明情况后,高俅也不依,开口就連王进的父亲也骂了下来,喝道,“你爷是街市使花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好家伙,真是劈头盖脑,不容分辩。接着又喝令“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将官劝说“今日太尉上任,好日头”,这才免打。
王进这时才“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心中说,“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回到家中闷闷不己,“母子二人抱头而哭”,他们是被“逼”得难以照样生存下去了,决定“走为上着”,于是逃出东京,“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
这一“高俅进,王进退”的情节,既是一个具体的情节,刻划了高俅这个人物形象,又是一个有象征意味的情节放在全书的第二回,实际是全书故事的一个真正开头,预示着从此以后是高俅这样的人得势,而王进这样的人連生存安身也难。
王进之“王”,在汉文里正是“王道”之王,“王道”的内容,就是书中前面说到的“仁、义、礼、智、信、行、忠、良”,高俅对这些是“不会”的。如果他是个一般的人,“不会”也罢,尽管踢你的气球去,吹弹歌舞去,帮闲别人花钱去,但他既然做了“殿帅府太尉”,他一手遮天的地方,因为他的“不会”,自然也就“王道”不存了。所以,“王进”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本该“进”的“王道”处在弱势、并且只有远远“退”去的一个总体象征,而放在全书故事的开头。王进的“退”的命运,代表了全书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命运,他是一个忠良,他有着好的德行和行为,但他只有被高俅这种势力逼得落魄而逃。王进和洪太尉一样,以后在书中再没有出现,他们作为全书开篇象征符号的作用,也就更为显著和有意了,暗示着、说明着和总括着全书的精神意蕴。
高俅这样的人,成了权势熏天的高太尉之后,做的坏事一定很多,而在《水浒》书中所做的第二件坏事就是陷害林冲。在所有“逼上梁山”的故事里,林冲的遭遇是个典型。他做着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岳夫是张教头,妻子美貌贤惠,家中用着一个使女,差不多是过着中等阶级的小康日子。林冲是在鲁智深视角里出场的,连用两个“只见一个官人”,然后进一步描写了林冲的衣着,头上戴的、脑后挂的、身上着的、腰里系的、脚上穿的,都值得一写,然后是“手中执一把折迭纸西川扇子”,可算悠闲自在。岂料大祸就要降临!大祸并不是自己做错了事,而是老婆竟被高俅的儿子撞见看中了。高俅为了满足儿子的荒唐要求,也就竟然与手下人设计使林冲蒙受不可饶恕的罪名,叫做“手执利刃,故入白虎节堂”,是该死的罪。
后来虽得人斡旋,也毕竟脸上刺了字,发配充军,远远打发,以便谋取他的妻子。林冲是一条好汉,见有人调戏他的妻子,是要举拳就打的,但一见是高衙内,也就“先自手软了”。高俅指使要在发配充军途中把林冲结果,不料被鲁智深救了。于是仍不死心,又派爪牙跟踪到充军所在地,贿赂管营差拨这些官吏,用了一条毒计,让林冲不被烧死也要因失火烧了大军草料场而得个死罪。林冲就是这样被逼得没有活路,由一个善良无辜平平静静过着好日子凭一身本领做着国家武官的人,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里生,拿起武器,杀了来害他的人,走上梁山,落草为“寇”,后来他的妻子在东京也自尽了,他活生生被高俅弄得有国难投、家破人亡。
高俅作为书中最为突出在前面的第一大坏官,他也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强硬派”。林冲的故事之后,笔墨也就从高俅身上移开,而去写林冲以外其它英雄的故事了,不可能老是盯着高俅来写,若写的是“高俅传”,倒是可以的。但因为高俅有着“殿帅府太尉”这样高的军权地位,又因为他和林冲的这段故事,而林冲上了梁山,所以高俅的身影实际上就在全书存在着。
在全书的中段,作者写了梁山好汉跟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知府高廉的战争,消灭了高廉。高太尉“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奏知皇帝,说“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恶,打劫城池,抢掳仓廒,聚集凶徒恶党,现在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廒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除,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句句皆为皇上的国家天下,没有一句说着他的兄弟,更没有一句说着他自己是如何逼得林冲这样的国家栋梁走投无路的,这一笔写出了高俅这类人正是封建国家败亡的根本,所以林冲在阵上骂的是“那欺君贼臣高俅”。
而梁山好汉之所以去攻打高唐州,皆因为高廉的妻舅殷天锡看上了柴进叔父柴皇城的花园住宅,要来强占,而柴进带着李逵去看望叔父时,殷天锡正好带着一伙人来行凶,李逵气不过,打死了殷天锡,柴进被高廉捉进了死牢,而李逵逃回梁山报信,梁山好汉是同生死共命运的,自然就要来攻打高唐州了。高廉会妖术,梁山人马先是打了败仗,后来请得公孙胜下山,才取得了胜利。
不言而喻的是,高廉能做到知府,是因为朝中有高俅,而殷天锡敢来强占柴皇城的花园住宅,是因为有上有高廉和高俅。作者决不是为了写公孙胜与高廉斗法,才写这个故事的,显然是为了写出社会现实的某种黑暗,即高俅既做了大官,他的叔伯兄弟也就能做到一州的知府,而叔伯兄弟的妻舅也就敢于来强占人家的花园住宅,说起来柴进的叔父还不是个等闲人物,是有宋朝的“誓书铁券”,受着国家特别优待的,高廉殷天锡却全不把这放在眼里,他们平时是如何骑在百姓头上,就不用说了。
梁山英雄排座次说明着梁山好汉已成气候,所以在朝廷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主张“早为剿捕”的,有主张“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的,结果天子决定招安,派陈太尉前往。这时高俅来到陈太尉家中,说“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内,必然阻住。此贼屡辱朝廷,罪恶滔天”,如果他们“怠慢圣旨”,你就“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整点大军,亲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就是说,相对于“主招派”,他是个强硬的“主剿派”。梁山好汉内部也有两派,一派是宋江为首的“望招安派”,一派是李逵为首的“反到底派”,结果此次招安在梁山“反到底派”努力下,未能成功,于是朝廷的“主剿派”占了上风,由枢密官童贯出征梁山。
童贯被梁山好汉打败之后,逃回京城,“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议”,高俅说,“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我和你去告禀太师,再作个道理”,结果,他们果然瞒了皇帝,由高俅亲自领着十路军马前来攻打梁山。高俅战不过梁山好汉,连败三仗,并且被活捉上了梁山。宋江以礼相待,希望他能到皇帝面前去说好话,招安梁山人马,“救拔深陷之人”,高俅当面答应了,回到京城之后,却将随同去的肖让、乐和软禁,自己推病在家不上朝,并没有为梁山请求招安。后来是梁山派人赴京设法把真相让皇帝知道,这才实现了招安。招安以后,梁山好汉为国家屡立功劳,到最后还是死在高俅手中,最后七零八落,死的死,亡的亡,一场英雄事业也就到了头,而高俅依然做着殿帅府太尉,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从《水浒》的结局可知,作者的现实主义是清醒而彻底的。
如何评价《水浒传》里的高俅?
高俅在《水浒传》里是个恶贯满盈的人物,干尽了坏事,虽然身为高官,却经常官报私仇,可见没有做高官的肚量。
高俅是个入错行的人,这不怪高俅,因为他伺候的主子徽宗赵佶,是和猪八戒一样投错了胎的人物,赵佶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应该说得上是才高八斗吧,但阴差阳错的把老赵投胎到帝王家,如果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赵佶哪能有昏君的骂名,估计评价是满满的艺术家之类的赞美之词了。
高俅能当上太尉,不是因为他军事能力出众,而是源自于他的一项绝技,踢得一脚好气毬,他使出一个“鸳鸯拐”,把毬稳稳当当的送到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面前,赵佶看呆了,这小子是个大毬星啊,必须让他上场试试,结果一番试验,高俅使出浑身本领,毬就像沾在了身上,高俅身法也十分漂亮,就算球王贝利穿越到宋朝,见到高俅的球技,也要甘拜下风。惹的端王和众人同声喝彩,赵佶对人才还是很重视的,马上把高俅收留到身边。
后来端王成了皇帝,就想提拔高俅当殿帅府太尉一职,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徽宗赵佶早想好了回应的话,我会画画的能当皇帝治理国家,难道会踢毬的就不能当太尉管理军队吗?这一番理论,大臣们都哑口无言了。
高俅从此当上了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烧哪呢,他上任第一天就发现了仇人王进的名字,因为高俅在街头当混混的时候,遭到过王进的毒打,高俅也算是快意恩仇的人,马上要把王进打一顿,王进机灵,找个机会偷偷的跑路了,虽然高俅这口气没出来,但也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小人得志。
高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陷害林冲,为了帮助义子高衙内,把林冲的老婆抢到手,充分发挥了一下聪明才智,设了一个大局,骗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成了罪犯,任由高俅摆布,最终被逼无奈上了梁山,高俅的智商还是很高的。
青面兽杨志为了恢复制使的职务,几乎是散尽家财,把有关的官员贿赂了一个遍,结果到高俅这卡住了,不是高俅为官清廉,不接受贿赂,事情应该怨杨志考虑不周。
杨志初到汴梁,对自己带的大量钱财非常自信,他想:我有这么多钱财,等不到用完就能把事办成了,等恢复了制使的工作,月月有工资,也用不着苦着自己,所以吃喝住都挑高档的,这样钱就花得多了。
他没想到事情没那么好办,时间一天天过去,等到高俅这一关,杨志钱用尽了,杨志当时的想法是:高太尉是国家高级领导,怎么能收我这点钱,所以空着手来见高太尉,高俅看着杨志,心说:你傻啊,来找我办事连盒点心都不拿,是不是没拿我当领导,一怒之下把杨志轰了出去,杨志这个懊悔,还不如把贿赂别的官员的钱给高俅留着呢,可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杨志就这样走头无路了,连回家的钱都没有,只好集市上卖宝刀了。
高俅当上了太尉,把权利发挥到极致,但他一点没有为国家大事考虑过,从高俅的表现来看,他的品质实在不适合做大官,做军事统帅更不行了,指挥大军剿灭梁山,三次被打得大败,自己也成了俘虏,说明高俅的军事能力真不行,所以这条道路实在不适合他,不过这是宋徽宗的错误,当初把高俅放在足球队,也能发挥他的长处,俗话说:用人要用他的长处,不是高俅无能,而是宋徽宗错用了高俅。
高俅除了踢球的绝技,早年就是靠给人帮闲混饭吃,这是个祸害底层老百姓的职业,如果一辈子以这为生,不知道祸害多少老百姓,高俅在这个职业上发挥最出色的一次,就是帮一个富户王员外的儿子使钱,把王员外的儿子教坏了,还把王员外弄了个倾家荡产,所以尽管高俅在这个职业上业务熟练,还是别干这个为好,高俅还有一项能力,应该是他一生最好的选择。
高俅的书法还是很不错的,想当初高俅发配临淮州的时候,认识了开赌场的柳大郎,柳大郎正需要高俅这样的人才,就把高俅留在了身边。等宋哲宗大赦天下的时候,高俅又想回东京汴梁闯天下,于是柳大郎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亲戚董生,董生知道高俅这人留在家里是个祸害,就顺水推舟,把高俅推荐到苏东坡的门下,进了学士府。
高俅能进学士府,是因为他书法不错,在那里可以做抄写的工作,苏东坡后来被贬,临走时把高俅介绍到驸马府,到驸马王都尉手下当了差。其实在高官府里当奴才,才是最适合高俅的职业。
第一:从个人角度考虑,高俅可以混得比较体面,也不用担心没有饭吃。
第二:高俅是见风使舵的人,很会讨主子欢心,又会踢球,又有一手好字,大宋朝能玩得东西,高俅都玩的出类拔萃,可以让主人玩得尽兴。
第三:在府里当奴才,高俅是不会像当太尉那样狐假虎威的,他知道夹起尾巴做人,这样就不会祸害那么多人了,更不会祸害国家了。
总结:高俅成为《水浒传》最大的反面人物,主要是宋徽宗让他干了不适合的职业,高俅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宋徽宗确不是知人善任的皇帝。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