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和一场令人艳羡的浪漫之爱竟然以分离的结局落幕,这令不少善良的读者难以接受。张生对崔莺莺的”始乱终弃“,也催生出后世之人对这个故事的集体改编,不惜打破现实还莺莺一个公道。比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清代的《何必西厢》,使得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在后世人中以”大团圆“的结局,成为才子佳人爱情戏的经典。
本答案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述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原因:
第一,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张生的“托词”是否可以作为分手的理由。
第二,从小说的创作角度看,有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作者元稹的忏悔录。
第三,从小说创作的时代来看,“始乱终弃”揭示了男女性别地位的巨大差异。
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张生最后“始乱终弃”的“托词”是否可以作为分手的理由《莺莺传》一开始赋予了张生一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写他性情温和、风容秀美、信守礼法。他年逾二十三,但还从来没有真正碰过女色。如此洁身自好,如此坚守德性,非一般人可及。但他并非是“柳下蕙”式的坐怀不乱之士,对于女色,他有着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他自己说,“大凡出众的美女,我未尝不留心,凭这可以知道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
张生自己认为不是大众眼中的“情圣”,他只是在等待一段缘份。果然,没过多久,天缘合作的时机就来了。在一次答谢的饭局上,他见到了崔莺莺,张生顿时被莺莺的美艳给倾倒了。那么崔莺莺是什么反应呢?
张生不断地找话题引导崔莺莺,但她并不打理,更不接话。直到宴会结束,莺莺仍然没有动半点声色。可见,张生与莺莺的初次见面,并非“两情相悦”,张生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回到家后,张生已陷入情网,红娘的出现成了他的救命恩人。红娘提议要他去正式登门提亲,结果张生说,这事他做不来,再说通过媒人提亲,又要“纳采”又要“问名”,手续烦琐,少说也得四个月,到那时,他恐怕由活鱼变成干鱼了。
张生看上去很善于找“托词”,既是认定的人,又不舍费心费力,可见,他并没有从封建传统的角度去珍视这段缘分,这也为崔张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隐患。
红娘这个中间人以诗文为崔张二人搭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果然张生以情诗打动了崔莺莺,二人在西厢暗渡陈仓。但是好景不长,张生要上京赶考了,二人就此别过,但并没有断绝来往,仍旧靠鸿雁传书维持感情。
张生的京考并不顺利,但是他决定滞留长安,这个决定几乎可以说再次为崔张二人的爱情敲响了丧钟。转眼一年过去,张生果然被长安留住了,他写信叫崔莺莺看开些,崔莺莺深知他已经不会再回来了,但仍旧回了一封情谊缠绵的绝笔信,此后二人各有归宿。
崔莺莺在与张生的交往中,一开始她是拒绝的。他们初次见面至二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但是自从红娘为张生想出这个写情诗的办法,崔莺莺对张生可以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以身相许,情谊绵绵,甚至到最后用了卑微的口气去乞求张生,表达了对这份感情的珍视。
张生则是刚好相反,一开始日思夜想,想尽办法讨莺莺的欢心,二人同眠共枕后,两情相悦,相互得到了慰藉。张生并不急于提亲,而是忙于京考,这说明在他的心中,男人的事业是第一位的,男欢女爱并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也的确没有给崔莺莺任何承诺。
崔张二人的爱情如果发生在现代,那是见怪不怪,但是崔莺莺是生活在千年以外的女子,也算得上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她不是不懂贞洁观念。从他的情信中,可以看出,她委身于张生是奔着结婚去的,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张生放鸽子,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接受现实。
相比张生,她的情感更加热烈,只是苦于无法倾心相诉。二人交往的过程,张生以进为退,崔莺莺则是以退为进,至最后深陷情感漩涡的其实是崔莺莺。
张生选择始乱终弃,他为自己找了一套说辞。如下: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对于张生的这段托词,我们可以引申出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就是鲁迅先生称之为“遂堕恶趣”,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金榜未题名的张生选择了“逃离”,他的主观动机是“忍情”,而客观上造成对莺莺的“抛弃”。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写道:“情最难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既然人的热恋温度不可能保持恒久,那么到了“意尽情疏”之时,要维系婚姻爱情持久,就只能靠道德责任来为情感保驾护航。从这个观点来看,鲁迅先生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批评并不过分。张生爱慕崔莺莺时尽情追求,自己提出分手了,最后还要给崔莺莺冠上“红颜祸水”的罪名,实属过分。
第二种看法,张生与莺莺的爱情令人扼腕叹息,但他们二人也算得上是“好聚好散”,避免了“爱之深,恨之切”。相爱的两个人能长相厮守固然是一种幸运,但并不是每一对相爱的人都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当两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包括张生所“托词”的原因在内,不能在一起的时候,双方为了这份爱,付出过的真情,相互祝福对方,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崔莺莺对张生之爱的宽宏大量,正体现出了她对情感的宽容气量,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古代的女性是很难得的智慧。
第三种看法,张生的“始乱终弃”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因素。著名学者陈寅恪指出:
“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其意是说,唐朝继承了南北朝士大夫的遗风,通常以二件事来品评个人的人品。一件是婚事,一件是官事。但凡要结婚就要娶名家之女,既要做官一定要经高官引荐。否则就会被别人看不起。可见,张生的“抛弃”并没有违背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对于寒门学子张生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求取功名,娶五姓女”,男儿志在四方、胸怀天下,他的选择也有苦衷。
从小说的创作角度看,有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作者元稹的忏悔录《莺莺传》里的主角张生是何许人也,自宋代以来,人们产生的大致思路,比较认同“自叙传”一说,也就是说,小说中“始乱终弃”的张生就是用情不专的元稹本人。
这种说法到了二十世纪,也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认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陈寅恪也在《元白诗笺证稿》时说:“《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
那么自宋代以来,人们何以认为发生在张生身上“始乱终弃”,实际上是作者元稹托名张生的现身说法呢?
我们要简要了解下元稹本人的情感历程。元稹秉性风流浪漫,富有“女人缘”。24岁时,当他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秘书省校书郎时,就得到了太子少保韦夏卿小女儿韦丛的垂青,并结为夫妻。他虽然娶了大家闺秀,但也没沾上老岳父的光,因为娶妻之后没多久岳父就去世了。因此,他宦官生涯中的岳父路线走得并不顺畅。
但是,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韦丛贤惠元稹体贴,二人相继哺育了五个子女,不幸的是,二人的幸福生活只延续了七年,便以韦丛离世而告终,所生子女也相继夭折。此时,元稹的仕途也不顺畅,因直言抨击宦官而被贬到江陵。
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比如流传至今的《离思》便是其中一首:
曾经沧海难为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一千古绝唱,用“巫山”“沧海”作衬托,表明了妻子韦丛在元稹心中无可替代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一首《遣悲怀》: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赏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相忆何深,相思何切!从这些诗词,我们看到元稹还算得上是一个“一往情深”的人。《遣悲怀》这首诗作于妻子韦丛去世的第三年,就在这年,元稹在江陵府上纳了妾,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元稹是一个“薄幸”之人,但是也不能排除他不是一个“薄幸”之人。
在韦丛活着的时候,他就出轨了。他曾和女诗人薛涛有过一段缠绵。据考证,这段外遇发生在元稹31岁之时。他在去蜀中出差的途中时遇42岁的薛涛,女诗人特别喜欢元稹的诗句,元稹离开蜀中,两人还表达了勿相忘的意愿。
这样看来,亡妻三年便纳妾是不是有点“薄幸”的味道。不料纳妾三年后小妾也离世了,人至中年的元稹经历了两度丧妻,之后离开江陵,出任通州司马,得到名相权德舆的关照,并娶了家娶了涪州刺史裴郧的女儿裴淑一。
后来,身为越州刺史的元稹又遇到了江南歌手刘采春,他被刘的美貌与歌喉所折服,不惜以给刘采春丈夫一笔钱为代价,将刘采春纳为小妾,这样的情谊也未能熬过“七年之痒”。他又冷落了刘采春,至使刘采春郁郁寡欢,以跳河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元稹的情感之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情而又不专一,多情而又不免薄幸。同时,他的政治品格也是游移不定。在仕途屡遭打击之后,他变得圆滑世故,转而与宦官妥协,逢迎宦官,在宦官崔潭峻的帮助下,他从祠部郎中一直做到宰相。从早期揭批宦官到后来与宦官同流合污,反倒真的为世人所不齿。
身为才子,元稹既解得风情,又懂得浪漫,在政治上品格又为人不齿,人们将《莺莺传》里的张生与元稹视为同一人,也就有了现实依据。再加上元稹写过一首《嘉陵驿》,41岁时还写过一首《春晓》,人们通过他的诗作,发现了元稹的这段恋爱史,发现了元稹对旧情的怀念与忏悔。并将这段恋爱史与他的作品《莺莺传》联系了起来,将元稹钉上了道德的耻辱柱,甚至连他的悼亡诗也饱受质疑。
陈寅恪也认为,元稹出卖气节,换取高官来做,尚可原谅;可恨的是,他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作为向上攀附的阶梯,实在可恶。
从客观的角度看,《莺莺传》毕竟只是一篇传奇小说,作者难免会将个人的生活经验融入其中,但也绝对不能把它与作者的人生划上等号,“以文证史”阐释的结论太过生硬。
从小说创作的时代来看,“始乱终弃”揭示了男女性别地位的巨大差异用现代的眼光看,崔张二人的故事毕竟发生在男权社会,男性公民们掌握着时代的话语权。“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男性利用礼法、教育、婚姻等各种社会控制手段,独占优势,将女性定格为“相夫教子”的角色,成为女性相对固定的发展方向。
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服务于男性,这样的思想在《莺莺传》中也不时流露出来。莺莺对张生的抛弃态度是:
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
聪慧的崔莺莺对于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料也存宽容,她说,你对我始乱终弃,我不会去怨恨,你对我从一而终,那是你有良心,只自哀叹自己的“僻陋”。她未指责张生的无情,实质上是由于性别定位的结果。作为女性,在中国传统父权中心的压抑下,传统女性自觉将身体托付给男性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在崔张二人的交往中,莺莺充满了矛盾,承受着来自伦理的巨大压力。传统伦理社会一向都预设女性对于男性的挑逗与勾引必须予以拒绝,莺莺初次面对张生也是这样做的,甚至在两人单独见面的第一次,莺莺也言辞拒绝了张生。但最终她还是让自己真实的情感战胜了伦理观念,因情感而突破了身体关系的限制,抛却伦理,充当了一回自我行为的主体。
因此,按照男权伦理,对于男性的“始乱终弃”,莺莺无奈的选择了“哀伤而不怨恨”。张生固然“好色而不淫”,但透过对女性身体以及女子的柔弱,不难看出,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男性一直占据着言论及身体行为的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请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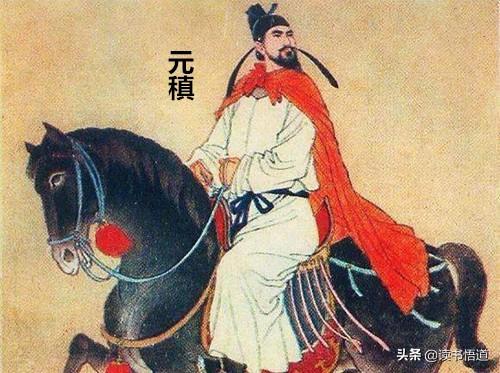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简单回顾下《莺莺传》的故事,崔莺莺是前朝崔相国之女,与母亲因故被困于庙中,得到张生的解救,因为红娘牵线搭桥,也因为莺莺对爱情的渴望,所以莺莺与张生,成就了好事,崔母得知,恨极,逼张生考取功名来娶莺莺,后来张生考中了状元,被当朝重臣看重,选为女婿,莺莺自然被抛诸脑后,多年后,故地重游,莺莺拒绝见这个“外兄”——《西厢记》里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写成了张生与莺莺大团圆。
相较于《莺莺传》和《西厢记》,莺莺传更现实,也更符合人性,其乐融融的结局,往往是梦想而已。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始乱终弃?
我个人的看法是张生始终没有爱过莺莺。爱上她和爱上她,真的是不一样的。很早以前,红娘就问过张生为什么不走正常路数,向崔母提亲,张生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什么纳采问名等等一系列的程序耗时太长,他实在等不及了,不愿意等了。真正喜欢一个姑娘,不愿意等?很明显,成年人都明白,这就是张生精虫上脑的意思,他要的,不过是崔莺莺的身子,其他的嘛,再说啰。
后来,张生发达了,怎么说崔莺莺的呢?“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不爱就不爱吧,为了开脱,竟然把曾经的枕边人,当作是妖孽祸水,可见,所谓的爱情,从来都是假的,至少在张生看来,年少的青春的崔莺莺,最大的作用,无非就是排解寂寞而已。
于张生来说,崔莺莺已经没有了价值,他要的东西,崔莺莺永远给不了。崔莺莺出身博陵崔氏,母亲出身荥阳郑氏,她是真正的五姓七宗望族的大小姐,如果她父亲在的话,光一个崔氏,就可以给张生带来无限的好处,更别说还有郑氏的加持了。可是,崔父已然是前相国,早就退出了朝堂的圈子,何况还死了,崔母一介女流,要命的是崔家并没有嫡亲兄弟之类的可以依靠。要说显贵吧,很显贵,要说没实权吧,也的确帮不上张生什么忙。
人都是务实的。张生作为读书读老了的,自有一番计算,相较于当朝重臣之女,崔莺莺能给的实在太少,张生想要在仕途上有作为,没有妻族的帮衬是不可能的,娶了崔莺莺,可以得到什么呢?除了一个重情重义的虚名外,好处很有限,而另娶他人,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何况大唐观念开放,婚前失贞的女子也可以有好归宿,崔莺莺失了贞,却也嫁得出去,有大把的人冲着她去,再说,崔莺莺外柔内刚,寻死之类的事情是不会做的——不会闹出人命,丑事不会被揭,张生放弃这段历史,也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嘛,负了一段感情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未来前程似锦啊。张生就是这么想,然后这么做了,至于黑历史,只要发达了,自然有人洗地,于他而言,没关系。(文/宛如清扬)
奉劝姑娘们,擦亮眼睛看清楚,婚前种种要慎重。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张生是《莺莺传》里的主人公,他对痴情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那么他为何如此呢?
第一、张生不爱崔莺莺,他巴结老夫人,是相中了崔家的银子。张生是一个书生,他到蒲州游玩,住在蒲州普救寺。恰好崔莺莺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回长安,途中也住进庙里。莺莺出身博陵崔氏,母亲出身荥阳郑氏,是名门望族之女。父亲生前是高官,家里有众多奴仆,万贯家财。
张生不过是一介穷书生,他便与崔夫人套近乎,因为张生的母亲姓郑,所以与莺莺的母亲连宗,认莺莺母亲为姨母。
张生已经23岁了,还没有成亲。可见他的家庭状况一般。否则早就应该成亲了。
张生认姨母,不过是想要有一个名门望族的贵妇人做靠山而已。希望老太太一高兴,资助他点银子。或者外人知道他是崔老夫人的外甥,对他高看一眼。
自从认了姨母,估计张生的生活费都是崔夫人负责的。张生进京所用的费用大约也是崔家资助的。
第二、张生不爱崔莺莺,他只是利用崔莺莺排排遣寂寞。崔莺莺颜色艳丽,光辉动人。张生一见,就惊呆了。然后请求莺莺的丫鬟红娘牵线搭桥,与崔莺莺春宵一度。
红娘建议张生和老夫人提亲,可是张生根本不想提亲,他搪塞红娘说自己相思甚苦,如果得不到莺莺就得死去。他不提亲、不纳采、不问名……总之,娶亲的三媒六证,他一样不想干。
张生23岁了,独卧禅房,春宵寂寞。他就是想得到莺莺小姐的身体,只是想和莺莺小姐洞房花烛。
张生不爱莺莺,如果爱她,就会舍不得让莺莺没名没分地和他私自约会。如果张生爱莺莺,就不会不考虑莺莺的未来,坏了莺莺的白璧之身。
第三、张生不爱崔莺莺,否则不会把自己和莺莺私会的故事,讲给同伴。《红楼梦》中,宝玉和香菱说起了薛蟠的婚事,他说:“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今儿又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的,后儿又议论王家的。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道遭了什么罪了,叫人家好端端议论”。宝玉认为,女孩子名字被外人提起,被人议论都是对女孩子的侮辱。
张生不爱崔莺莺,如果爱她,就一定不会把自己和崔莺莺的故事,讲给同伴听。更不会把莺莺的笔墨给其他人看。让大家笑话崔莺莺。
在那个年代,女子的名节非常重要。张生那么做,是在摧毁莺莺的名节。如果莺莺在京城,她都可能嫁不出去,因为她的名声坏了。
第四、张生不爱崔莺莺,否则不会给崔莺莺扣屎盆子。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元稹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他抛弃红颜知己,进京赶考。24岁,“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当了官。
不久他就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
张生当了官,就不再与莺莺书信来往了。他知道自己攀龙附凤的机会来了,于是彻底断绝与崔莺莺的联系。
他与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说的冠冕堂皇,仿佛他是一个心志坚强,能拒绝诱惑的正人君子。而崔莺莺则是一个红颜祸水。张生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克制感情,斩断情丝。
他把崔莺莺当成了妲己、褒姒这样的坏女人,他表示不做殷商的辛帝,西周的幽王,他不能被女人毁了前程和富贵功名。
结语:《红楼梦》中,贾宝玉爱林黛玉,可是他对林黛玉不敢说过格的话,免得唐突了林妹妹。元稹对崔莺莺,根本没有怜惜和尊重。他写诗,只是调戏莺莺,只是想着将崔莺莺据为己有。他对莺莺始乱终弃。
不过崔莺莺也是一位坚强的女人,被渣男骗了,没有自怨自艾。她嫁了人,开始了新生活。
多年后,张生又想起了崔莺莺,还想见崔莺莺一面。莺莺拒绝见面,并告诉张生:“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一叶七珠原创非首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句诗不知道打动了多少憧憬爱情的姑娘。可是你们知道么,诗句虽然深情,可是这诗的作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他就是元稹。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生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死于大和五年(公元831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白居易并称“元白”。
很读者都熟悉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喜剧,这戏剧中男主角张生没有辜负崔莺莺,两人最后携手在一起。其实,《西厢记》是根据元稹的《莺莺传》改写的,到明朝被改编成红极一时的戏曲《西厢记》。《莺莺传》名为莺莺记传,实为元稹之自传。元稹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了崔莺莺。崔莺莺家室不好,娶了她元稹在官场上得不到任何助力。以元稹为原型的《莺莺传》是一出元稹始乱终弃的悲剧,更让人不齿的是,元稹还在文章里为自己开脱。他说莺莺是尤物,不祸害自己,定祸害别人,我要顾全大局只有跟她断绝关系。 莺莺后来意识到知道自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该抱枕而去,以至再不能光明正大做人妻。但她没有怨恨元稹,甚至去信嘱元稹好好生活,不用牵挂她。 这是悲哀的清醒,她最后另嫁他人,终身不再见张生。
元稹在和崔莺莺有私之后,红娘问他为什么不求婚, 谁知元稹却说:“昨天我一见崔莺莺就不能自持,数日来废寝忘食,只怕没有几天好捱的了。如果明媒正娶,又要纳采,又要问名,几个月的时间我可能就会因相思 而死了。”多么无耻的借口啊!完全秒杀现在的花花公子。恰逢这时,元稹得到了长安令韦夏卿的赏识,而且韦夏卿还有个尚未婚配的女儿韦丛,于是顺理成章的,元稹娶了韦丛,抛弃了崔莺莺。多少年后,也许是受良心的谴责,也许是对初恋情人崔莺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不知道莺莺后来是不是看到这篇传奇小说,一生的伤痛,再也抹不下去。
当时二十四岁的元稹科举落榜,但是韦夏卿很欣赏元稹的才华,相信他有大好前程,于是将小女儿许配给他,而元稹则是借这桩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机会,不过两人在婚后却是恩爱百般,感情非常好。以韦丛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从元稹留下来几首那时期的诗来看,当时正是他不得志的时候,过着清贫的生活,韦丛从大富人家来到这个清贫之家,却无怨无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和体贴丈夫,对于生活的贫瘠淡然处之。元稹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政治上晋升的途径,却没想到韦丛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女子、体贴的娇妻。韦丛的贤惠淑良,元稹在数年以后,总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与他共度清贫岁月的结发妻子韦丛。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韦丛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此时的三十一岁的元稹已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爱妻却驾鹤西去,诗人无比悲痛。韦丛营葬之时,元稹因自己身萦监察御史分务东台的事务,无法亲自前往,便事先写了一篇情词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韦丛灵前代读。但即便如此,到了下葬那天,元稹仍情不能已,于是又写了三首悼亡诗,这就是最负盛名的《三遣悲怀》(即《遣悲怀三首》) 。元稹对妻子一直有深切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悲伤,韦丛与他同苦七年,却在他即将飞黄腾达的时候离开了他,而元稹能做的只有祭奠亡故的爱妻,以及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思念。“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韦丛因为几组情意绵绵的诗歌而永远留在了后世读者的心中。
韦氏去世后,元稹写诗悼念她,于是就有了这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甚至还许下了终生不娶的誓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等等,可以说篇篇都感人至深。我们从这些诗篇里可以想象韦丛是一个贤淑美丽的女人,还可以知道元稹是一个痴情感恩的男人。但是,元稹虽然嘴上说不娶,流连花丛的事情可没少干。
元稹31岁时,在成都认识薛涛,薛涛是唐代著名的女诗人,她制作的“薛涛笺”一直流传到至今。她才貌过人,不但聪慧工诗,而且富有政治头脑。虽然身为乐伎,但心比天高,十分鄙视那些贪官污吏,达官贵人。元稹认识薛涛时,她已经42岁了,但仍风韵不减当年。 当时韦丛还没有离世,元稹出使地方遇到了薛涛,两人互相欣赏,然后同居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元稹因为得罪权贵遭到贬斥,从此两人劳燕分飞,关山永隔,著名的薛涛笺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其实就是现在的情书。
薛涛一生未动过男女之情,遇到元稹,就像张爱玲遇到胡兰成:“见了他 我变的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心里是欢喜的 又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
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就是如此慈悲吧。 元稹确实是个懂诗的人,尤其是他写给薛涛的情诗更令薛涛爱潮汹涌。在薛涛自称自己已经老了,比不得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时,元稹的诗着实给她很大的刺激。他写道: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我们将会是同心人。大唐开国以来,女诗人并不多,洪度,你是最杰出的一个。洪度是薛涛的字。这些年来,薛涛几乎已忘记了自己的字。但元稹居然知道,薛涛感动万分。与元稹相处的那一段日子,是薛涛一生最快活的。薛涛仿佛从四十多岁回到了十四岁以前。后元稹要回京城了,薛涛嘱咐元稹:勿忘我!他说:不会的,我即使会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你的诗啊。你的诗我全带了,如你怕我忘记,就常常写诗给我吧。”元稹就这样带走了薛涛的诗和爱情。这是她一生唯一的爱情。踏上他新的仕途,后又做了乘龙婿,薛涛重回了浣花溪。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虽身为艺伎,却如此分晓进退斩断情丝。就是这样一位心底纯净、智慧冷静的蜀中一代才女,竟是被人生生说成品行不端。何其可悲。可读罢他与薛涛的故事,虽不至于说他无耻,但由此对他的好感尽失。再读此诗,却感觉他实在是虚假万分,虚情假意到令人不屑。
元稹实是有罪,薄幸寡恩,既不想与薛涛相伴终生,既不想救她于水火,又何苦给她希望和幻想,令她刻骨铭心地朝暮思念。与此同时又与名妓刘采青私交甚笃、如火如荼。元稹何其风流何其残忍。我们还记得薛涛笺和“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的诗。即便是史料齐全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还在大肆赞扬元稹的所谓刚正不阿,一往情深,殊不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认真了解事实的人,还公然推崇元稹的刚阿正直,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恩爱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莫待是非来入耳,从前恩爱反为仇。 这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几
句话,只要琢磨一下你就理解这是为什么了。喜新厌旧人之本性,没有必要讨论这些问题,说来话长,适可而止!
张生为何对崔莺莺薄情始乱终弃?
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其实共有三个版本:一是唐朝的《莺莺传》,二是元朝的《西厢记》,三是这个故事的历史原型,也就是唐朝大诗人元稹与崔莺莺的经历。
我们先来说《莺莺传》,说的是一个叫做张生的书生,有一次来到蒲州普救寺寄住,恰好当时有个崔家寡妇带着女儿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
这一年,著名将军浑碱在蒲地去世,他的士兵趁着办丧事期间进行骚扰,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很多,因此不可避免会受到乱兵的抢劫。
恰好张生与蒲地一位将军是好友,便请来了一些军队保护崔家母女,因此崔家才没遭到兵灾。后来崔母便大摆酒席款待张生,并引荐女儿崔莺莺与张生相见,张生见崔莺莺长的貌美如花,不由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张生便多次托崔莺莺的丫环红娘代为引见,而红娘却反问张生既然喜欢崔莺莺,为何不借着对崔家的这份恩情而光明正大提亲呢?
张生却认为媒妁之言要数月之久,到时自己早就相思而亡。其实从张生的这个态度来看,就已经注定他们这段感情只能是露水之缘。
后来在红娘的牵引下,两人私下往来两个月,并多次在西厢房一起睡觉,但这期间张生始终未提媒妁之事,而崔莺莺也没有提要张生娶她之事,毕竟张生是要到京城赶考之人,而长安的一切崔莺莺不能给予,崔莺莺也深知这些,不挽留不为难,也不会开口提婚嫁之事。
等到张生离开的前夜,张生也只是在崔莺莺面前愁叹,但不说任何誓言,崔莺莺这才慢慢地说道:“这段感情是我主动献身,我自不会怨恨。如果你娶我,那是你的恩惠。你不娶我,也是情理之中。正所谓山盟海誓,也有到头的时候,你又何必对这次的离去有这么多感触呢?”
言毕, 崔莺莺弹了一曲《霓裳羽衣曲》,多年还没弹几声,发出的悲哀的声音又怨又乱,不再知道弹的是什么曲子,身边的人听了哭了起来,崔莺莺也突然停止了演奏,扔下了琴,泪流满面;急步回到了母亲处,再没有来。第二天早上张生出发了。
后来,张生来到长安,还时常给崔莺莺寄来胭脂水粉,崔莺莺也回复书信。
此后两年,张生始终没能考中科举,他和崔莺莺的联系也就渐渐悄无声息,再后来张生索性留在长安,并娶了一个长安女子,继续科举之路,而崔莺莺也嫁了别人。
从这层意义上说,在《莺莺传》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爱情一样,明知道不会有结果,但还是在一起,最终却还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谈不上谁抛弃谁,只能说有缘无份,双方都有各自的路要走。
至于在《西厢记》中,前面的情节基本都差不多,只不过添加了崔母强烈反对的情节,再就是后来张生进京赶考高中状元,最后的结局也是大团圆,张生高中状元后回来迎娶了崔莺莺,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所谓的始乱终弃。
最后,就是张生和崔莺莺的历史原型,也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与崔莺莺的故事。
这是在公元799年,刚满20岁的元稹因考中科举被朝堂派到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任小职,当时正值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便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崔氏母女。
等到乱军平定后,元稹就崔家少女崔莺莺相爱。虽然崔莺莺才貌双全,而且家中富有,但毕竟没有权势,这与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离。根据唐代的举士制度,士之及第者还需要经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所以元稹便在第二年再赴京应试。
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着,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丛尚未许配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
公元803年,元稹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拨萃科,进入秘书省任校书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此时,韦夏卿又表示很欣赏元稹的才华,愿意将女儿许配给他。
元稹经过权衡得失,最后选择抛弃莺莺,而娶了韦丛。毕竟,对于元稹来说,这是一次难得向上爬的机会。不过,虽然元稹和苇丛是标准的政治联姻,但两人婚后感情却非常好,在苇丛去世后,元稹还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佳句来悼念亡妻。
对于初恋情人崔莺莺,或许是受良心的谴责,又或许是对初恋情人的难以忘怀,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恋为原型,创作了传奇小说《莺莺传》,即后来《西厢记》的前身。从这层意义上说,现实版的张生之所以抛弃崔莺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