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文臣尹嘉铨,是如何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时光将自己作死的?
尹嘉铨是乾隆年间的“名儒”,与乾隆皇帝同庚。尹嘉铨的一生很平庸,最高职位做到大理寺正卿,四品官。他的特长在做学问,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并且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尹嘉铨曾经对朱熹的《小学》加以注疏,形成《小学大全》,得到乾隆皇帝的好评。
因为善做学问,尹嘉铨被授予稽察觉罗学主管,觉罗学就是专门为皇室子弟设立的学校,稽查相当于督学。
乾隆四十六年,尹嘉铨七十周岁了,他被赐光荣退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养老。在京城,尹嘉铨的四品微不足道,到了地方绝对是“首长”。在家乡父老的艳羡目光中,尹嘉铨活得很尊崇,很舒坦,若不是后来发生的变故,尹老将在充满溢美的悼词中结束一生。
就在他退休的当年,乾隆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按旧例,乾隆会在保定接见当地官员,以及士绅名流等,当然也包括尹嘉铨这样的退休高官。
给皇帝的礼物,以及修改了若干遍的马匹话,一应备好,可是让老尹很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接到皇帝召见的通知,这让他很没面子。皇帝路过自己的家乡,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那就说明自己在皇帝面前没分量,一辈子京官白当了。
老尹接受不了了,昨天还享受着父老乡亲们的崇拜,以后还不得换成讥笑乃至鄙视的目光?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于是尹嘉铨决定自救。他叫过来儿子,拿出一封亲笔奏疏,郑重地嘱咐儿子,一定亲自送到皇帝行宫。
没费什么周折,老尹的奏疏还真到了乾隆手上。乾隆看着看着,眉头皱起。原来尹嘉铨奏疏的内容不是什么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其父亲尹会一。
尹会一是清中期较有影响力的名儒,著有《尹健余先生全集》。跟尹嘉铨不同,尹会一一生都出任地方官,漂泊于大江南北,官至两淮盐运使,从三品。由于勤于政事,尹会一的官声非常好,因此去世后,被朝廷批准进入“名宦祠”。
所谓“名宦祠”,是由各地建立的,用于祭祀对本地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官的祠堂。尹会一能入“名宦祠”,标志着他老百姓和朝廷对他的认可。
可是尹嘉铨不满足,他向乾隆提出两点要求:给父亲加谥号,让父亲入从祀。
加谥号大家都很熟悉,从祀是指入祭孔庙,也叫配飨,就是跟着孔子,一起接受后人祭祀。
孔庙除了祭祀孔子外,还有三个等级的陪祭人员。第一等叫“配飨”,有复圣颜回、述圣孔伋、宗圣曾参、亚圣孟轲,亦称“四配”;第二等叫“配祀”,有子路、子贡、子骞等孔子十一名弟子,和朱熹,合计十二人,亦称“十二哲”;第三等叫“从祀”,又分为先贤和先儒两档,合计一百五十六人。整个满清一朝,有资格入先儒从祀资格的,只有五人。
由此可见,从祀资格是极其难得的殊荣。另外谥号也不是随便可以加的,官方的谥号,必须经由礼部提交申请,有相关官员讨论认定,不允许自请。
尹嘉铨对父亲的推崇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应该不清楚,尹会一距离加谥号和从祀资格,还有相当的距离,况且这也不是哪个臣子可以自求的。那么,尹嘉铨为何要如此逾越呢?
我觉得他被坏心情搅混了头脑。由于得不到皇帝接见,让他丢了面子,恼怒之下失去理智,试图找补偿。这是其一,其二跟他自我膨胀的状态也有关系,他自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很高,其父水平不在其下,争取一下加谥号和从祀,他觉得当仁不让。第三点,或许他还认为为父求封,那是孝行,至少皇帝没理由处罚自己。
可是尹嘉铨忘记了乾隆是谁,拿自己的想法,揣度大独裁者,无异于摸老虎屁股。果然乾隆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旨将尹嘉铨交付刑部审理定罪。
老尹美滋滋地等着“雨露”时,被“雷霆”击中,一条锁链将他牵回京城,蹲进了大狱。
更糟糕的事在后面,乾隆知道尹嘉铨著作多,令大学士英廉牵头,查抄尹嘉铨的所有著作,从中甄别是否有悖逆之言,谋乱之语。
又一场文字狱开始!如果非要从文字里牵强附会挑毛病,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英廉即使有意放过尹嘉铨也没那个胆,那可是高压线。于是从尹嘉铨的老家和京城宅邸,搜出九十多部著作,大小装了几十箱,最后从中居然找出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估计这时候的尹嘉铨,恨不能撕烂自己的嘴!
面对拷问,尹嘉铨清醒了,智商又占据了高地。他做了两点,首先问什么都承认自己有罪,第二承认自己的罪是疏忽,而不是故意诋毁朝廷和皇帝。
史料记录了审讯的过程,明显可见其中大多是牵强附会,或者说是不同语境的理解歧义,但是尹嘉铨确实也让人抓住了一些小辫子。
比如:他在《尹氏家谱》中,用了“宗庙”、“宗器”等词语,他自己的解释是古书就是这么用的。这就显示自己的狂妄与无知,中国的哪一个词刚开始不都是平等的?“朕”在秦始皇以前随便用,你敢用吗?
又比如,他称自己的母亲去世为“薨”,“薨”这个词只有满清的皇亲才有资格用,比如皇太后、皇后、皇子、王爷等有爵位的贵戚。
最让乾隆恼火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他被尹嘉铨“盗用”“古稀老人”一词。乾隆在自己七十大寿的时候,作御制诗一首,自称“古稀老人”,还特地制章一枚,尹嘉铨居然也自称“古稀老人”。你虽然与乾隆同岁,但是不同命啊!
第二件事,尹嘉铨在他的《朋党之说起》中有这么一句话:“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句话与雍正的《朋党论》有悖,被认为是与皇帝唱对台戏。
其它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事,比如尹嘉铨把尹会一、汤斌等人称作“四子”,跟孔庙“四配”相提并论,被批狂妄至极。
经过前后十七轮过堂,最后形成如下意见:销毁尹嘉铨著作七十九部,所题碑文全部砸毁;尹嘉铨判绞杀;家产抄没,家人入官为奴。
后来乾隆“皇恩浩荡”,免除尹嘉铨死罪,也没有祸及全家。估计尹嘉铨就是个闲散官,没有结党的把柄被抓,万幸得以逃生,就是不知道,他以及他的家人,经此一吓,还剩下几口气。
这个事件中,尹嘉铨利益熏心,狂放自大,自惹祸端,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晚年,也毁了一家人的幸福,实属咎由自取。另一方面,乾隆帝的独裁嘴脸也暴露得淋漓尽致,也照见了满清没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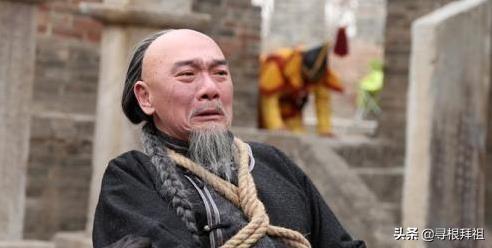
乾隆朝文臣尹嘉铨,是如何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时光将自己作死的?
尹嘉铨,原籍直隶(河北省)博野县,举人出身,先后作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升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
乾隆年间的尹会一、尹嘉铨父子,是清史上的名臣。父子官做的都不小,父亲做到吏部侍郎,儿子也做到了大理寺卿,都是高官。不过,两个有名倒不是因为官大,二三品的官儿,清朝多着呢。父亲的名气来自为官能干,,做地方官劝耕办赈很有成绩,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受到皇帝表彰的孝子。但是,儿子尹嘉铨的名声,却源于一起大狱——已经退休致仕的他,偏要上奏请求皇帝把他父亲和清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从祀孔子,并请求给他父亲一个谥号,借此为他的父亲扬扬名。自己也顺便博得一个孝子名声。没想到,却惹得皇帝大怒,把他打进了大牢。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返回京城时驻跸保定。早已退休解职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得到了这一消息,虚荣心作祟,想参加接驾盛典。可接驾的名单中没有他的份。这个尹嘉诠绞尽脑汁想要参加,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道学家尹会一,自以为找到最高妙的理由,于是便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号;二是从祀。他自以为是一箭双雕,要是得到皇帝恩准,不但自己捞得一个孝子名声,还能风光一把。写好这两份奏折之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将折子向上呈送,在家里美美的做开了他的春秋大梦。
乾隆皇帝看到了尹先生这两份完全是从自己私利出发的折子,立时十分恼怒,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乾隆圣喻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警告这位尹先生叫他老老实实“安分家居”着,他为自己老父请求谥号“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再妄想就是“罪不可逭矣”。一般人到此,恐怕早已经出一身冷汗,庆幸老虎没有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那样定已身首异处了,要做的事情就是连连祷告“阿弥陀佛”,赶紧夹着尾巴一边躲着去吧。
可是这位尹先生也不知着了什么魔,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以“古稀老人”自称,又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芝麻没得到竟然要西瓜了。乾隆帝看到这样的折子,估计脸色都得气绿了,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圣喻下了,这就好办了。承办官员各尽所能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大学士英廉查抄其家产,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又发现他强娶50岁的节妇为妾,其中最不可饶恕的罪名是“古稀罪”。因为,天子乾隆早就昭示天下,他是“古稀老人”。天子占了的称号,那是庶民百姓不能摸边的,普天下无论人名、地名哪有不避讳的。这位尹先生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争夺天子的风雅,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尹嘉铨被皇帝视为“大肆狂吠”的“疯狗”,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继而拷讯,查审著作和藏书;最后“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各种著作,无论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触犯禁忌,一律销毁。当然最后尹嘉铨其实没死,最终被乾隆赦免回家吃自己去了。
出自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据说当年办此案的刑部郎中,奉旨记有《纪事》一篇。说的是当年定罪之后,尹嘉铨判了死刑,乾隆意犹未尽,遂命尹嘉铨的好友,备一桌酒席,到狱中为尹送行,看尹嘉铨说什么,然后回奏。哪知道,在饮食时,尹嘉铨脸色不变,镇定如常,只是一个劲儿地自责自己混帐,辜负了皇帝的圣恩。这个情况反馈到乾隆那里以后,兴致好的乾隆见了尹嘉铨。
一见之下,乾隆先是声色俱厉地数落尹嘉铨的罪行,破口大骂,骂够了,然后宣布赦免其罪,放他归田。在尹嘉铨千恩万谢之后,乾隆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尹嘉铨回答道,说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余下的岁月,唯有天天焚香祷祝皇上万寿,争取活到一百岁,不敢一天间断,多一天就多祷祝一日。这样的超级马屁,惹得乾隆大笑。最终以这样一个超级马屁,被放过之后,回家养老了。
乾隆朝文臣尹嘉铨,是如何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时光将自己作死的?
我是潘多拉效应,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在清朝乾隆年代,发生了史上最诡异的尹嘉铨血案,这个案件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为何把乾隆气成这样?
对于清代比较出名的大臣,我想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刘罗锅,和珅、纪晓岚三位。实际上这仨老兄在历史上都不占什么位置。如果说他们仨占了点位置的话,那这个位置也多半是和珅占下来的,纪晓岚、刘罗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么个评价,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呢?这已经是很厚道、很厚道的评价了。要知道,就在纪晓岚、刘罗锅在乾隆脚底下磕头的时候,爆发了史上最诡异的尹嘉铨血案。
此案诡异之处,就在于情节简单,但内容却超出正常人的理解。事情发生在乾隆带着纪晓岚、刘罗锅在第五次南巡之后,经山西回京。当地离休干部、前大理寺卿尹嘉铨赶来迎驾,并呈上申请表,要求替他已死的父亲尹会一申请一个谥号。乾隆见状,怒不可遏,猛可地咆哮起来,喝令将尹嘉铨拿下。
拿下之后,乾隆又意识到尹嘉铨的做法并无不妥,不应该拿下。于是立即下令,让官员查抄尹嘉铨的家,在他写的文章中寻找狂妄之语,以便找个拿下的理由。
官员们在尹嘉铨写的文章里挨个字地挑剔寻找,竟然未能找出毛病来。可没有毛病怎么成?说尹嘉铨没毛病,那岂不是乾隆有毛病?你还想不想混了?
于是官员上奏,尹嘉铨文中语多狂妄,证据就是尹嘉铨在文章中引用了唐人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连诗圣的句子你都敢引用,真是太不像话,有这条证据就够了。于是尹嘉铨被判三千六百刀凌迟剐死,临至行刑,乾隆开恩,改为绞立决,用一条白绫勒死了尹嘉铨,以显示乾隆的洪恩浩荡。
杜甫的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竟为尹嘉铨引来杀身之祸,这其中的因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的症因,就出在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身上。说起尹会一其人,实乃帝国时代民众心里标准的模范官员。此人事母甚孝,服务乡梓,什么地方的百姓遇到了困难,尹会一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办公解决。百姓称赞他,猜猜他是怎么回答的?
如果搁在现在,官员就会说:感谢国家,感谢……感谢那个最大号的领导……这样的话,最大号的领导听了心里就特舒服,少不得夸奖几句。如果勤政为民的官员活活累死,各层次的领导还会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追悼会现场,表示功劳也有他们的一份。
总之,官场上的规律就是:活你要独自干,功劳却要归于大家,否则你会死得很惨很惨。
而那个尹会一,却全然不理会这些规矩,百姓称赞他,他却不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国家,感谢英明神武的乾隆大帝……他不说这些,说什么?他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我妈,这都是我妈让我做的。不谢乾隆谢亲妈,你说乾隆心里是什么滋味?
可以确信,每时每刻,乾隆都恨不能生吞了尹会一。可是尹会一确属传统意义上的清官,家徒四壁——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家里没床没被褥也没枕头,晚上睡觉的时候,尹会一就躺在地上,脑袋枕个土坷垃。这么个搞法,让乾隆想下手也难。
幸好尹会一还经常讲学,按说这是一个机会,只要随便抓住尹会一讲出来的几句话,牵强附会,硬栽给他一个谋逆,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在尹会一这里,偏偏是真的不可能。因为尹会一讲的都是些极为古怪的术语,诸如什么天理性命,这些形而上的名词,远不是原始人乾隆所能理解的。
始终抓不到把柄,乾隆应该是恨得牙根发痒,看着尹会一穷死。正当乾隆叹息,以为这个仇是没法子报了的时候,尹嘉铨却自己跑来了,竟然想为父亲尹会一申请一个谥号。理论上来说,像尹会一这种道学夫子,朝廷也确应该给个谥号——可正是因为应该给,乾隆才偏偏不给,而且要绞杀尹嘉铨,让别人摸不到自己的思维规律。
大人物,是一定要喜怒无常的。小人物一定要喜怒有常,循规蹈矩,这样才能够让周边的人对你有一个标签性的认知,才容易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大人物的思维规律如果被别人掌握,就多半死定了。此外,乾隆憎恨尹会一,还因为他讲学,讲学风起,帝国必亡,因为思想与智慧是摧毁专制的利器。这一点,也是学界的共识。
从上面我们可以得出,史上最诡异的尹嘉铨血案原来是他的父亲尹会一招惹到了乾隆。碰巧乾隆还没有对付尹会一,他已经死了。然而他的儿子尹嘉铨却不知死活跑来找乾隆为父亲申请谥号,你说乾隆能不生气吗
乾隆朝文臣尹嘉铨,是如何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时光将自己作死的?
乾隆带着纪晓岚、刘罗锅在第五次南巡之后,经山西回京。当地离休干部、前大理寺卿尹嘉铨赶来迎驾,并呈上申请表,要求替他已死的父亲尹会一申请一个谥号。乾隆见状,怒不可遏,猛可地咆哮起来,喝令将尹嘉铨拿下。
拿下之后,乾隆又意识到尹嘉铨的做法并无不妥,不应该拿下。于是立即下令,让官员查抄尹嘉铨的家,在他写的文章中寻找狂妄之语,以便找个拿下的理由。
官员们在尹嘉铨写的文章里挨个字地挑剔寻找,竟然未能找出毛病来。可没有毛病怎么成?说尹嘉铨没毛病,那岂不是乾隆有毛病?你还想不想混了?
于是官员上奏,尹嘉铨文中语多狂妄,证据就是尹嘉铨在文章中引用了唐人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连诗圣的句子你都敢引用,真是太不像话,有这条证据就够了。于是尹嘉铨被判三千六百刀凌迟剐死,临至行刑,乾隆开恩,改为绞立决,用一条白绫勒死了尹嘉铨,以显示乾隆的洪恩浩荡。
乾隆朝文臣尹嘉铨,是如何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时光将自己作死的?
尹嘉铨乾隆年间道学家,官至三品,父尹会。退休两年后正值乾隆到五台山驾临保定,为享龙恩浩荡想一法为父请溢号,既显自身是孝子又出了名,岂料得罪地方现任官员,联名告他强娶五十岁妇女等事,乾隆大怒将他处死,真所谓不作不会死。
乾隆朝文臣尹嘉铨,是如何利用退休后的大好时光将自己作死的?
尹嘉铨的死,是自己作死,是出于贪婪和虚荣心。在官途上,尹嘉铨已是大理寺正卿;在文学上,尹嘉铨加疏的《小学大全》更是得到乾隆的赞赏。而且,尹嘉铨还负责教授了旗籍子弟。可以说,尹嘉铨到七十岁退休时,已经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不负一生所学了。
但是,坏就坏在,尹嘉铨是一个贪婪且虚荣心极强的人。或许是因为之前得到乾隆的称赞,亦或者是因为他交手过很多旗籍子弟,让尹嘉铨觉得自己就是乾隆身边的“大红人”,就算是辞官告老还乡也一样。同时,因为《小学大全》的传播,也让尹嘉铨有了个“名儒”的名头。这么一来,尹嘉铨的虚荣心就更加的膨胀了。
所以,当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的时候,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以尹嘉铨当时的身份和曾为乾隆臣子的过往,尹嘉铨都有理由前去觐见乾隆。可是,虽然尹嘉铨也很想去觐见乾隆,但是他更想让乾隆去召见他,而不是他自己主动去觐见。
毕竟,这主动和被动的觐见,很大程度上会显示着尹嘉铨是否仍然被乾隆所恩重。如果是乾隆主动召见,那尹嘉铨无疑会更有面子,在家乡更能吃得开。可实际上,乾隆并没有召见他。这么一来,尹嘉铨就急了。但是,他又抹不开面子主动去觐见。
所以,尹嘉铨就打起了已过世的父亲尹会一的主意。尹会一是雍正时期的臣子,曾做过扬州知府,河南巡抚。尹会一对程朱理学也有一定的研究,而且也又教授他人《小学》的经历久而久之,尹会一也被人冠于了“名儒”的身份。
因此,尹嘉铨为了让乾隆召见他,便以尹会一为例子,给乾隆写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让乾隆为自己的父亲给个好的谥号;而是从祀,让乾隆批准他的父亲尹会一可以配祀文庙。
谥号这种东西,是人死之后便盖棺论定的。尹会一的谥号,在他去世之时,便已经由朝廷的确定了。而且,尹会一虽然有个“名儒”的名分,但这只是比一般的儒生强一点而已,难道还能和韩愈等人相比,还能追加个“文正”,“文忠”的谥号?尹嘉铨无疑是在做梦。
而且,从祀孔庙这种东西,也不是随便一个“名儒”便能够从祀的。尽管从祀只是文庙的第三等级,但很显然,尹会一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再说,能否可以从祀也是乾隆所决定,而尹嘉铨直接明确要求乾隆要这样做,岂不是僭越和教乾隆皇帝做事?
所以,乾隆皇帝对尹嘉铨很愤怒,但因为考虑到尹嘉铨之前教授过旗籍子弟,又在《小学》上有所成就,便念他是出于一份孝心,口头上骂了一句就放了他。
但是,乾隆的开恩并没有让已被虚荣心填满双眼的尹嘉铨看清形势。相反的,当乾隆驳回他的奏折后,尹嘉铨再次上了奏折。尹嘉铨的再一次举动,直接惹起了乾隆皇帝的杀心。所以,乾隆派遣英廉去寻找罪名,把尹嘉铨抓拿入狱了。
而乾隆给尹嘉铨的罪名也很简单,就是“古稀之罪”。“古稀之罪”或许就是文字狱的典型事件之一,当时,英廉在尹嘉铨的著作中,发现尹嘉铨居然给自己起了一个“古稀老人”的称号。尹嘉铨辞官时已是年近七十,说自己是古稀老人也无错。
但是,错就错在乾隆皇帝之前也自称是“古稀老人”。皇帝用了这个称号,那尹嘉铨这位臣子就要避嫌,不能再使用这个称号了。否则,那尹嘉铨就是想要和乾隆齐平,想要谋朝篡位了。所以,就是因为这四个字,让乾隆直接叛了尹嘉铨一个凌迟处死。但后来,乾隆又改凌迟为绞刑。
可是,无论怎么改,尹嘉铨这位被虚荣心所迷惑的老臣子,最好还是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