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主张是什么?
两千多年来,孔子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他关于教育的主张非常多,很难在这里一一列举。因此,这里我们只探讨问题的核心:孔子关于教育的主张,可以分为“教育目的”的主张,和为实现其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的主张。
孔子主张的“教育目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孔子生于东周末年(春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春秋乱世,应该如何救世呢?孔子知道,想要救世就必须要找到这个乱世的病因。
(图 | 《孔子问礼》)
天命又是什么?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乱?
孔子认为老天爷是人格化的,他是通人性,有道德的。周礼,即代表天道(天命)。然而,世间确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就是当前乱世的答案,为何“礼崩乐坏”?那是因为世人不认周礼。
政治秩序也是人的秩序,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形态是教育,这种教育首先应该是当政者们的自我教育,也就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和情操陶冶。君子能在具体的行为选择当中,随时遵从周礼,从而树立人事的典范。只要教导世人向往成为君子,那么这个世界的秩序也就恢复了。
因此,孔子的毕生理想就是将“礼崩乐坏”的社会恢复到之前周礼的秩序中。为实现这一理想,就必须要以教育的形式教化世人。
孔子的教育核心可以由一句话概括:以文化教养实现对个体人格的整体提升。正所谓“克己复礼”,这是孔子“教育目的”的主张。
孔子为实现“克己复礼”的教育目的,又提出了哪些主张?“儒”在最初的时候,是对某些职业的概括,其来源分别是以六艺教民的“儒”,和以德行教民的“师”。而孔子既是“儒”也是“师”,所以为后世的儒家奠定了基本面貌。
以六艺教民的“儒”,是当时社会上掌握特定专业技术的人员。比如观星象、辨别农时、预报天气等,以及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礼节、仪式的专家,尤其是治丧礼仪顾问。礼坏乐崩之际,朝廷之礼虽然被贵族们抛弃了,但在民间还完整地保留着一部分周礼(如丧服、相见、昏姻等礼),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持续地起作用。
以德行教民的“师”,则与官学中的乐师有关。先秦典籍中若单单提到“师”,则往往特指是乐师。乐师所教授的乐舞,一方面保留了很多上古巫觋传统的遗迹,如祭祀、祈雨等仪式。另一方面,周代的乐舞教育已经人文化,乐教主要以培养人的协调的德性、“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为目标。这是一种以艺术教育的形式呈现的德育。然而,这种教育面向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贵族子弟和未来的政府官员。
所以,孔子一生所关切的内容,就是礼乐文化。无论是授徒、从政、还是删诗作史的事业,孔子都是为了学习礼的内涵、恢复礼的秩序、发扬礼的精神,而这些主要是通过美育(乐)的途径来实现的。
然而,实现复礼的目的并不容易,必须克服多个问题:
首先,他能教育的人,只是贵族子弟和未来的政府官员。为了实现将“天”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当中,孔子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扩充“人”的内涵?
一、如何扩充“人”的内涵?孔子答:有教无类。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孔子说:“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呢!”,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法架构崩溃、个人意识觉醒以,个人的精神世界进一步扩大的历史潮流。孔子格外注重周文化中天人关系的传统,因而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点。这里的“人”也不再指贵族,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所有人。
要知道,在春秋之前,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接受完整的教育,这本身就是礼的一部分。而当时周朝的贵族或者其他文化人,不是依附于君权,就是被贵族豢养的门客。贵族依附君权,那些文化人呢,为君主和贵族服务,也通通都是官家人。
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既没有独立的身份,更谈不上心灵的自由。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制度逐渐解体。于是,那些贵族和文化人逐渐地流落到社会中,这样一来,他们的身份独立了,心灵也解放了,也就可以自由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了。
孔子把“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自己办学的时候,所主张的是“有教无类”。
那个时代的人想跟他学习,只要交适当的学费就行了。孔子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弟子当中,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有。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老师。
孔子将“人”的内涵扩充了,问题又来了:
二、如何传教,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载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礼的精神?孔子答:礼教为体,诗教为用。
比起那些形式性的礼乐仪节,春秋贤者们其实更关心曾作为天人秩序之载体的“礼”在当下混乱社会形势中呈现的实际生命力。这一点,从《左传》中各种“礼也”和“非礼也”的评论就可以体会到,当时的人们已经把礼作为规范、衡量人的行为的基本正义原则。
那时代的贤人,一方面想要完整地保留古礼的典章仪式,另一方面还想将礼的精神、礼的本意提炼出来,并且通过适当的方式作用到现实当中。而《诗》就是那个时代贵族社会共同的语言来源,是最能保持礼的精神的文化载体。
《诗》(即《诗经》)最初是民间口口相传的诗歌,在当时闭塞、信息稀缺的古代社会,是人们最得力的精神共享手段,它包含了地方风土人情的多样形态,成为沟通上下、远近的桥梁。
那时的人们通过《风》来沟通王政和民情,通过《雅》来讽喻和抒情,还要通过《颂》来完成庄敬典雅的仪式。所以,《诗》在那个时代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
这么说可能略显干巴,那么举两个例子:
在诗经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小雅·鹿鸣》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诗》是当时是各诸侯国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话语平台。歌诗待宾和赋诗言志,是上层社会流行的交往和表达方式,也是贵族交往礼仪中所必需的手段。无论邦国外交还是宴飨宾朋,都要歌《诗》并伴以优美的音乐。
外交官掌握了《诗》的内涵,就可以在樽俎鼓乐之间,得心应手地曲抑强权,展现本国的文化实力。如果一个士人大夫不具备欣赏和灵活运用《诗》的素养,就无法在往来酬酢的场合中合适地发言。这不仅自己丢人,更让国家蒙羞。
孔子曾经对他的儿子孔鲤说: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意思不是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是说,如果不学习《诗》的话语和表达方式,你就不知道如何恰当地与人说话(如何恰当地表达复杂的、微妙的意思)。
你看,《诗》不仅塑造了贵族文化,而且向世人传递了一种恰当、含蓄、得体的表达习惯。
其实,在之前周代的王官之学当中,已经有了诗教,主要是教导人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功利作用。而孔子扩展了《诗》的用途,提出了“诗可以兴”。
“兴”其实有两个意思:
- 第一层意思,是作为一种与“比”和“赋”并列的创作方法。郑玄指出,“兴者,托事于物。”“兴者,以善物喻善事。”(《周礼注》)兴与比经常联用,都是产生一种意象以指喻他事。
- 第二层意思,是作为欣赏诗而产生的升腾高越的情感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怡情。
诗歌的兴,用情景合一的审美意象来让普通人的情怀具有文采,让君子士人的忧怀得到宣释,让这些幽微的情愫感人益深,流传久远。客观自然世界没有改变,然而人们当下的精神世界意蕴却因为“兴”而变得不同。不仅如此,诗教的荡涤使人们从日常局限当中跳脱出来,由贫乏的“小我”而成为“大我”。人的精神世界因为“能兴”而变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开阔、包容,逐渐摆脱了小人的习气。
因此,解放并提升人们的精神思想,这是孔子诗教的最终理想,孔子为诗教注入了审美式教育的新内涵。
孔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复礼,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让审美式的教育与政治发生联系。
三、审美式的教育与政治如何发生联系?孔子答: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暫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孔子主张用审美式的教育方式把秩序、条理化入理想人格的修养当中,使人成为丰富与协调相统一的“君子”。
“君子”常常和“小人”一起出现,那时候的“君子”和“小人”只是社会等级与分工的分野,还不包含价值褒贬的意味。“君子”是中上层贵族与社会的管理者,“小人”则是承担具体职事的下层贵族或从事生产的庶人。概括地说,前者是协调组织者,后者是具体执行者。
而孔子强调了“君子”精神意象层面的意义,弱化了“君子”与“小人”身份、社会分工方面的意义。“君子”与“小人”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对“道”的把握: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孔子说:“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观念,作为人格素养的“和”,至少有如下两个层次的内涵:
- 一,“和”意味着一个人具有协调各种要素、创造新意义的能力。
- 二、“和”也意味着君子拥有广大的气量、心胸。
因此,君子的“和而不同”,是一项美好的情操。
孔子煞费苦心地教导世人成为“君子”,想让人“克己复礼”,然而,问题又来了:春秋时期,人们眼看着不遵循周礼的诸侯越来越强大,天命并没有对其制裁,那么人们有何动力一定遵循周礼呢?因此,孔子必须要为礼找到一个内在动因。
四、礼的内在动因是什么?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仁是德性之根本,是一个人对道德规范的内在自觉。它并不仅限于诸德目之一,而是具有统御功能的基础性的道德概念。
“仁”还是善恶、美丑评判标准的最终依据:“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认为美恶并没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标准,唯有仁人能准确地辨别善恶与美丑。
对于现实世界的政治,孔子主张实行“仁政”。仁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以对待家人的态度爱护生民,以文化、道德来维护秩序,反对滥用战争、刑政。周文化以民为天命之源,看重生命的尊严。殷人杀俘虏,周人则不杀而迁之。
管仲曾以大智大勇维护了周文化的尊严,他当政期间没有导致生灵涂炭,而且惠泽长远。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史记·管晏列传》
所以孔子不吝把“仁”的至高评价许给这位被世人认为品行有瑕的政治家。
孔子反复地强调,仁是人的心灵秩序,失去这个秩序,礼就找不到内在动因;仁是礼乐的精神内涵,丢弃了这个内涵,礼乐就成了没有生命的死物。
结语孔子主张以文化教养实现对个体人格的整体提升,以“克己”实现“复礼”的“教育目的”。为实现这目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把“学在官府”变为“学在民间”,实现了“人”之内涵的扩充;孔子主张“礼教为体,诗教为用”,最大限度地保持礼的精神;孔子主张用审美式的教育方式把秩序、条理化入理想人格的修养当中,使人成为丰富与协调相统一的“君子”,让审美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孔子提出仁是德性之根本的主张,为礼找到了内在动因。
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是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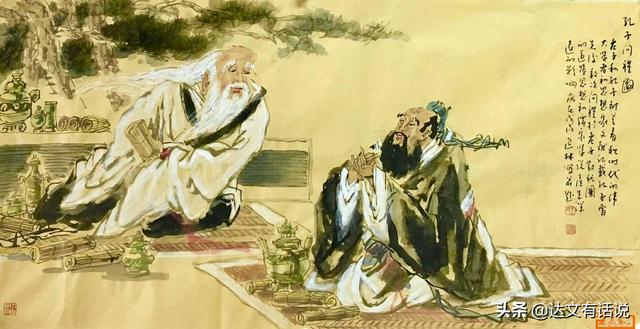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