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书法作品的品级?
书法作品有品无级。
这个品,也是依据做出评判的人自身修养、水平、社会地位来的。
鉴别是个复杂的概念,凡事要有目的,你必须弄清楚
“你因何而鉴别”。
所谓收藏,因自己喜欢而入手为收,为别人喜欢入手谓之藏——藏,现实的理解就是“为别人而保管”。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喜欢,那就好坏你说了算;如果你是为了以后出手,对不起,无可奉告——你没有办法知道以后买你这个作品的人他喜欢什么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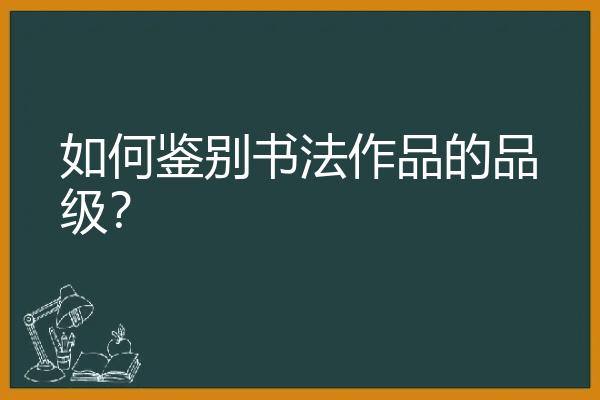
如何鉴别书法作品的品级?
第一阶段:普通大众认为好的书法是,结字匀称,用笔精到,笔画劲健而灵动,(临摹段)如果达不到这水平,就不是高水平,达到此水平,就是高水平了。上述我认为是初级水平。
第二阶段:临了十年二十年以上帖的人,并且创作作品,重技术安排,用笔,通篇和章法刻意安排的一类书法者,他们对书法理解什么是高水平的书法,即用笔精到,点画有神而灵动,通篇气韵连贯,章法布局合理,虚实相生,并得笔于魏晋,节奏感强,达到此类书法为高水平。而我认为这是书法的技术层面,只注重技术的躯壳,没有思想感情,重技巧不读书的一种书风。应为中等水平。
第三阶段,我认为书法的最高水平应在上述二阶段基础上,书人喜读诗书,手不释卷的文化人。他们在创作上,忘记技巧,全身心投入意境中,与物象对话,与天地同歌。他们的书风是简单自然,不为技巧笃伴,清远无为而幼拙,篆籀而不失灵秀,书卷而内涵充盈,这才是书法的最高水平。😀😀
如何鉴别书法作品的品级?
这个问题,其实是书法艺术的大问题之一。
判断一幅书法作品好不好,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社会上,在大部分只是喜欢,欣赏者和初学者中,往往各执一词,相互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不同看法非常混乱。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没有统一标准不是没有标准。这个标准,大体上是:
一:看法源。
只要叫书法,就要看法从何处来。是传统的法,还是自己的法。
看法源的问题,在篆书,隶书,楷书方面表现不明显。因为这些书体,不学习古代经典,胡写的基本都不象样子,大家一眼就能看透好不好;
几乎所有的混乱现象都产生在行草书这一大块。社会上对行草书的理解还存在许多误区,毕竟专业学习书法的人不多,一些从来没有认真学习传统的人,就集中在行草书这一块或自娱自乐,或欺世盗名,或到处骗人。而古今所有的行草书,基本是一个人一个风格,又都表现的自由浪漫,没有固定的写法。这一方面使人难以判断一幅书法的好不好,一方面又给浑水摸鱼的人提供了方便。
但基本的标准,肯定是有的。一幅字好不好,看是从古代经典中继承而来,还是自由体,拿毛笔在宣纸上胡写。没有任何古代经典书法的基因传承,可以肯定不好,甚至不是书法。
二:看创新。
如果还是一点一画原原本本照搬原帖,那是初级阶段。这样的一幅作品,也不能算是好作品。书法就要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表现个人的发挥和性情。所有的艺术形式,这个原则是不变的。
如何鉴别书法作品的品级?
说到书法的细节很多!
比如说提按,只是,现代人真正的懂得提按的人太少了。可能很多人不服气,你怎么能说太多人不懂呢?就你懂!不是我懂,是没有理解到魏晋唐书法的人,确确实实都可以说是不懂提按,即使是历史上的有些大家都如此!
飞白!书法历史上真正能写出飞白并存世墨迹的人很少,有些人为了制造飞白,使用枯笔,焦墨,枯笔是可以理解的,焦墨就是取巧了!飞白是书法功力的体现,没有强悍的书法功力是不能使用正常的墨水写出精彩的飞白。即使是头这人取巧写出飞白,在高手的眼里还是难以过关的。
险绝可以制造书法的跌宕,无论是涉及每个字,以及整体的章法上,没有险绝的书法就是一潭死水,平庸,呆板!
今天就谈这些,诸多细节问题留给以后再探讨!
如何鉴别书法作品的品级?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应该是既对书法传统有明显深入的继承,又具备强烈的个性特征,既能表现作者的大情怀大格局,又能做到人见人爱、雅俗共赏,而不是孤芳自赏。一幅作品欲同时达到这么多要求,实则不易,所以,特别好的书法作品其实是不可多得的。
特别好的书法作品一般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但书法名家也不能保证每幅作品都是精品。对书法家来说,创作一幅好的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综合因素的配合。比如,书法家要喜欢作品的内容,书写作品必须是自愿、发自内心的,作品所送对象是自己喜欢的人,创作时的氛围符合平时书写习惯等等。请人书写作品要有诚意,好作品都是求出来的,故常听人说“求字”二字。
还有人说,上百年才能出现一些作品能真正传世的书法大家。每位书法家在其作品的成熟期或者高峰期,也只有为数不多好的作品,这些好作品往往就成为书法家屈指可数的代表作。因此,书法名家的好作品难得一见,而他们的代表作,就更加可遇不可求了。
如何鉴别书法作品的品级?
书法欣赏是学习书法的重要内容。学习书法欣赏可以邦助学书者开阔眼界,取精用宏,提高对书法作品的审美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审美能力——眼光的不断提高是人们书艺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书艺水平的提高,除了临池的功力之外,主要靠眼光的提高。
宋代黄庭坚在《论书》中说:
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人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隨人意。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也说:
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穉,则天分之限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学力之疏也。由此也可见书法欣赏的重要。
一幅好的书作对于懂得欣赏的人是有巨大魅力的。欧阳询观索靖碑,李阳冰观大篆碧落碑数日不能去的故事,都可说是书法欣赏的佳话。然而,只有识者才会如此。就书法艺术的追求来说,临池和欣赏是不可分割的。功力是积累起来的,然而也并不是天天写下去就能不断进步。所以说“眼高手低”,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人们总是要求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使自己感到满意,如果自己经常不满意自己的书作,那他总会想方设法努力提高。眼高,手就要跟上去,眼再提高,手再跟上去,这样循环往复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
历来书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外露型的。它的美是一望而知的,如赵孟頫、董其昌均属此类。第二种类型是内含的。这种类型意境幽深,内含丰富,而其外貌有时是鉴赏水平不高的人所难于接受的。如清代的伊墨卿,有人给他一个“书如佳酒不宜甜”的评价,确很贴切。近代的沈寐叟、謝无量、高二适都可归入这一类型。第三种类型就是不仅内涵深邃,外貌也美,真可谓“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者,象钟繇、王羲之则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第三类型的书作要真能赏其妙谛,确也并不容易。比如在欣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时,我们应首先了解颜真卿博学工词章,正色立朝,一生正直不阿、而且是一位刚烈不屈,临难不苟的烈士。知悉颜平原的立身人品,再去体察他的方严正大的书风,就会完全理解并同意人品定书品、字如其人的说法,这时再看《祭侄文稿》,就会透过满纸忠愤看到这一书作真是大气磅礴,罕有其匹。如此看来,尽管我们不否定宋徽宗瘦金体的艺术价值,但这种书体似乎也只能写些风花雪月之类的东西吧。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一个人的欣赏能力和他本人的书艺水平虽然不无关系,却是要求不同、概念范畴不同的两回事。有鉴赏能力的人不一定能写出一笔好字,而有相当书艺水平的人却不一定鉴赏水平很高。对于前者,我们不应说“你自己既然写不出来,就不要发议论”。古往今来,不会作诗却善解诗的颇有其人,不善书却知书的人也是有的。要振兴书坛,恰恰需要这些别具只眼的品评家。对于品评家们,应该要求他们有广博的学问,既要懂得我国书法的传统、源流、历代的品评依据,又要能够善于吸取新的美学理论成果,这样才能提高欣赏能力,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
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书法的欣赏:
一,笔法、结字、墨法、章法当我们接触到一幅书作时,笔法、结字、墨法、章法都是看得到摸得着的,所以把它们归纳为“从实的方面看”。
这四者是不是等量齐观呢?不是的。尽管很难说各占怎样的比重。但四者之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笔法,也就是指用毛笔写出的字的点画形态。蔡邕在《九势》中说: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善,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那么,怎样的笔法是好的,怎样又不好呢?从正面来说,用笔要有停蓄,要能蓄而不发,要留得住。各个笔画要有轻重快慢的节奏,“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宋姜白石论用笔迟速说:
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我们从点画可以看出书写者的技艺,从技艺的运用和变化可以看出书者的功力和性情。
就笔法来说,不外方圆之分,以西周的鼎彝到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总的说来是从方笔到圆笔。再从圆笔的秦篆发展到方笔的汉隶。汉隶《石门颂》用圆笔,有篆书意趣,方笔的隶书如《张迁碑》、《礼器碑》。《天发神谶碑》则用隶书的方笔作方整的篆书,楷书和《爨宝子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铭》、《始平公造像记》都是方笔,《郑文公碑》、《瘗鹤铭》则是圆笔。草书《书谱》是圆笔,《景福殿賦》则是方笔。当然,还有方圆并参的
结字就是指字的形态,字的结构。中国文字是由各种笔画循着一定的结构规范搭配起来的,这个形态大有讲究。
第一,从书法源流来看,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章草、今草、楷书、行书,这些书体的演变,主要是结体的演变。
第二,在书写上就其结构而言,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安排要求,如我们常说的偃仰向背、阴阳相应、鳞羽参差,以及避就、顶戴、穿插、意连等等。尽管有这些普遍承认的法度要求,即要求停勻、平稳,却每个人写来都有自己的面貌、风度。
第三,在有法度的基础上,又要能自出新意,所谓“结字无定法”,所谓“结字奇而稳”,也都是这个意思。新意是有法度的、有准则的,而不是无本之木。
第四,结字与用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连属,又相对峙。很明显的道理是:无一字无笔画的运用,而与此同时,无一笔不在字的结构之中。字的结构体势之美,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笔画的秾纤间出以体现,而笔画的机杼妙用又需通过字的结构来发挥。所以,结字与用笔说是两回事,在某种意义上却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回事。
第五,《书谱》中对书体有很精辟的论述:“古质而今妍”,“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就是说吸取古代的风貌时要注意不要违背时代的要求,如取流行的体势则要注意不要沾染上不好的习气。当然,不能说质朴好,妍媚好,但无论如何好的作品总要经得起品评,如果一幅字乍看很好,但经不住看,越看越不好,归根到底是缺少隽永的意趣。中国艺术审美上有一句话叫做“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墨法,用墨如何也是品评的要点,传世的很多名迹在用墨上都是很讲宽的。《书谱》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这就是说用墨不单调也是种艺术。重要的是要在自然之中见匠心。谛视名迹中的枯笔,实际上并不枯,所谓“枯,不枯,中润”就是这个道理。董其昌说:“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者合之,乃成画诀”,这虽然是用来题画的,但在书法上也可借鉴。当然用墨和书体也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楷书要求停匀,行草书则要多些变化。古人有云:“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大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运墨好坏显然直接关系到艺术效果,所以《书谱》在提到五乖五合时把“纸墨相发”作为一合。我们不应孤立地去看用墨,墨趣也是通过点画、结字表现出来的。卫夫人《笔阵图》中有几句话:“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里看来是讲点画,实际上也是讲用墨。当然,有时厚重与墨猪,筋书与病书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古代很多值得后世取法的墨迹,如李建中的《土母帖》,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都是以凝重浑厚、朴茂郁勃见称。又如有人说黄庭坚草书有惜墨如金之妙,又有人说黄的草书如枯槎架险。其实,仔细看来其中也偶有数笔用墨较丰,这就是说,惜墨如金也好,枯槎架险也好,恰恰是从这种用墨对比之中得出的评价。
章法,又叫布白,就是通篇来看一幅字,这也是品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点成一画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这个排列问题大有讲究,古人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可见考虑得是非常缜密的。章法大体上不外乎几种排列方法:即横直成行、直成行横不论,或星罗棋布等等。看来不复杂,但从古到今也变化不少。比如行距的疏密,字距的疏宻,以历代墨迹中可以看到这些。明以前一般行距较宽,至清代就很少看到这样的布白了。清代刘墉的大字,字距行距疏疏朗朗,看来好象一个一个字单摆浮搁着,但远远望去却行行贯气,且通篇气象圆融,于静默中有运势,可说别具风貌。应该说古人在这方面的创造也是不少的。还有所谓秾纤相间,大小相间等等。最重要的是气不断,气要圆,而且要出于自然。刘熙载提出的“章法要变而贯”,就是说既要有变化,又要贯串一气。所以通篇的位置经营,虚实照应,不仅是品评优劣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书学中大有探讨余地的一个领域。此外,还应注意到古人关于布白的论述常与结体研究在一起,比如邓石如曾提出:“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宻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应该承认,笔画、结体本来就联系着布白效果的。再如“担夫争路”之说,看起来是对布白的描述,实际上这种艺术效果图如果不从字的结体体势来考虑,如果不从字和字的上下左右错落关系来考虑,如果不从笔画走向以及与周围的字形成的照应关系来考虑,那又如何理解那种超奇度险的艺术趣味呢?
从以上所讲备点可以看到笔法、结字、墨法、章法这四项要素,尽管从品评的角度来说各有所指,但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相互渗透,甚至是互为因果的。
二,形貌与神理,功力与性灵,自然与雕琢笔法、结字、墨法、章法都是可以看得见、能够言说的表现形式,而鉴赏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要透过形式看内容,这最主要的就是看神理。神理的核心内容就是作品表现出的神采。南齐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唐代张怀瓘说:“深识书者,性观神采,不见字形。”所谓神采,是指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这是鉴赏书法作品时要着力去感受的主要内容。古人常常用人类和自然界一切事物来评论书法,其目的也在说明神采。例如: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古今书评》)。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唐人书评》)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书后品》)。没有神采的书法如土梗木偶,娟面腊人,纵然妍美,亦无生命。学书要取神采,鉴赏亦如此。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
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真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杨少师变右军之面目而神理自得……两千年来善学右军者惟清臣、景度耳!以其知师右军之所师故也。变其面目得其神理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试加分析:以清代来说,康熙学董,乾隆效松雪,御刻《三希堂法帖》中赵、董所占篇幅之大可见一斑。说后世登二王堂奧的惟赵、董,这是极大的歪曲。其所以如此,首先是政治需要,赵松雪尽管是宋宗室却降了元,而且做到翰林学士承旨,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自然不提倡民族气节;其次,乾隆本人的字有松雪风,说赵登二王之室就意味着乾隆也是二王的继承人了。我们看自唐以后临《兰亭》的真是不少,多数临摹本都可以说具体而微(如以定武本为圭臬),而赵的临本却仍是赵的本来面目,有的字结体虽象而笔致完全沒有那种雄强之势。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赵跳不出他自己的那种柔媚书风的缘故。康有为所说的但模其形而失其神,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吧?我们撇开《兰亭》、《圣教》再看一些流传有绪的王帖,拿颜平原,杨风子的行草书相比照,就更可看出颜、杨融合汉分于今体。抓住雄强的本质就使人感到形貌虽异却神理相通。这就是说笔致的接近是根本上的接近,神理的接近,而结体的相象只是形貌而已,包世臣提出“神为上”是有道理的。清朱和羹也说:“要知得形似者有尽,而领神味者无穷”我们品评书作自然要特别注意神理。
欣赏品评不能不注意功力问题。“规矩既失,神就无存”。我们品评书作,要从功力上来品评,同时还要从性灵的流露与发挥上来品评。清朝陆听松《书画说铃》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
著意而精者,为心思到而师法正也;著意而反不佳者,过于矜持而拘滞也。不著意而不佳者,草草也;不著意而精者,神化也。有临摹而妙者,若合符节也;有临摹而拙者,画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机趣生而兴会佳也;有自出心裁而无可取者,乃作意经营而涉杜撰也。这些议论使我们认识到功力与性灵的结合与发挥是完全可以用于书作品评的。古人有这样的话:“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书谱》上的“五合五乖”之说固然也可以邦助我们进行欣赏,但真正的精品应该是为力与性灵和谐结合的产物,应该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看都是自然的,不是刻意雕琢的。黄庭坚有句话:“初未审识画,然参神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悉知巧拙工俗。”这就是说书艺到至高境界,功力是内含的,望去若无功力。杨凝式作书每不检束故多奇岩,刘熙载称:“杨景度书不衫不履,然而非独势奇力强,其骨里谨严,真令人无可寻间。”陆放翁有一句论作诗的名言:“待到无人爱处工”,作诗不要取媚于人,作书何独不然?所以多为酬应作书是很容易写坏手的。与这问题有联系的是平正和险绝的问题,生和熟的问题。《书谱》中有这样几句:“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还需补充一句就是:“难能可贵的是寓险绝于平正之中,遁榘矱于恣肆之内。”至于说到生熟,俗谓“由生入熟易,由熟入生难”,生是生涩,熟选熟练,由生涩到熟练是人们能够理解的。而再由熟练到生涩是怎么回事呢?这后一个“生”是大不容易的。这绝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由娴熟转而追求质拙,从而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所以说这个“生”,是不落前人蹊径的“生”,是别具风貌的“生”,说它难是决不过分的。要知道熟则伤雅,熟则近俗。赵书熟,所以从明朝起即有不少人说赵书俗,甚至到清朝梁闻山也说“子昂书俗”。
三,格调、气息与习气格调通常指书作的风度、仪态、风格。气息就是指书作的意趣。从这方面来品评自然要求更高一些。这就不仅要求欣赏者本身有相当的艺术修养,而且要求有相当的字外功夫。这条标准是异常重要的。有这种情况:有人朝夕经营点画之微,功夫不可谓不深,但书作都缺乏隽永的意趣,原因在于格调低,书法作品只有些笔墨技艺。換言之,这种书作尽管人们得承认写出这笔字需多年的功力,但一看也能断定它不是出自一个富于学养的人之手。而格调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书作的品格,这是不能忽视的。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把姚鼐的行草书品位定得很高,看来总是和这位先生长于义理,考据词章,特别是精研经学,工于古文不无关系的吧。
这里再谈一下习气的问题。什么叫“习气”?书法上所谓习气,一般是指个人书写上的积习。清恽南田与王石谷论书画一则,对习气评说得很清楚:“凡人往往以己所是处求进,服习既久,必至偏重,习气亦由此生。习气者,即用为之过,不能适补其本分之不足,而转增其气力之有余”,所以偏重是习气的实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习气是阻碍进步的东西。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后人很多学宋代苏黄米三家的字,而很少人去学蔡襄的字,为什么?因为蔡没有什么习气,而学苏黄米的字恰恰多是从学他们的习气入手的。尽管有人不赞成这种临池态度,但人们看了这样的临习之后转而觉得学得象。譬如说:苏字厚重而有抗肩的习气。明朝吳宽学苏字,还故意夸大这种习气,使人一眼看出他在学苏。其实即使很象,又有什么意思呢?黄庭坚的习气是结体奇瘦,中宫收紧而笔画纵放,明朝吳门画派的沈石田一辈子学黄字,反正他的字题在画上不讨厌也就是了。尽管他在这方面下过不少功夫,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他在书法上有什么成就。后人学米的更多,因为米的习气更重。其特点是自左向右欹侧,有那么一股霸气。我们知道苏黄米都是学养极深的,他们各自的习气是和他们的书作杂糅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他们各自独特的风貌,所以这些习气在他们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而后世沒有他们那样学养的人,学他们的字,乃至偏重夸大了他们的习气,岂不令人觉得乏味?
四,鉴赏书法需要多方面的修养书法的鉴赏需要鉴赏者多方面的修养,经史之学,文艺美学素养、经世阅历等对鉴赏书法作品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我们在欣赏时,除了应该看到那时王羲之在书法造诣上已臻人书俱老的化境(即书谱所说的: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以外,还应看到当时他所处的环境、际遇:江左文人集会,以逸少为文章泰斗,推他撰序,而他一方面为此踌躇满志,一方面又受东晋士风的陶染和影响,感慨胜会不常。这篇茧纸文稿就是这种交织着矛盾心情的产物。据晋书等史籍所载,王羲之擅文采,,境界极高,当时虽流行骈文,讲求词藻华丽,而王羲之的文风则比较恬淡,有政治识见,所作文辞,质直尽言,不事采飾。如果我们能对右军的人品、文风有一定的理解,那将有助于体察他的书法风貌。而这篇“兰亭序”手稿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超脱自然而又极富变化。所以书谱给“兰亭集序”的评价“思逸神超”是很有见地的。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学知识,欣赏时就只能停留在“兰亭集序”的笔法、结字等形式上。又比如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如果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我们就可以全面欣赏这幅历来受到人们激赏的艺术珍品。
首先从内容上看。这两首黄州寒食诗既写出了苏东坡在受贬黄州时的凄苦生活,又写出当时萧索苍茫的心境。前首以海棠花遭雨后很快凋谢,借惜花而自怜。后首借空庖寒艾、破灶湿苇极写生活艰难,又以乌衔纸点明寒食时人家烧纸的情景,从这里引出“欲归朝廷,君门九重之深,欲返故里,坟墓万里之远”这样一种进退失据的悲叹。结句说虽至穷途未路,但由于历经忧惠,已心如死灰,欲哭无泪。“死灰吹不起”既指寒食烧纸钱的灰经雨后而吹不起,又比喻自己的内心。一语双关,言尽而意不尽。这真可说“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从诗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生活如此凄凉困苦,但作者还是旷达的。这两首诗就意境的苍茫沉郁来说,宛如少陵,而托物寄兴又象太白。如果我们有过与作者类似的遭遇,对这两首诗就一定产生嘤鸣之感。理解所书文字的含义,我们就能把握到作者书写时的激越哀伤、心潮起伏的心情。从理解书写文字含义着手,从掌握作者书写时的情感因素着手,是我们能否正确地掌握作品的艺术内涵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看这幅书作,除就字的形体,因字就势而有自然的大小相间外,总的看来前小后大,总体观之越到后面,气势越盛,这和诗意的发展若合一契。通篇书作,从用笔来看可沉着痛快,确如黄庭坚所说“兼颜真卿、杨少师(凝式)、李西台(建中)笔意。”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看到,这幅书作的绝妙处还在它的气息和神韵上。字幅中有两个字是衍文,用旁点点去,漏写一病字加在行侧。可谓不经意而工,即所谓神化者。这两首是抒发性灵的诗,这幅字也是抒发性灵的字,由乾隆的题识中有这样一句“所谓无意佳乃佳”,倒是点到了关键所在。陆游有诗云“诗到无人爱处工”,这幅字可以说是:“书向无人爱处工”。信笔写来,把沉在心头的百感,寄兴于笔端。所以这是当性灵和技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杰作。
书法的鉴赏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因此,在鉴赏书作时,人们常常会由书作联想到作者创作时的状态,作者的人品、气质和经历等等书作中并未直接展现的东西。除此而外,还会由书作联想到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情态,从而感受到书法美之所在。实际上,欣赏过程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但是,倘若我们仅仅具有书法方面的功力和知识,毫无学识修养,孤陋寡闻,困于一隅,囿于某派某家之说,是不可能具有真正欣赏眼光的。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