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感谢邀请!
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学者司马迁所著,成书于汉武帝时期,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历史学界地位极高。
而《竹书纪年》的成书年限上要早于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书由是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所以从时间上看,其要比《史记》大概早200年。按理来说,《竹书纪年》应该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才是。
但是,但是在传统史学界,《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一本“异书”,因为书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其内容与《史记》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比如,《史记》中所推崇的尧舜禹禅让,在《竹书纪年》中却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与此同时,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后来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还有《竹书纪年》中说,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而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是囚禁太甲3年以后见太甲改过自新了便将国家还给了他。
以上种种记载,可以说是极具颠覆性了,那么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竹书纪年》成书以后,并没有作为史料一直传承下来。其是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史记》成书近400后,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
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并没有参考到《竹书纪年》的内容!
第二,在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统一文化,统一思想,听取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这些书籍或是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或是被焚烧销毁,加之后来秦朝灭亡,天下大乱,像有关先秦时期的珍贵史料大都遗失,所以两本书的参考史料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第三,各自主观性有所不同。
比如《竹书纪年》有着很大主观编撰的嫌疑,要知道其成书的那个时代可是三家分晋,以下克上,礼乐崩坏的乱世,特别此书还是出自分晋之一的魏国。所以很有理由怀疑其目的性,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
而《史记》同样有着儒家思想的灌输,其记录的先秦时代那段历史,太过于的理想化,似乎远古的先民们,比我们更加的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未免有些不真实。人类的发展,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如此看来《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这两本史书我们都不能武断的去评判其真假。只能将作为参考,多方论证,不可全信一家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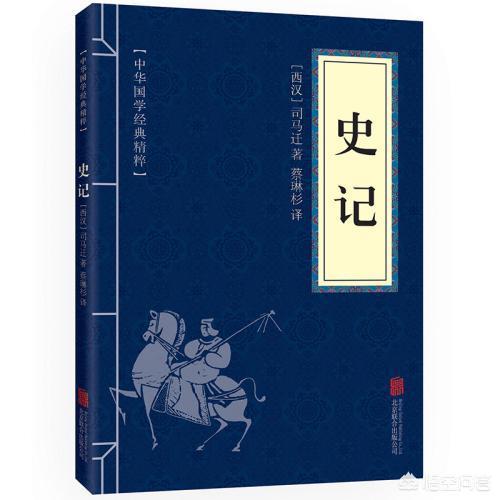
《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史学是很严肃的,不能没有证据就发明创造,以上答主说竹书纪年是野史的,你们够了!那是魏国国史!是史官写的。可靠程度不亚于史记,先秦史很多问题反而是竹书纪年比史记更正确
第一,史记对于汉代以前历史,是二手资料,并不是原始史料,是二传手,而司马迁手中资料未必是准确可靠的,史记并不百分百可靠,举例,关于中宗祖乙,竹书纪年和甲骨文等其他史料相印证,是正确的,而史记是错误,还有苏秦苏代史记更是错的离谱,先秦纪年史记错误比竹书纪年多多了,毕竟竹书纪年才是先秦当时的史官亲手记载,当然竹书纪年在更早的商和西周时期记载一样错误很多,比如伊尹,竹书纪年就是错误的,史记和甲骨文相印证,是正确的。
再有,著名的“共和”问题,我国国名共和国的来源,共和纪年,史记记载是周公和召公共和治国,但竹书纪年记载是共伯和干王政,共伯和篡位当王,近年史料越来越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史记是错误的,
竹书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
《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竹书纪年》为史料可信。
对于春秋战国,毕竟竹书纪年的史官是当代人,比二传手司马迁记载更准确是自然的。
第二,竹书纪年已经失传,现在流传的是竹书纪年在各种传世文献中的引用,如《古本竹书纪年辑正》,哦,竹书纪年还有今本和古本两个体系,所以,竹书纪年真正的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
第三,《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竹书纪年>所产的年代为春秋时的晋、魏史官所作的:″编年史",年代较久。也就是说:″更自然的靠近古代历史",它的真实性就更可靠。其中还有,当时的儒家思想还没灌输到所有人,也包括编史者。所以在编辑时,不会受到任何思想的左右,因此可以实是求事保留原历史。
而司马迁的<史记>,远离更远的历史。有些只能靠:神话故事和传说来编辑,事实难以清楚。更主要的是,他所处的年代,儒家思想以被立为主导思想,司马迁不可能不被熏染。再加之自身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也可能挾杂着一点:″以古论今"的个人思想。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中,所编辑出来的<史记>难免与其它:如出土的竹简上说法不能统一。可能是带仇恨去写历史,因此有些涉嫌伪造。如<史记>中的秦法律,与出土的真正的秦法竹简大相径庭。
因此,<史记>中有很多不实之处,所以我更相信靠近历史的<竹书纪年>。虽然在它被发现后,也可能被后人篡改过,但它与<史记>相比,可靠性还是较大的。
<竹书纪年>,成书早于<史记>。被发现,晚于<史记﹥。但它记录的东西,与现今所考证的史实是相同的,所以<竹书纪年>还是很可靠的。
《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题主看法欠妥,有抑《纪年》而非议《史记》之意。《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就应该以《竹书纪年》为准吗?恐怕未必。
首先,世上本就没有《竹书纪年》传本,拿什么去跟《史记》比较呢?进入宋朝,已很少有人见到《竹书纪年》了,它在那时已亡失了。后来,有人掇拾《纪年》佚文,凑合史传的记事,抄录《宋书符瑞志》的文章,托名梁沈约注,是为《今本竹书纪年》。至清钱大昕、纪均、洪颐煊、郝懿行等已疑其为伪书。朱右曾更力斥其不足信,并从各传世文献中辑出《古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加以补充订正,后经我国文献整理专家范祥雍先生校理、订补,加上范先生依《史记年表》整理出的《战国年表》,仅百余页的小册子。可以说内容极为有限,不及《三家注史记》内容四十分之一,怎么能跟《史记》媲美呢?
其次,两书性质各异,《史记》上起五帝下迄汉武帝,包罗万象,是司马迁对其所能见到的文字材料和口述历史的系统梳理,是一个浩大工程,倾注了司马氏几代人的心血和这位伟大史家的真知灼见;《纪年》仅魏、晋史书,迄于魏襄王,仅国别史,而且内容多已残缺,难窥全貌,甚至绝大部分内容需借助《史记》方可理出头绪。
历史学是个材料科学,《史记》以今世逻辑观之,确有不乏推敲之处。但从《史记》记述,与其所运用的《世本》《国语》《左传》《战国策》传本比较来看,司马迁极为忠实文献,并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把握,这是一个真正史家的可贵品质。但一些列传比较有文学性,博采途说,我们应以《本纪》《世家》《书》《表》为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很多考古材料,太史公没法见着,比如长沙马王堆所出十几篇苏秦书信,那是苏门弟子的绝密,所以今天看来,《苏秦列传》有很多不实之处。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不掌握《战国纵横家书》的情况下,能作出很多精彩评述,已足见司马迁的睿智。
最后,《竹书纪年》虽系战国中后期史书,但却出土于晋武帝咸宁五年,那时太史公已逝数百年矣。但说实话,数车竹简虽由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荀勗、和嶠、束皙、卫恒等整理,但时人毕竟已不怎么懂战国文字。若太史公能见着那些竹简,《史记》面貌又当如何,我不敢设想。起码临不着后人说三道四。
没有《史记》,中国文化是什么面目,我也不敢设想。两千年中,《史记》塑造着中华国民精神,太史公可谓不朽矣。我们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不应该苛求前贤;但像《汲冢竹书》那样的文献,应该越多越好——这恐怕正是史学真正的魅力之所在!
《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谢谢邀请。
《竹书纪年》的确是先于《史记》成册,奈何在先秦时期便被湮灭,直至西晋才被重新发现,换句话说,真正面向大众的发表会晚于《史记》。
《史记》应该属于汉朝官方的史观,而被发掘于战国魏王墓的《竹书纪年》的身份属于野史,说好听点是有待考证,难听点就是不予采纳为正史。
主流和野史,当然是主流被供奉,野史被不屑。
理由很简单,《竹书纪年》是一部很颠覆的史册,尧舜禹汤的禅让与德政都被彻底抹煞,几乎用两个字形容:厚黑。
儒家弟子们岂容这类的史观来挑战已由《史记》建立的史观系统,很快就再次湮没离散,直至宋代又一次被整理成册。
奈何宋代的儒学更是对其视如异端学说。
这是《竹书纪年》的命运。
至于司马迁编纂《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目前还未有尘埃落定的考证。
但据我个人认为:
第一,秦的焚书坑儒,之所以《竹书纪年》在西晋时代的战国魏王墓被发现,也就是说存于世面的现有书籍,特别是这类的各诸侯国的官方书籍全被秦始皇掌控,寻常百姓和贵族并没太多收藏,所以被集中大量毁掉是很容易的,因此在后世掘墓过程重新被发现属于正常现象;
附:秦焚书应该是有的,统一嘛,话语权掌控很需要,特别是各国的史观需要统一,书籍更是掌控话语权与解释权的重要渠道,因此司马迁在只能在众多只能依赖背诵和默记待日后复原的学者那里获得资料。
奈何这些学者理应会对厚黑二字重新修订,甚至是舍弃。
第二,司马迁的资料来源还有部分是来自民间演义;
呵呵,这一点就不需要过多说明了,所谓演义和史实是有出入的,特别是道统和反道统的划分更是叫人有先入为主的观感,并且有美化与粉饰的嫌疑。
一家之言,仅供交流。
《竹书纪年》早于《史记》,司马迁编的《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讨论。
司马迁对离他比较远的历史事件是怎么记述的呢,两个办法,一个是找史料一个是找口述资料。但是秦始皇时期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不少史书都不存在了,所以找史料并不能完整找到信息。而口述资料会在人口耳相传中,有所变化。所以说,司马迁在探寻离他很远的历史事件时,确实可能写下的东西并不是历史真实。
所以,《竹书纪年》中会有不少内容和《史记》不一致,当然也不是说竹这本书里面内容完全正确,只是想说明司马迁在当时的条件下,对离他比较远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复原。
而竹这本书离得比较近,相比较而言,就靠谱一些。
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详细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